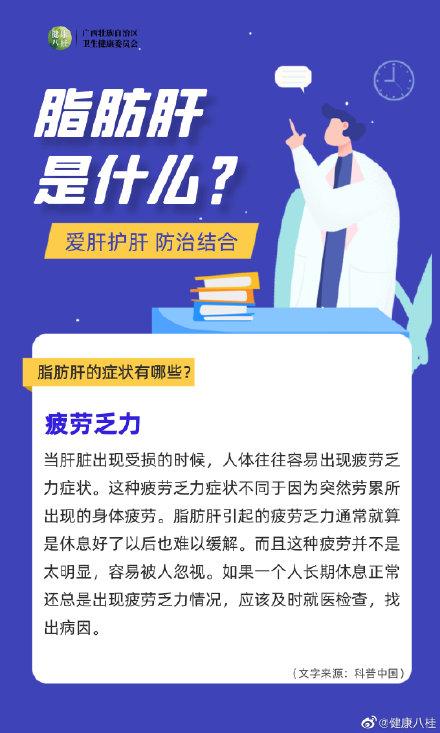文/月下婵娟
这是我深切钟爱着的一道菜。它来自于毗邻我故乡的一座名城,帝王故里与长寿之乡——钟祥。文字记载这座城的历史长达2700多年,春秋战国时它是楚国的陪都,战国后期为楚国的都城,三国时吴国在此筑有石城,两晋至明朝为郡、州、府治,明朝时为全国三大直辖府之一的承天府所在地。
它有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光辉灿烂的楚文化,更有着“石城湖上美人居,花月笙歌春恨余。独自楼台对公子,晚风秋水落芙蕖。”这般诗篇反复吟咏歌之的莫愁女和莫愁湖。
我说了这么多,并非夸耀这被明世宗嘉靖皇帝取“钟聚祥瑞”之意御赐县名的古城钟祥市。它不是我的故乡,哪怕地理位置上它与生我养我的小山村仅仅只相差不到一百公里。
明显陵的大气和神奇,莫愁湖的百岛俊秀、水天一色,黄仙洞的气势恢宏、波澜壮阔,是今日钟祥令人津津乐道的引人神往之处。但唯有诞生于此处的一道菜,令我念兹在兹,不能忘之。
这不到一百公里的地理位置上的差距,令我的故乡,人人都做这道菜,人人都吃这道菜,也人人都爱这道菜。且同钟祥城一样,无此菜不成宴席。

好了,请相信我,它的上场是配得上这般冗长的铺垫的。它是“皇帝菜”,是明代宫廷御宴上的美食上品,也是现今的“钟祥三绝”,其制作技艺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本身,也已列入《中国菜谱》。
它的名字叫蟠龙菜,又称盘龙菜,卷切,剁菜。
出身高贵,用料奢华的蟠龙菜是用鸡蛋,猪肉,鱼肉,葱姜和钟祥人民的智慧一起精心制作出来的。一道菜,“吃肉不见肉”,色泽鲜艳,肥而不腻,肉滑油润,香味绵长。
装好的蟠龙菜如一条黄龙卷切于盘中,热气腾腾的摆在宴席上活像一条真龙,正腾云驾雾一般。时人有诗云:“山珍海味不须供,富水清香酒味浓。满座宾朋呼上菜,装成卷切号蟠龙。”
公元1521年,三十一岁的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无子继位,张太后和内阁首辅决定,由近支的皇族,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此朱厚熜,即是明世宗,那位与蟠龙菜有着莫大关系的嘉靖皇帝。
彼时的朱厚熜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王爷,封地便是今天的湖北省钟祥市,抛开历史上一个由司礼监、皇室和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王府迎接其北上京城继承大统的一套严谨礼仪与规矩不说,民间对年少的朱王爷踏上帝王之路的过程进行了想象力丰富的演绎。
传说武宗去世后,太后同时诏回了安陆州(此安陆州便是现今的湖北省钟祥市)的朱厚熜,德安的寿王朱佑榰,卫辉的汝定王朱佑梈,三诏齐发,“先到为君,后到为臣”。这三个王爷,一个在河北的沧州,距京城仅几百里,一个在南京,也只一千多里,而我们的小朱王爷兴王府的所在地钟祥离京城三千多里。山水迢迢,山长水阔,沿途还要周旋于达官贵族们的欢送宴请,更要提防竞争对手的阻挠和刺杀,要想抢先进京实在是难上加难。
然而对皇位不抛弃不放弃的小朱在臣僚的妙计之下,假扮起了钦犯,坐上囚车,日夜兼程赶往京城。这样免去了路途上的许多麻烦,可小朱乃是藩王世子,自小娇生惯养,生活奢华,坐囚车容易,沿途吃糠咽菜却是真正困难。不食粗粮,又恐路人怀疑自己的身份,左右为难的小朱命令厨子做出一种吃鱼肉却不见鱼肉的菜,若做不出来,就要性命难保。
府中的大厨子詹多虽厨艺高超,可绞尽脑汁也做不出符合要求的菜。夜幕降临,做不出菜的大小厨子长吁短叹,詹多的妻子记挂丈夫,便带了蒸熟的红薯去看望詹多。烦躁的詹多正为了项上人头担忧,哪里还有心情吃蒸红薯,一摔手碰破了红薯皮,彼时詹师傅头内灵光一闪,一道流传于宫廷与民间四百多年的名菜,蟠龙菜便横空出世。
鱼肉剁成泥状调于鸡蛋清,蒸熟后裹上红薯皮,这“仿真红薯”好吃不腻,美味可口,小朱带着红薯坐着囚车,抢先进京登上金銮宝座成了嘉靖皇帝。
做仿真红薯的詹多自然是在京城为嘉靖皇帝继续做菜,升级版的“鱼肉剁成泥状调于鸡蛋清”再也不必裹上熟红薯皮,而是细细摊匀还要涂上美丽颜色的鸡蛋皮。这样裹好的长条形馒头状食物先上笼大火蒸熟,然后被詹大师的巧手一块块切成薄片码成盘踞的卧龙模样扣在碗底,在御厨的蔼蔼蒸汽中二度散发出它令人难以抵挡的香气,一路而来,揭开扣碗正式展现它的庐山真面目时,以它的色香味和吉祥昌盛的寓意真真切切地俘获了真龙天子嘉靖皇帝的心。由此被正式定名为“蟠龙菜”。

因它是盘踞在囚车中的真龙天子所吃的佳肴,又被称为“盘龙菜”。又因为人们习惯把它卷在菜盘子里切成一片一片的,所以俗称“卷切”。而至于得名剁菜,是因为那些鱼肉是剁碎了蒸熟才做成的,加上发明者是詹多,称为“剁菜”是取詹多“多”的谐音以纪念这位美食家。
道地的蟠龙菜选料精美,做工精细,做法极其讲究。
剁好的肉茸要用纱布包好,放在清水里漂,直到血色漂尽。再将肉茸和精盐、淀粉、葱姜等调料搅拌均匀。此时尤其要下功夫,据说只可顺着一个方向不停搅拌。吃过太多次的蟠龙菜,如出一辙的方法,同等的食材,不同的人烹调出来的,还是味道不同。有人说做菜是讲究天分的事情,如泡一坛水清皮红的萝卜,味道上也有天壤之别,将蟠龙菜吃得满嘴鼓啷啷的我,深以为然。
与帝王之乡的蟠龙菜师从一人的我的故乡人,不是这样将这道菜做成贵族做派的。它十分的接地气。那个小村子里人们叫它卷切,而再接地气的卷切,也是平常不易吃到的菜。
快过年的时候,母亲换上她洗得发白的围裙,在菜园子里挖她自己种的香葱,起好的生姜用沙子养着,防冻。父亲从集镇上称了红薯淀粉,母亲煮好了稀薄的粳米粥,猪肉剁碎,香葱和生姜剁碎,红薯淀粉用清水合着,调匀的米粥,也加了鸡蛋,不知道是怎样妙不可言恰到好处的化学反应,那肉少米面多的食材就被母亲揉成了一条一条的圆筒状,温顺而可喜的趴在蒸笼里。
它们同竹篾大蒸笼里的其他美食,排骨、粉蒸肉、鸡鸭,莲藕,馒头……一起在土灶上经受柴火的蒸煮。在我眼巴巴的凝望里,在我馋涎欲滴的等待里,在大铁锅水汽咕嘟的欢叫声里,变成热乎乎香喷喷的蟠龙。它们如同农家对小康生活由衷的珍惜,如同母亲对春节来临的庄严郑重,如同一种幸福的仪式,被细心地一条条码放在案板上。然后母亲端了那一碗用温水化开的红色颜料,用纱布蘸上一点,将鲜艳又喜庆的红从头到尾涂满卷切的一身。
很多年之后我都固执地认为,这世上不会再有比家乡的蟠龙更好吃的菜。那扎根于土壤的朴素的鲜香与醇美,那热腾腾的不可名状的温馨与安宁的幸福滋味。
它们是和那个热闹集镇里用淳朴乡音在腊月的末尾吆喝着“卖卷切红……卖卷切红……”的老人一起烙印在我的童年时期的。
它们是和年末寒冬的烛影,炉灶里冉冉舔动的温暖火苗,母亲套着围裙的年轻腰身,和那些村庄清明的远天,沉默的大地,夜半时抵达梦境的鸡啼一样烙印在我的少年时期的。
日子如流年,我是那个小山村里吃着蟠龙菜长大的姑娘,后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离开它,简单的快餐,食堂里的大锅饭,或者是宴席上隆重美丽却让人没有食欲的大餐,这些食物滋养着我在城市里奔波忙碌的身体,却并不能喂养我饥饿的灵魂。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如此迫切的渴望着这道并不通行全国的菜,数个独立中宵的夜晚,握着电话,打给母亲,呐呐半晌,只说我馋了,想要吃蟠龙菜。
我想念它,想念母亲,想念那个小山村。
那是一个与帝王之乡隔了不到一百公里的小山村,那里的人人人都爱蟠龙菜,每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蟠龙菜。
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生老病死,又或者酷暑严寒,春夏秋冬,那第一道端上来的菜必定是蟠龙。揭开盖碗,如龙安卧着的美食在热气氤氲中流淌着四百多年的鲜香与醇美,像我故乡的山川与河流,也像我故乡的父亲母亲,也像我,嘹亮婉转吆喝着卖卷切红的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