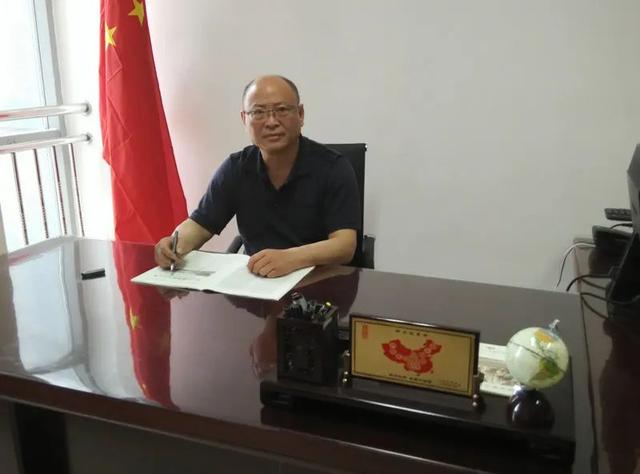我的幼年是在日本统治下的大连度过的。我爸爸少年时在烟台当纺织工人,上世纪30年代又到大连经商,开了一个小杂货店,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我们一家老小返回老家山东牟平林家口子村,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并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儿童团长。
跟妈妈回老家
爸爸的店铺在大连时,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住在仍是野狼出没的山区旅顺,住的很简陋,吃的更是粗茶淡饭。那时中国人吃饭只能配给高粱米和橡子面,吃起来又苦又涩,难消化,大便很困难。我们都不愿意吃,可妈妈总是无奈地说:“孩子,不吃怎么办?粮食都被日本人控制了。”
日本人在大连横行霸道,对中国人施行高压政策,欺压百姓。所以我们对日本人都很仇恨。但老百姓都敢怒不敢言,小孩看见日本宪兵就像看见恶狼似的,怕得要命。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在东北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更加疯狂地欺压百姓。在日本控制下的大连,中国人难以生存。我们一家走投无路,无奈之下,妈妈带着我们一家老小返回老家山东牟平大窑林家口子村。
这里是个偏僻的小山村。人烟稀少,交通极为不便。山塂薄地,主要作物是地瓜。人们世世代代除了种粮糊口,主食地瓜以外,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是以物换物。男人和孩子们夏天都不穿上衣,除了小脚妇女,男女老少夏天很少穿鞋子。我刚回老家的时候,对这样的环境有些不习惯。街道崎岖不平,下雨后到处泥泞难行。与街上的小朋友说话口音不一样,习惯也不一样。他们会爬树,光着屁股赤着脚,我好像不入群,感到有些隔阂和孤独。

1941年前后,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实行经济封锁。爸爸的店铺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也返回老家,弃商为农了。天长日久,我们逐渐适应了农村的艰苦环境和生活习惯。
记得我们家在林家口子村北台上,是个四合院。大门朝南,院子不大,分南北院,中间隔了一道墙。院子里有一棵大苹果树。砖瓦房,有东屋、西屋、南屋和堂屋。西厢房是平顶的,可以晒粮食,有人怀疑是八路的粮库。东山上的二鬼子也曾来检查过一次,没发现什么问题,也就无功而返了。后来听姐姐说是西村贺家庄一个汉奸捣的鬼。
我的姥姥家在离昆嵛山九龙池不远的山脚下。那里山深林密,到处是青松翠柏,郁郁葱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一支游击队经常在这里活动。神出鬼没,宣传群众,发展革命武装。
那时,我在姥姥家经常接近一些游击队员,知道他们是打小日本鬼子的,从内心敬佩和羡慕他们,暗暗下决心自己立志要当个像他们那样的游击队员。后来才知道,这支队伍的前身就是于得水领导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
当儿童团长
回老家不久,我7岁了,上了林家口子村小学。
学校非常简陋,设在本村林氏家庙里。一个老师,一个教室,两个年级复式教学,共计三十几名学生。教师是一位私塾老先生,是邻村窑口人,也姓林。上课时老师领读课文,老师念一句,学生念一句,反复重复直到下课。二年级上课时也是此种方式。我们到二年级时学校由村办转为政府办。学校正规多了。政府派来了校长。学生也多了,有了正规的课本。有了算术课,也有了儿童团组织。

电影《鸡毛信》剧照
我们的小山村有个传统习惯,每逢过年,正月里闹新春。我上小学时,村里有个小剧团。民兵大多是剧团的积极分子。剧团的道具很简单,就是几把二胡和锣鼓。小学老师自编节目。如“小放牛”、“花子拾金”、“土匪赵保元”等抗日歌剧。
记得我与一位女同学顾善英演“小放牛”。我演牧童手拿马鞭在舞台上边舞边对唱:“牧童开言道,大姐你细听,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在华中,抗日救国立下大功,全世界都闻名…….”一次,我们的小剧团在村民兵的带领下去养马岛演出,不巧与国民党孙进先部相遇。在民兵的带领下,我们趁夜色机智转移才得以脱险。
过了不长时间,我学会了这里的说话口音,好像又较土生土长的小朋友们更显得活跃些。因此,老师们都喜欢我,所以我很快就参加了儿童团。
记得学校校长本来姓曲,为了掩护自己改为姓林,叫林喜。他30多岁,高高的个儿,穿着一身粗布衣服,待学生很和蔼。除了日常上课以外,还经常给我们讲八路打鬼子的故事,教我们唱歌。
他组织大一点的学生学军事操练,每人自备一长木棍当枪,课余时间学步伐、学刺杀。有时星期六下午把学生拉到山里搞演习,分对立两方,我是一方的队长。由于演习成绩好,不久我就当了儿童团长。
我们这些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也经常参加当地民兵的一些活动。有时民兵派我们站岗放哨,有时派我们送信。

电影《鸡毛信》剧照
有一次,我们三个儿童团员奉命到10里以外的小山村去送次日开会的通知。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晚饭后,我们三个小伙伴碰头后,便带上通知出发了。
途中隔着一座大山,我们默默地走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一阵阵的大风吹动着树叶,发出唦唦的可怕的声音,心里确实有些恐惧。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吓得哭了起来,我就鼓励他说:“我们三个人一起你怕什么?要是姥姥村的那个小八路呀,他一个人就敢来。八路军可勇敢啦,你不是也想当八路军吗?想当八路军就要学习八路军。要是我们完不成任务,以后怎么当儿童团呀!”就这样我们手拉着手,互相鼓励,鼓起勇气继续前进。
我们终于翻过大山,将通知送达目的地,又赶在天亮之前返回。路上我们高兴地唱起儿童团之歌:“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员……”因我们胜利完成任务,回村受到了民兵队长的表扬。
小山村夜里经常开会,小学校长是主讲人。讲抗日形势:八路军百团大战,太平洋小日本打了败仗,小日本兔子尾巴长不了,等等。每次会前民兵、妇救会、儿童团、拉拉队互相喊口号。我是儿童团长,带领儿童团喊口号:“妇救会唱一个。”那边喊:“儿童团唱一个。”这边又喊:“民兵队唱一个。”儿童团这边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嘹亮的革命歌声此起彼伏。
自造小手枪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自造小手枪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43年秋,日本鬼子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经过我们村时宿营。我们村的东山上有伪军二鬼子的碉堡。这一带属于敌占区,但村里有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和农、青、妇、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晚上,八路军部队经常在这里活动。听说鬼子要“扫荡”,早就实行了“空舍清野”(就是把粮食和大牲畜都藏在山洞里)。青年和妇女都转移到山里隐藏起来,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
日本鬼子来了,既找不到人又搜刮不到粮食,很恼火。后来找到了小学校长,“叽里乌拉”了半天,校长也听不懂,只是摇头。鬼子手握指挥刀,一步步逼近了校长。校长无奈,只得把他带到我们家,找我爸爸,因为我爸爸从年轻时就在日本控制下的大连做买卖,懂点日语。在爸爸的多方周旋下才免去了一场灾难。
那天中午,一个鬼子军官在我家吃饭,他把一支手枪放在椅子上。我在一边两眼盯着这把手枪,羡慕得不得了,心想我要是有这样一把手枪就好了。我情不自禁地想伸手去拿,被爸爸发现了。他瞪大双眼,怒视着我,示意我到里屋去。进屋后,爸爸把我狠狠训斥了一顿,说:“你不但拿不成,还会给全村惹来大祸。”
捞不着摸真抢,从此以后我就整天琢磨着自己造枪。
有一天,我到姥姥家,找到八路军叔叔去看他的枪。可是,他的枪太大啦,是装在木盒子里的那种匣子枪,我扫兴而回。
后来,我又见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八路军叔叔,腰里别着小手枪,我伸手顽皮地去摸。八路军叔叔先是予以制止,然后把手枪里的子弹退出来,让我玩他的手枪。他高兴地问我:“小鬼,喜欢吗?”我说:“喜欢!”他又说:“等你长大了当八路军会有枪的。”我高兴极了,拿着手枪,摆弄来摆弄去,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真是爱不释手。
回家后,我凭着记忆,根据八路叔叔那支抢的结构准备材料。首先准备子弹壳、弹簧、铅块、木头和工具等。然后整天刀割锉磨,日夜赶制。经过一段时间,待自制小手枪有了雏型以后,又找民兵队长要造地雷用的炸药,然后用黄土做模具,化铅造弹头。经过了不知多少次的加工修改,我心爱的小手枪终于做成啦!小手枪可以打五六米远。我整天自豪地把它别在腰上,美得不得了,别的小朋友都很羡慕。
掩护地下交通员
1943年的冬天,牟平连续下大雪,昆嵛山一片白茫茫。
一天,姥姥村的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冒着大雪来到我家找我姐姐。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忽然听见大门外有敲门的声音。妈妈和姐姐立刻提高了警惕,一面让那位交通员平心静气地继续吃饭,一面要我赶紧把交通员的小布包和手榴弹藏到大院内的雪堆里。
我虽然不知道那位交通员和我姐姐的具体任务,但我感受到他们是在进行秘密的抗日活动。于是,我放下饭碗,赶紧跑到院子里,将那个小布包(那时没有背包,所有的材料都是用一块方布包起来捆在腰里)和手榴弹埋在苹果树下的雪堆里。因为雪在继续下着,一小会儿便盖住了痕迹。
这时姐姐不慌不忙地起身,一边往外走一边问:“谁呀?”打开大门,不出所料,迎面进来了四个提着长枪的伪军。我们都称他们为二鬼子。
这四个家伙瞪着滴溜溜的贼眼在院子里扫视了一番,又到东屋和西厢房的平台上转来转去,没发现异常,领头的二鬼子和另一个交头嘀咕了几句,就离开了。
后来我才知道姐姐加入了共产党,是地下党员,听她说这准是村里的汉奸给东山据点里的二鬼子报的信。从此以后,再有姥姥家八路军的地下工作人员来我家,姐姐就让我到门外佯装玩,去放哨,并嘱咐我:“一旦有情况,就敲东邻伯伯家的门,连敲三下为信号。”
那时,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保护了党的地下交通员。
联络同伴去当八路
1944年秋,日本鬼子大“扫荡”。我村东山上炮楼里的二鬼子也经常出来骚扰欺压百姓,因此激起了周边各村人民的抗日怒火。在一次本村民兵配合八路军游击队攻打东山上的鬼子碉堡失利以后,几个参加攻打碉堡的民兵秘密地离开了家乡,跑到了解放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当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立即产生了当八路军的念头。

电影《闪闪的红星》海报
于是,我与伯伯家堂弟秘密地策划如何去找游击队。经过多次商量,决定我先去姥姥村探听一下消息。当知道了八路军游击队(县独立大队)的行踪以后,便进一步做了走的准备。
首先是把我们的两人队伍扩大到四人,那两人也是我们儿童团员中最积极的。我们四人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决定立即行动。每人准备了一个本子一支钢笔。记得我的钢笔是在我家西院的大杏树下捡的。那时的八路军战士大多没有文化,所以要有钢笔和本子,要利用一切时间学习文化。
一天凌晨,村庄还在沉睡中,我们四个人便偷偷地离开了家,经过近半天的路程,跑到离家几十里路远的屯圈村,找到了县大队队部。
一位年轻的战士接待了我们,说明了来意后,那位战士就回到屋里去报告。不一会儿,一个背着盒子枪的年长者从屋里出来,我们心里猜他可能是个首长。他打量我们一番,然后对我们进行了问话和目测,还幽默地说:“先留下两个大的,你们两个小的(指我和堂弟)背不起枪来,回去长长再说吧。”
我们四个人一听,顿时都哭了。那首长又劝我们说:“哭鼻子还能当八路打鬼子呀?”我们央求了一阵,还是不行。我和堂弟无奈,只好告别了两个同伴回家了。
第二天,那两个同伴的家长找到我,问他们的儿子哪去了?我不敢透露实情,只好违心地说不知道。其中有一个同伴是独生子,爸爸早已去世了,妈妈哭得很伤心。后来直到区政府送来了军属证,才真相大白了。
他们两家门上也都挂上了“军属光荣”的牌子,享受军属待遇。他们家的地由村里派劳力给他们代耕。后来才知道那两位同伴,一位当了司号兵,一位当了通讯兵。我非常羡慕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