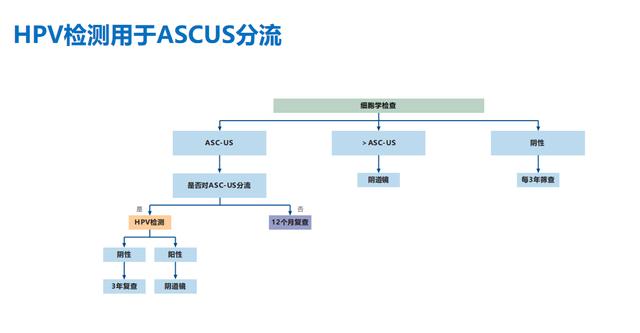王国维诗学的“境界说”以西方近代先验美学为思想基础,结合中国古代诗学传统,将西方美学引入古典诗,带来中国古典诗学思想的重大变革。

钱钟书在其著作《谈艺录》与《管锥编》中佐证了中西诗学共通的“文心诗眼”,即共通的心理、智慧和审美情趣。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集诗人、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于一身的学者,梁宗岱深受西欧尤其是法国诗学影响,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贡献巨大。

朱光潜的《诗论》聚焦于中西诗共同原理,关注“因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
——读江弱水《诗的八堂课》
在北京,你爬高楼一望,满眼还是高楼;在杭州,你在城里随便什么地方,只需稍微调整角度,便能与山相看。由此我产生一种职业病式的乱想:长居北京者写诗文,多少都有点儿苦大仇深的面孔;而居江南者,其诗文常有散逸的韵致,即便讲苦大仇深,也多些从容。在当代文学学者中,江弱水先生的学问和文章,很能代表江南风格。
有一次,我俩倚运河夜饮,微醺之际,就探讨文章句子长短的问题。我说:您也是个能尽量把句子写短的人。我们的谈论,自然别有所指,当代学院文风,大多粗鄙,许多看似复杂,实则简陋。江弱水早年从卞之琳诗艺入手,兼治古典诗歌、现代诗歌和比较文学,其写作素以杂糅古今中西诗学著称,与许多食洋食古不化,故作高深者不同,他在文章上亦有发明。他能够把学问的驳杂,挫磨为文章的精纯。当然,精纯既是学问境界,也是修辞功夫。南方文人,普通话大多学不地道,基本上得凭书面语感写作,文章因而多书卷气。比如,在这本《诗的八堂课》里,当写到张枣在德国馋中国菜的情态,作者还得动用《水浒传》中的现成话:“在嘴里淡出鸟的德国……”,看似轻易的一笔,却藏着修辞暗劲。可以想象,要让王朔或刘恒来写同样意思,该是啥样儿腔调。
抽丝织锦
重新续接汉语古典诗学的脉络
《诗的八堂课》最吸引人的,自是作者关心的诗学问题以及“抽丝织锦”展开问题的方式。前几日出差,在高铁翻阅《诗的八堂课》,忽而进一口深长隧道,闭目抬头之际,想起严复译的《天演论》。通过严复的译笔,英吉利人赫胥黎这本演讲与论文集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不但内容上幻化为纯正汉语古文,其目录体例差不多成了《文心雕龙》《文史通义》式的。看江弱水此书目录,亦采取了汉语古典论著常用体例。且看这八课题目:“博弈第一、滋味第二、声文第三、肌理第四、玄思第五、情色第六、乡愁第七、死亡第八”。若不读具体内容,我们多半儿会认为这是一本讲汉语古典诗学的书。江弱水多年前写《古典诗的现代性》一书想说的是,西方现代理论家费尽口舌给现代诗归纳的“现代性”特征,在汉语古典诗里照样能找得着。到这本书,他表露了进一步的想法:这些大多来自古典诗学体系的关键词,也具有普遍的命名能力,它们可用来总结中西古今现代诗的一些基本特征。
作者这种思路,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学研究中很重要,却有些孤绝的一脉。王国维、钱钟书、朱光潜、梁宗岱等近现代大家,都曾试图用中国古典诗学歌观念,来理解西方诗学。比如,梁宗岱以中国古典诗学之“兴”,来理解西方诗学之“象征”,朱光潜用“阴”与“阳”、“南宗”与“北宗”,来比附德国古典美学之“崇高”与“秀美”……可谓两个范例。如此比附,自然难免有不吻合处,但借此打开的视野,却十分开阔。无奈在过去的这一百多年,总是西风压倒东风,在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所有领域,总是新词胜旧词——王国维早就感慨过新名词大量涌入汉语的基本现实。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激荡,我们是否能重新续接这一脉络,建构一套以汉语古典诗学观念为“原子核”的普遍性诗学观念?读毕此书,我欣喜地看到,作者非常用心地致力于这一尝试。
谈诗,自然要从如何写开始。作者巧妙地借“博弈”一词包含的两层含义,来辨析写作中的“灵感”派与“技艺”派,绘声绘色地描绘出“赌中妙手”与“棋中圣手”的种种情状。编织这一课动用的观点和材料,自然是遍采古今中西之阙文遗韵,错杂熔铸而成文。后面每课,也照此法徐徐展开。如何把众多“原料”“切碎调匀”,再“焖”出独自的味道?这是最体现作者文思和笔力之处。可以看到,笔者发现了古今中西诗歌之间的众多“契合”:在分属于王羲之、陈子昂、杜甫、司汤达、里尔克、瓦雷里的诗句里,作者发现了共同的“形而上学时刻”;在诗经、楚辞、汉赋、陶诗、红楼梦,与莎士比亚、斯宾塞、波德莱尔等的作品中,看到了关于情色的相似语言编码方式。在热烈的“契合”中,不时会涌出这样的诗学妙谛:“喜欢锤炼的诗人是健身狂,忍受不了一点多余的脂肪,非在身上凿出六块腹肌来不肯罢休。”“如果没有玄思,一首诗很难从有限上升到无限,空灵不起来;但如果没有情色,其实也很难沉醉于纯粹的现实中,因为最切近现实的就是肉身。”
诗的精神
世界黑夜中向存在和语言的突围
对作品的细读,是此书另一特色。除了对古典诗词吐香缭绕的评点,作者也分析了许多现代以来的诗,比如鲁迅、卞之琳、冯至、纪弦、郑愁予、张枣、杨炼、欧阳江河、于坚、朱朱、黄灿然、卢卫平、泉子等的作品。作者治现代诗数十年,因此无论对所评诗作的选择还是阐释,看似信手拈来,实际却四两拨千斤,每有所论皆能有新见。比如,他对冯至十四行诗、鲁迅《野草》中生死主题的论析,十分令人叹服。再比如,他对下半身写作的评价:“下半身写作严格说起来只是社会讽喻诗。身体写作则是一种写作政治,是对自己身体的权利进行宣谕,把身体当作对抗世界的根据地。在语言配方和身体编码方面,它们都乏善可陈。”
在作者的行文中,显然有他的偏爱,比如,对卞之琳和张枣诗歌的推崇。他坦言:“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人中,一前一后,有两位顶尖的技巧大师,一位是卞之琳,一位是张枣。”在文学批评这个行当里,有所偏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每逢谈论所钟爱的诗人作品,就如恋人絮语,不但自己陶醉其中,也最能感染读者。在全书八课之中,我们可以随处见到关于卞之琳和张枣的品藻文字。
作为张枣的学生,我每读至相关文字,自然别有会心。在“滋味第二”里,写到了张枣爱吃的细节种种,我也是见证人之一,张枣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期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吃的佳话。在“声文第三”里,作者着力分析了张枣《父亲》一诗在音韵上的细致与精确,他将诗中的音响“暗哨”逐一明察,可谓心细如发。关于古典诗的音乐性,有现成技术标准,而汉语现代诗则尚未有类似标准,学界虽有“内在韵律”的讨论,至今未成技术性共识,此书里的分析,堪称这方面的重要尝试。
当然,探寻白话诗的音响特征,的确是个不易讨好的活儿。如作者所感慨的,白话诗的声音设置难上加难,比杜甫周邦彦难度更大;而由这种难生出的“巧”,也就隐藏得深。比如就张枣《父亲》一诗而言,全诗倒数第一行和二行文字之间的空白,读起来就有一种特别“巧”的音响效果。诗人这首诗,写的是1962年的父亲,而张枣本人亦是1962年所生。三个“转身”之后一行空白,末了以“变成了我的父亲”单作一节收尾。这个特别的空白,既是阅读上的短暂静默与休止,也是一个意义暗示。由此我们得知,诗人既在写父亲,也是写自己的起源。
上面对此书短斤少两的评介,乃是为了指出:作为一次杰出的诗学阐释尝试,作者以这八个诗学关键词为枢纽,串通古今中西,可谓四通八达地重新编织了一些基本诗学问题。显然,这是一个可以无限展开的工作,如果请作者再讲上八课,他肯定还能同样精彩地发明出别的诗学枢纽来。按已故意大利作家艾柯的话说,今天是个矿物记忆(硅)的时代,全世界都被装进一个深不可测的网络,可谓“天下归一”;而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界,“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得一察焉以自好”(《庄子·天下》),依然是常态。《诗的八堂课》的写作,可谓一次拆除壁垒,打通关隘的试验,无论其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作者的初衷,但一字一句都饱含着“诗的精神”,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诗的精神是在世界黑夜中向着存在和语言的突围。”顺着作者的文路,我们的确可以进入更宽阔的诗思天地。
□颜炼军(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