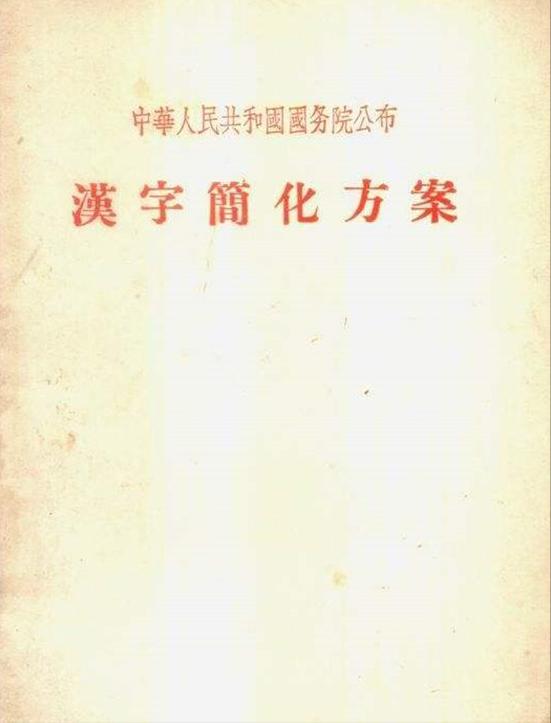《说文解字》中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生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巫师、术士。

“独尊儒术”,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可知它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必然,其内充满一定的偶然性。所谓偶然,包括巧合、某些事件影响及君主的临时起意。
儒学历史久远,经过数千年发展,已成为中国人的正统思想。历代历朝中,儒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充满着坎坷与争议。新世纪的今天,儒学有了不同的面貌,正在朝着“复兴”的方向发展。无论是把儒学当做信仰,还是对其抨击不屑,都不可否认儒学的影响力。
不知何时,关注儒学的人愈来愈多,尤其是当下,儒学更是成为了一种风潮。

此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儒学如此受到关注?
首先,要明白儒学的特点“仁德思想”,儒家所倡导的思想无疑有利用国家稳定,教人从善,便于统治者治理国家。简单概括,即:儒学只是稳固统治的工具,而独尊儒术,只是汉武帝加强皇权的政策。
众所周知,独尊儒术源于西汉,由董仲舒提出,受到汉武帝赏识并全国推行。汉武帝的目的很明确,即利用儒家主张,达到封建思想统治的目的。若准确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我们需要先看三件事,与三个人有关。

秦始皇“焚书坑儒”——史书中详细记载了此事缘由,并非秦始皇憎恨儒学,而是另有原因,且看背景:两千多年前,古人平均寿命不高,哪怕是千古一帝秦始皇,依旧抗衡不了岁月的力量。作为一统天下的君主,秦始皇自然不甘就此死去,便痴心寻找长生不老之法。
当时,秦国有许多方士受命寻找长生之方,可这世间哪里有什么长生的方法,这些方士知道无法完成任务,选择了半路逃亡。秦始皇大怒,命地方御史调查此事,这御史抓来儒生审问,不料这些儒生并不配合,相合告密。
秦始皇盛怒之下,圈地抓人,共逮捕四百六十余人,活埋于咸阳。事后,朝廷历数众儒生罪状,昭告天下。《儒林列传》记载:秦始皇焚书后,为了树立威望,对天下的儒生进行灭绝屠戮。实施过程是先利用官职引诱儒生进入咸阳,而后,再以“种瓜之计”将儒生骗至坑杀地点,进行活埋。

显然,秦朝的“坑儒事件”是经过精心预谋。
以上两段有关“坑儒”记载,存在诸多不同,如人数差异、动机不同,说明“坑儒”存在疑点,这也是后世广泛争议的地方。
有观点认为,秦始皇并非罪恶之人,所杀四百余人与项羽坑杀四十万降军相比,可谓是仁慈至极。另有观点称,秦始皇坑儒次数不止一次,学术界普遍认为至少两次以上,如果秦室进行秘密活埋,或许“坑儒”受难者远不止四百余人。
《秦始皇本纪》对“坑儒”过程的描述仅有四字,即“坑之咸阳”。而另有部分史书,却是详细记载了坑杀全程,甚至,连音容反应都描述的极为真实,仿若目睹一般。目前来看,过于翔实的细节,皆有作者的主观发挥,真实性存疑。

随着现代学者对历史的研究,秦始皇“坑儒”之事似乎有了新的发现。有学者认为: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确实有过焚书行为,但是,并未进行“坑儒”。所谓“坑儒”实则为“坑方士”,即:遭到活埋的四百余人皆为方士,并非儒生。
这种说法拥戴者众多,笔者觉得有这种可能。
回顾历史,秦朝建立后,儒家在秦代的地位显著提高,说明秦始皇并未刻意打压儒学。哪怕是“坑儒”之事发生后,秦代儒家的发展并未受较大影响。其实,“坑儒”实则“坑方士”此观点历代皆有提起,如:清代学者梁玉绳便称“余常谓世以‘焚书坑儒’为始皇罪,实不尽然。……其所坑者,大抵方伎之流,与诸生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显然,秦始皇杀的极可能为方士,那为何秦始皇会背上“坑儒”的罪名,其实与各地的政治不同有关。儒家倡导仁德治国,而秦始皇推行法理治国,在儒家眼中,法律是不近人情的,刑罚是残暴冷血的,因此,儒家著书宣扬秦始皇暴政治国,这便有了“暴君”之名。秦始皇并非完美,执政期间确有过失,但“坑儒”一事,属实为儒家强加的罪名。

战国时期,“儒”的含义极其广泛,可将其当做孔孟学派的弟子,也可泛指学识渊博的文人。如庄子,就有人称他为“小儒”。“儒”字不同的搭配会有不同的意思,孔子即特意强调,“儒”可分“君子儒”、“小人儒”,重点不在于“儒”,而在于君子与小人之分。荀子亦强调称:“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对于违背儒家思想的人,可以“贱儒”称之。
故而,后世不必在“儒”字上纠结,史书中的“儒”并非为真正的儒学传承者,或为“俗儒”或为文人,或为方士。“坑儒”一事由方士欺骗引起,秦始皇就算报复,也会选择与坑蒙拐骗相近之人,而非饱读圣贤书的儒士。

汉高祖刘邦溺儒冠——刘邦轻贱儒生,这是自古皆知的事情。至于他为何不喜欢儒生,史料中并未进行记载。有观点称:“刘邦不喜欢读书。”其实,这些都是片面说法,没有足够的依据。
与刘邦同时期的项羽,虽说是武夫形象,但是,不代表他没有读过书。相反,出身贵族的项羽,饱读圣贤书乃是必修课,而刘邦出身普通,中年时期还只是亭长身份,可谓是大器晚成的典范。
刘邦是否文盲,历史并未记载,不过《高祖本纪》曾载:“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意思为:刘邦是经过考试,方才当任亭长一职,且当时要求“以吏为师”,这也说明刘邦还是有些文化基础的。

所以,若说刘邦不喜欢读书人,这点显然说不通。
像他身边的萧何、张良、陈平都有文化基础。既然如此,民间为何盛传刘邦不喜儒生。归根结底,是因刘邦不喜欢儒家那套繁文缛节,而非抵制儒生。当初郦食其投奔刘邦,刘邦正在屋内洗脚,听闻有儒生来见,当即爆粗拒见,称郦食其为“竖儒”。
此话被郦食其听闻后,当即不悦,本身他性情高傲,怎会忍这般羞辱。当下,郦食其推门而入,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不曾想,刘邦不仅未生气,反而顿生赏识,立刻拜郦食其为广野君。

另一个事例还有叔孙通。
当时他见刘邦时,身穿为儒家服装,刘邦看到面露憎恶。意识到不妥后,叔孙通换下儒服,另穿楚制短衣,刘邦这才面色舒展。可知,刘邦厌恶的并非儒生,而是儒家那套缛节繁饰。世人常说,叔孙通是儒家败类,为了奉迎汉王,寻求前程,败坏儒家声誉。
其实,这倒有些冤枉叔孙通了,早年叔孙通在秦朝做博士,他见秦皇残暴,便逃出投刘,这应当为顺势而为,明智之举。叔孙通对儒家的利弊看得十分通透,并利用这点,助刘邦设计朝仪,去糟取精,重现孔圣礼乐精髓。
刘邦在看过他设计的朝仪后,不禁盛赞:“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窦太后使儒生刺野猪——西汉窦太后喜欢黄老之学,有次,她召来朝中儒士辕固,要向其请教一些时期。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后竟然“请教”一个儒士,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难不成另有目的?
当时,儒家在汉代的地位很微妙,朝内有不少学儒的博士,像辕固就是汉景帝身边的博士,但朝政的实际控制者窦后,偏偏信奉黄老之学,这些儒士自然不敢过于宣扬儒学。当日,辕固到来后,窦后当即发难,说了不少轻视儒学的话。
辕固也不甘示弱,当即反驳:“这是妇道人家的见识罢了。”

要说辕固胆子也是挺大,说这么一番话,这不是暗讽窦后见识短浅嘛。窦后听后,面色铁青,命辕固与野猪搏斗。堂堂一个朝中儒士,竟然要与野猪搏斗,如果传出去,岂不是令人笑掉大牙,儒学声誉将就此一败涂地。辕固也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得知消息的汉景帝及时赶来,化解了这次危机,否则儒家名声将受到严重影响。
通过以上三件事,可看出儒生的地位十分被动,这种被动一直维持至汉武帝初期,直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儒家才是真正拥有主动权,迎来扬眉吐气的时刻。其实,此时的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

上文所载的三件事,只是儒学与权力擦出的火花罢了,它见证了儒学的发展历程,唯有了解其本质,方能感受儒家思想的玄妙。
不过,后世对于儒学的争议仍未终止,独尊儒术的出现,尽管提升了儒家的政治地位,使儒学成为西汉的正统思想,但在一些人看来,独尊儒术的作用言过其实,被后世儒生渲染夸大。换言之,儒家在武帝之前,被压迫千余年,好不容易靠“独尊儒术”翻身,自然会被大做文章,刻意夸大作用。
两种说法争论至今,各有说法。
参考资料:
『《说文解字》、《儒林列传》、《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