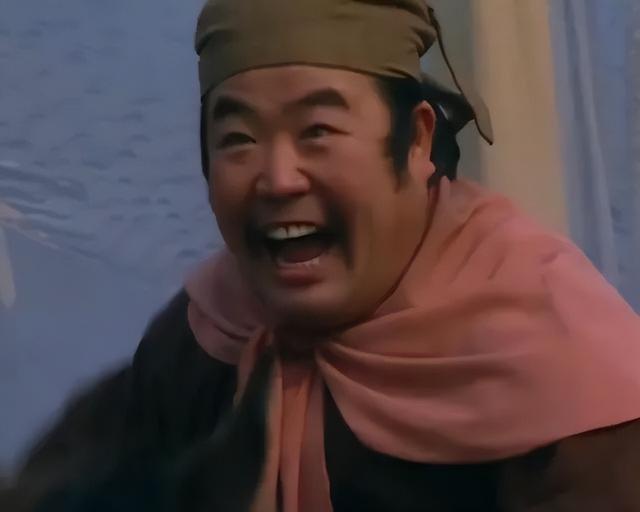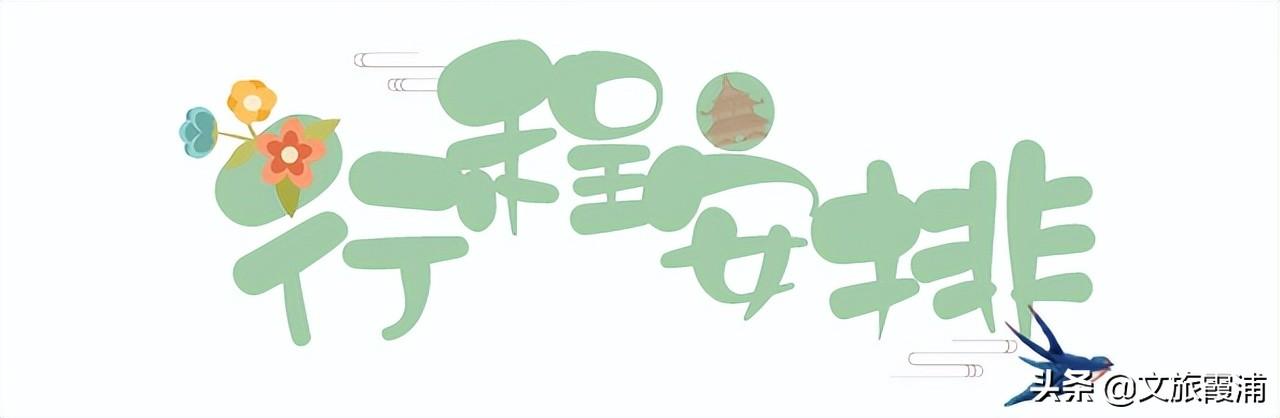当年读金克木的《谈外语课本》,对他提到的一个朋友非常感兴趣“我有个朋友学过不止一种外语,而且学得不错他常对我说,自己脑筋不灵了,学不好什么学问了,只好学点外语,因为学外语不费脑筋”对费尽心思而学不好外语的人来说,会觉得这话有显而易见的凡尔赛成分,进而想追问,“谁敢夸这海口?是说胡话还是打哑谜?”这个哑谜,金克木自有解答,有心人可以去翻看相对于这个哑谜,我更想知道的是,说这话的究竟是何方高手?,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优柔寡断的将领?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优柔寡断的将领
当年读金克木的《谈外语课本》,对他提到的一个朋友非常感兴趣。“我有个朋友学过不止一种外语,而且学得不错。他常对我说,自己脑筋不灵了,学不好什么学问了,只好学点外语,因为学外语不费脑筋。”对费尽心思而学不好外语的人来说,会觉得这话有显而易见的凡尔赛成分,进而想追问,“谁敢夸这海口?是说胡话还是打哑谜?”这个哑谜,金克木自有解答,有心人可以去翻看。相对于这个哑谜,我更想知道的是,说这话的究竟是何方高手?
金克木的文章也有一种“互见”法,此处没提名字的人,有时候会在彼处出现。在自问自答的《如是我闻——访金克木教授》中,他就说出了这个朋友的名字:“在沙滩北大认识了沈仲章。他是北大物理系毕业,跟刘天华学过音乐,在刘半农的语音乐律实验室工作,对学外国语有兴趣。英文从小就会,还学别的。他说自己现在头脑不行,只能学学外语,因为学外语不用脑筋。”从这段话看,沈仲章不但会多种外语,还具备多项技能,他的人生究竟是怎样的呢?今幸有其女公子沈亚明所著《众星何历历:沈仲章和他的朋友们》,让我们的好奇得到了相对满意的回应。
沈亚明自小跟随父亲,听他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在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1966年至1973年间和1985年,沈仲章又有两段时间相对集中讲述自己的经历,沈亚明和其他协助者都有录音并做了记录,因而留下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尤为可贵的是,作者的写作并不只是口述自传,而是结合父亲的经历,追查甚至考证各种材料,复原当年的各种历史场景,勾勒出了一个大时代中卓越人物的面影,让我们鲜活地感受到了这位名声不彰者的闪耀之处。
沈仲章生于1905年,他开始学外语,其实只是出于一个年轻人无来由的上进心。“父亲少年时在上海的一家洋行当学徒……他的英语最初是下班后,从办公室‘字纸篓’里捡出破纸片自学的,年少时不知天高地厚,听说读写都敢试。”后来,这个连小学毕业都“不算”的年轻人,凭借自学来的英语,居然考进了唐山大学,并于三年后转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的这段时间,沈仲章熟悉了法语和德语,并学过梵文、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据父亲学生时代老友说,父亲可以‘对付’十几种(外语)”。谦虚的沈仲章说,“年轻时好奇好学,多‘碰’了几种外语。不料传闻在外,有些年少气盛的学生不服气,会出其不意地拿些较偏僻的语种来考他。他同样年少气盛,也不服输,好在印欧语系中的许多语种相近相通,连蒙带猜,竟译个八九不离十,于是名气就更大了。‘盛名’之下,父亲不得不‘真’的多学一点儿”。
据沈亚明推测,沈仲章能用于对话和阅读的外语,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世界语和马来语。其他涉猎过的语种,包括瑞典语、日语、八思巴文和斯拉夫语系的若干语种,另外还有阿尔泰语系等。虽然数量之多已足够让人吃惊,但大概仍然不是全部。沈仲章“碰”过的不少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应该跟金克木相似,都是以用为先,“要用什么,就学什么,用得着就会了,不用就忘了,再要用又拣起来”。书中提到一个细节,尤其让人感佩:“父亲晚年又‘碰’过日语,起初我家多人一块儿开始学,我浅尝辄止,父亲比我学得久也学得好。那时父亲学日文的促因之一,可能是友人罗传开有不少日文资料,介绍西方音乐的较新发展。”
我有点怀疑,沈仲章这种上进心和以用为先的方式,也正是他娴熟各种技能的原因。尽管手头的这本书主要写的是沈仲章跟北平学界的师友之谊,包括跟陈寅恪、胡曲园、周祖谟、徐森玉、钢和泰等人的交往,从中就已经能够看出沈仲章的多项才能了。除了上面的多种外语翻译,沈仲章还曾从刘天华学二胡和小提琴,在刘半农的语音乐律实验室工作并随其到塞北调查方言民俗,协助欲把中国戏剧推向西方的洪涛生筹建剧团,参与斯文·赫定将查勘队所获文物带回瑞典研究的商讨……以上所说,只是沈仲章年轻时各种活动的一部分,这里不妨再提一事。1984年,做过居延汉简研究的劳榦致信沈仲章,感谢他抗战期间秘密救护汉简的工作:“在当时香港的局面已经十分危险,在人手不足情形之下,把工作匆匆中结束,真是好不容易有此成绩。……至于我所经手印出的,还是您从香港寄来的反面照片再转成正面。”
我们当然可以把以上多姿多彩的活动,看成一个年轻人因精力无限而做出的选择,那后面提到的两件事,就不能用精力来解释了。新中国成立后,沈仲章几乎倾其积蓄购买了米友仁《云山墨戏图》和黄公望《天池石壁图》,却并没有据为己有,只自己拍了两张照片留念,便无偿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仍会把自己有限的补助款留出一部分,以备从事古琴者中有“更需要”的人和事。如此行为方式,大概只能用品性来说明了。书中附有林友仁、刘立新撰《沈仲章生平纪略》,提到一个细节,或许可以旁证以上推测:“他收购的大量珍贵书籍,没有一本盖上‘沈仲章藏书’的印章。他认为‘书,不是藏的,而是要用的’。对于研究者,他从不吝啬,但他决不能容忍这些用以学问的书被埋没,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非要强调个人选择,那或许可以说,沈仲章的多种才能,是因为他不试故艺。说得更具体些,其实就是他以“做事”为先的态度:“父亲回避名气地位,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做事’。父亲一再言及,有了名气地位就麻烦了,人事方面就复杂了,‘我就不能真做事了’!”不止如此,除了“生性不在乎名分,只求把事情办好”,“综观父亲的一生,不声不响,尽心尽力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不胜枚举”。或许这就是沈仲章夫人讲的,他一直对人慷慨,对己节俭。书中刊出的一张四人照片里,另外三个人均已站好,只有设置相机的沈仲章立足未稳,“父亲乐于为别人服务,总把自己放在最后……以至‘留影存照’时,‘本人还没来得及站好’”。这也就怪不得平生好友金克木说他,“一生好交朋友,却从来不说自己的事。他做的事只有他的好朋友才知道”。
这样性情的人,自然容易在每个可能的节点上,都是虽不可或缺但一直待在角落里,因而不为人所知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读沈仲章的生平不难发现,如此一生实在难以归到某个领域或某个类别,大概只能照沈亚明说的,他“one of a kind”(自成一类)。这些自成一类者的存在,挽救了诸多濒临消失的东西,弥补了不少大事的漏洞,在某些时刻温暖了人的心,让世间少了些遗憾,可以供人从容走过。这样的人,当然不应该被遗忘,甚至值得更深入地考察,以便留下更多值得回味的东西。书的献词引希罗多德的话,“但愿人们之所历不随日久而消失……所作不因无闻而湮没……”。那些动人的故事,将在不断的推敲和讲述中重新栩栩如生。(黄德海)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