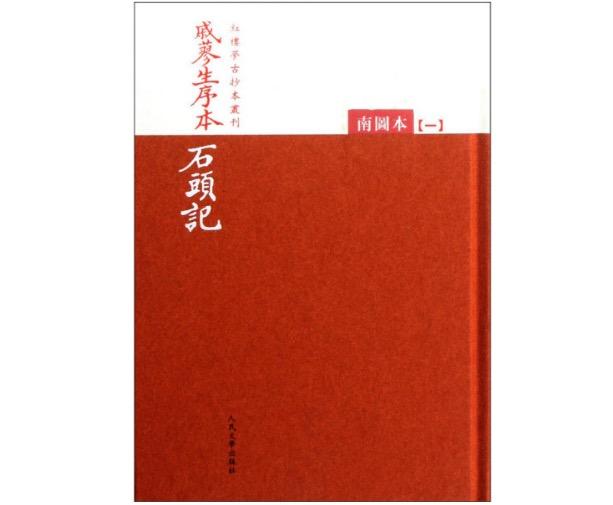描述汉唐时期的书籍,需要对书籍形态进行概括。翻阅文献学、书籍史、出版史等领域的论作,会发现,所用称呼五花八门,常见的就有十数种:“抄本””纸抄本”“写本”“纸写本”“卷子”“卷子本”“纸书”“写本书”“手写本”“手抄本书”“纸卷”“古抄本”“古写卷子本”“卷子写本”等等。其中,以“抄本”和“写本”最为常见,使用起来却也最为随意。
“抄本”、“写本”概念在文献学领域中比较常见,文献学形成于20世纪初叶,是书籍史、出版史的重要学科倚傍,其基础是传统的校雠学、目录学和版本学。对于“抄本”和“写本”的辨析,笔者曾寄希望于文献学,但翻检20世纪以来的文献学知名论作,却发现,对于这两个概念,文献学界亦莫衷一是。其主要观点大致可总结如下:
“抄本”与“写本”不仅指纸书,还包含了简册和帛书。此为现代人的新理解。在传世文献中,“写本”“抄本”均指纸写成的文本,简册、帛书未见有称为“写本”“抄本”者。但20世纪以来的文献学领域中,简册、帛书被包含进了这两个概念中。
1940年代,曹伯韩《国学常识》称:“自唐以前,书籍的流传,全靠抄写。写本的书籍又分两个时代,周秦汉为简册时代,隋唐为卷轴时代。”[1]曹伯韩认为,“写本”包含简册、帛书和卷轴纸书。
1980年代,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其《中国文献学》中,亦持此观点,他将雕版印书以前的统称为“古写本”[2],且明确以“写本”和“传抄本”指称帛书与简册:“汉初用以抄写书籍的材料,不外竹简和缣帛……出土帛书有十多种古籍,其中以《老子》为最重要,并有两种不同的写本。……上面但就西汉初年的传抄本帛书《老子》来看,便存在这样多的问题。推之他书,莫不如此。足以说明汉代流行于社会,保存在朝廷的图书,是一大堆丛杂、散乱、编次不同,没有篇题、错字很多的传抄本。”[3]
将简册、帛书称作“写本”“抄本”,显然是20世纪以来学界的一种新提法,但也并非通行观点,如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就不认同,他将“写本”“抄本”仅看作是纸本文献的版本类型。[4]
“写本”与“抄本”基本同义,但使用于不同时期。这一思路继承自传世文献。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将雕版以前的书称“写本”,雕版以后的称“抄本”:“广义的版本包括没有雕版以前的写本和以后的抄本、稿本。”[5]
陈宏年《古籍版本概要》认为“抄本”与“写本”通用,但习惯上,以唐代为界,分用二者:“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的书本。……习惯上,人们把唐以前抄写的书籍称‘写本’,唐以后抄写的书籍称‘抄本’”。[6]
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将明清时期的手抄书称“抄本”,之前称“写本”,有“唐写本”“宋写本”“辽写本”“金写本”“元写本”之称:“我国的写本、抄本书,在保存古代文献方面,曾起过重大作用……唐人写本,现存的只有唐卷子本和唐人写经,为数无多。宋代写本尤其少见,……辽代写本,只有山西应县发现的辽藏残卷,金代写本未见任何实物,元代写本……盖传世绝少。抄本中比较常见的是明抄本和清抄本。”[7]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将“写本”视作宋和宋以前手写传抄的书籍。宋以后传抄的书籍称”抄本”:“写本: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入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是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若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或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8]“抄本: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9]
以笔者所见,目前学界以李致忠先生对“写本”“抄本”的分析最为全面和认真,他试图从学理意义上将“写本”和“抄本”区分开来,也比较清晰地阐述了文献学界的常见观点。但如对照传世文献,就会发现,其表述是有问题的。首先,“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这一判断是基于宋代以后人们的理解,传世文献的梳理告诉我们,唐以前,“写本”并非书籍的名词性代称,那时的人们对书籍的称呼,或直接采用书名,或统称“文籍”“集本”“书”“坟籍”等,“写本”多为动宾形式,是“抄写本子”之意。真正将“写本”作为名词指称书籍,是宋以后的事。李致忠此论采用的是宋以后人的看法,而非汉唐时人的理解;其次,李致忠指出,“写本”是“手写传抄的书籍”,“抄本”是“据底本再行传写”。但“写本”同样也是据底本传抄,这与“抄本”有何区别?而且李认为“除了写本、稿本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似乎“写本”又与传抄无关。此类表述显然矛盾重重。但李致忠所言“写本”的时代早、与刻本相关等观点与传世文献所呈现出的特征是吻合的。总体来看,李致忠所论之“写本”“抄本”的区别,还是集中于使用时间段的不同。
上述陈、王、洪、李诸先生之论,均以为“抄本”与“写本”应分时期使用,这一点,可视为文献学界的共识,但在具体的分期标准上,他们却明显存在分歧:或以宋代为界,如王欣夫、陈宏年;或以元代为界,如李致忠;或只将抄本归属于明清,如洪湛侯。
上引诸说,均来自专论过“写本”与“抄本”的文献学著作,各家显然看法不一。如果再延伸及其他文献学类论作,会更难发现规律。例如,从分期使用的角度,一般认为,汉唐属于“写本”时代,对于敦煌文献的文本,“敦煌写本”几乎成为代称,但在当代敦煌学研究中,“写本”并非专用。知名著作如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书中“写本”“抄本”并用,如“列一四五六法忍抄本王梵志诗”;“伯三七二四王梵志诗写本”,同为敦煌文献,为何一用“写本”,一用“抄本”, 作者未作解释。另外,对敦煌文献中同一文本,学界的表述并不一致,或称“写本”,或称“抄本”。以《文选集注》为例。清末,董康在日本发现了《文选集注》一书的残卷。1918年,罗振玉整理出版了《唐写文选集注残本》;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勋初辑录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2007年王立群撰文《从左思<三都赋>刘逵注看北宋监本对唐抄本<文选>旧注的整理》[10]。同为《文选集注》,罗振玉用“唐写”,周勋初用“唐钞”,王立群则用“唐抄本”。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使用上的含混性,在作为高校文献学教材的《文献学概要》中,“抄本”与“写本”的关系甚至出现了矛盾表述。一方面,“抄本”成为了“写本”的附属:“写本一般又分为:手稿本、清稿本、抄稿本、影钞本、抄本”[11]。另一方面,在具体解释中,“写本”与“抄本”又成了平起平坐的关系:“写本,又叫抄本。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固然都是写本。印刷术发明以后,仍以写本居多。宋以来,印刷术普及了,写本才逐步减少,但其绝对数量仍然相当大。……在印刷术高度普及的明清及近代,写本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部头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就只有写本。这一时期著名的藏书家都极重视抄本。” [12]“抄本:即一般手写本,其中往往有特别罕传的书籍。”[13]
综上所述,文献学界对“写本”与“抄本”的理解,主要基于版本鉴定的角度。尽管有所辨正,但显然还存在不少分歧。与传世文献相比,文献学界给了这两个概念新的时间段界定,或前提至简帛时期,或以宋、元甚至明清为界分用两者。而在实际应用中,又并不完全遵从上述规定,较多随意而为。
参考文献
[1] 曹伯韩《国学常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1-53页。《国学常识》一书初版于1943年,1948年出第二版,2010年,中华书局据1948年版校订重印。
[2]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3]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0-201页。此书最早于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另外,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中也提到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将之称为写本:“即以《老子》而论,已有两种写本。一本写在汉高祖时期之前,一本写在汉高祖时期之后。由于历时久远,文字时有缺脱。”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5页。
[4]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5页。
[5]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5页。
[6] 陈宏天《古籍版本概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7] 洪谌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3页。
[8]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年,第226页。
[9]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年,第226页。
[10] “本文暂以《文选集注》本保存的左思《三都赋》刘逵注作为考察对象。”王立群《从左思<三都赋>刘逵注看北宋监本对唐抄本<文选>旧注的整理》,《河南大学学报》2007第1期,第115页。
[11]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6页。
[12]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5页。
[13]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6页。
封面图片源自网络
责任编辑:龙亚莉
作者简介
陈 静,山东大学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教授。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古代出版文化;近年来关注女性与出版问题。出版有《唐宋律诗流变研究》《图说中国文化·艺术卷》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所撰传统文化普及类作品输出版权到韩国。出版六家
—出版人的小家—
出版六家公众号的所有内容,均为原创。
未经许可,请勿使用。
欢迎合作、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