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部音乐剧被誉为百老汇世纪之交的惊喜,
创作历程本身即是一场翡翠色的探险!
“The process of the adaptation is an epic itself.”
—— Marc Platt
文/wicked
《纽约时报》称它是“百老汇最大的票房炸弹”,《泰晤士报》认为它是“继《剧院魅影》后最为恢弘的巨制”。自2003年抢滩登陆百老汇以来,揽下包括美国托尼奖、英国奥利弗奖在内的一百多个国际大奖,先后在十四个国家进行巡演,超过五千万人次观看,至今影响力仍经久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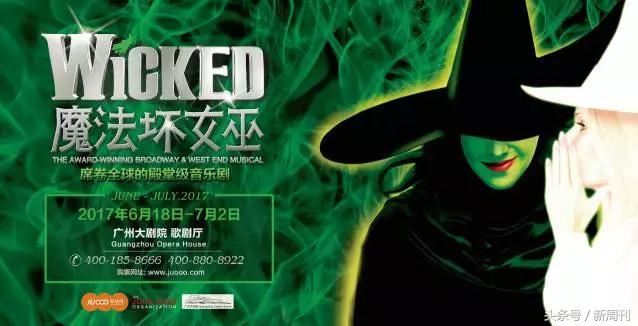
音乐剧《魔法坏女巫》(Wicked),灵感源于L.弗兰克·鲍姆的原著《绿野仙踪》,该作在美国称得上家喻户晓的国民故事,影视制作公司争相将其搬上荧幕。音乐剧版则采用了不同于正统叙事的个人视角,以解构和重述的手段,再现了奥兹国那段不为人知的往事,为臭名昭著的“西方坏女巫”翻案。人性的善恶边缘、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政治角力与话语权等命题,在看似轻松猎奇的情节里一一铺展开来。
【“铁三角”的聚首】
当大多数的孩子随桃乐茜一起,在《绿野仙踪》里展开新奇刺激的探险时,格利高里·马奎尔却在思考这部童话背后的道德内涵,而一次对时事政治的偶然思索,成了他解构原著、挖掘成因的创作契机。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英媒有关萨达姆恶劣行迹的报道铺天盖地,背后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军事介入伊拉克而制造所谓的‘民意’。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政治立场似乎在向‘右’转,可几分钟前我还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怎么会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马奎尔将这个自我诘问与之前有关女巫的疑问联系到一起——人究竟是生而清白还是生而邪恶?人身体里是否存在早已命定的邪恶因子?39岁的他决定写一本书,为原著中人人憎恶的坏女巫辩护——《女巫前传:西方女巫的命运与一生》由此而来。
该书一经上市,不仅引发读者群的疯狂追捧和争相抢购,还引起了环球影业总制作人马克·普莱特对它的商业兴趣。在他的支持下,环球旗下的制作公司将《女巫前传》搬上了大荧幕,遗憾的是,结果并不尽人意。按马克的话说,总觉得缺点什么。
“我希望能深入探讨格琳达和艾芙芭的微妙关系,在同样的大背景下,展开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行动、选择和命运。但电影版浓度太高,且过于依附小说,我需要展现的深层次对话,似乎没法用电影完成。”

与此同时,史蒂芬·施瓦茨因友人推荐,饶有兴趣地阅读了这本小说。读罢,他立马找到他的律师,打听这本书的版权方何在。曾为《福音》《丕平正传》等多部经典音乐剧操刀的史蒂芬,在当时已数次提名托尼奖,是百老汇殿堂级的创作大师。几个月后,他找到还在等剧本二稿的马克·普莱特,劝他放弃把这本小说拍成电影,不如尝试用音乐剧来讲这个故事。
“97年那次见面,史蒂芬一席话给我点了盏明灯,我恍然大悟,这不正是之前电影缺的那点‘什么’吗?”马克回忆道。
有了词曲和制作方,还缺一位优秀的剧本创作。史蒂芬推荐了温妮·霍兹曼,而早在1996年,温妮便被《女巫前传》深深吸引,想要将它写成一部电影。但当获悉环球影业已经买断版权后,她就把这本书束之高阁,再也没看过一次——她为自己与这本精彩的书无缘而怏怏不乐。当史蒂芬约温妮共进午餐,并提出应该把坏女巫的故事写成一出百老汇音乐剧时,这位真性情的女作家为他的卓识惊叹不已。
“我从没想到用音乐剧去表现这本小说,而他的话一出嘴边,我当时就冒出一句内心独白:‘天哪,就是该这么干!’史蒂芬邀请我和他一起做这部剧,那一刻我有种强烈的预感,自己接下来一定能学到很多干货。”
巧的是,马克之前在电视上已经对温妮有所耳闻,并对她笔下那些少女的成长故事颇为关注。在征得原书作者同意后,集结完毕的三人立刻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工作。

【最初的探索】
要把一本400页的小说改编成一出舞台秀,还要不失原著中剧情、人物、细节的丰富饱满,无疑是一场漫长而曲折的征途。第一年,三人基本都在马克的办公室讨论,终日进行头脑风暴,把想法写在小卡片上,再按一定条理,分类贴在黑板上,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搭建故事的框架。
“回想起来,我们真的是一个个场景推敲,一个个角色斟酌,才串起了最终的整个故事。直到我们把所有小卡片都过了一遍,史蒂芬和温妮才分别开始动笔。”马克说道。
2000年春天,主创们在洛杉矶一所剧院组织了第一次读本会,只邀请了少数人到场。当时,仅仅第一幕的试读就长达两小时以上,主线剧情在开场后很久才浮出水面。经过一轮反馈与修改,同年九月,他们在环影公司的一间大厅里开始了第二次读本会,为期两周,呈现方式也比第一次要求更高。过程中大家发现,整部剧依旧很长,部分情节逻辑还很混乱。然而幸运的是,他们遇见了克莉丝汀,这位命中注定的“格琳达”。
当时的克莉丝汀是百老汇炙手可热的当家花旦,刚在1999年获得了托尼奖最佳女演员。彼时,她正在忙活一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NBC情景喜剧,身心疲惫,勉强接受了史蒂芬的邀请。但当她看过一遍剧本后,便毫不犹豫地出现在了读本会上。

在最早的版本里,格琳达只是一个辅助性角色,第一幕长达三小时的剧情里,几乎不见格琳达的身影。而克莉丝汀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读本时我只专注于我自己的部分。我觉得是台下观众开始慢慢感受到我们俩之间奇妙的化学反应,他们会忍不住想,‘天哪,这应该是格琳达和艾芙芭两个人的故事,而不是围绕艾芙芭一个人的。’一切都那么顺其自然,我并不感到意外。”
在克莉丝汀的建议下,史蒂芬和温妮重写了第一幕,并完成了第二幕的初稿。2001年三月,他们在环影公司举行了第一次完整的剧本试读和歌曲试唱。虽然他们三人自己对作品都颇为满意,但当时现场热烈而真挚的反响,仍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所有在场的人都激动地说不出话,只有雷鸣般的掌声在排练厅里久久回荡。
三人相视而笑,他们知道,是时候继续启程了。
【舵手与缪斯】
2001年夏天,乔·曼特罗作为导演正式入组。当时的乔在业内颇受认可,也执导过几部小型的音乐剧和歌剧,但从来没有接手过像《坏女巫》这样大制作的工程,因此不少人持观望态度。
“执导戏剧和音乐剧,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合作的性质。”乔谈道,“在戏剧里,导演和剧作家的关系较为私密,也相对可控。而在音乐剧里,将有更多人的参与决策,掌握航向也更需要技巧。不过好在,如果是和一屋子聪明人共同商议,解决问题的过程会更有趣也更刺激。”
当乔收到剧本和第二次读本会的录像时,演出开场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第一个登台的是摩丽波校长,由她宣布坏女巫的死讯,并接着引出桃乐茜、小狮子、稻草人和锡皮人。

“这四个角色都太深入人心了,我担心他们一开场就同时出现,会引发观众观感不适。事实上我在想,干脆一个都不要出现。”乔觉得当时的开场并不是最佳方案。
此时克莉丝汀已经读完了整部剧,二人默契地达成共识:应该由格琳达乘着她的泡泡船缓缓从天而降,进而揭开这出戏的序幕。
事实证明,乔对剧作杰出的驾驭能力,迅速推进了整个故事的发展,他能很好地把握笑点与亮点,平衡叙事节奏。在正式选定克莉丝汀出演格琳达之后,他很快在纽约主持第一主演艾芙芭的选角。当时距离“9·11”事件刚过去十天,正是人心惶惶,主创们为了赶进度不得不打起精神。而伊迪娜的出现,不仅成为沉重工作氛围下的重要慰藉,更让人们看到了一颗冉冉升起的百老汇新星。

当时的伊迪娜是第一个走进面试间的演员,她涂着绿色眼影、绿色口红,甚至腮红都选了绿色。就是她读完小说对艾芙芭的第一印象——眼睛像上了烟熏妆,穿着破烂的深色衣服,邋遢而落魄。
所有人都很喜欢伊迪娜,尤其是温妮,几乎一见如故。当她第二次来面试,大家基本就认定不会再有更好的人选了。然而伊迪娜在试唱主题曲《Defying Gravity》时,高音并没有完全唱上去,她为此还在家大哭了一场。
“我对这个角色和整个剧组都有种莫名的归属感。乔先生和史蒂芬前辈,都是我梦寐以求的合作对象。我也期待通过这次经历,自己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工作者。但这首歌确实被我搞砸了,我唱到一半破了音,最后几乎是骂着喊上去的。当时我心里想,他们喜欢也好,反感也罢,我都豁出去了。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骨子里有部分和角色是息息相通的,我相信他们也会看到。”伊迪娜说。
伊迪娜是对的,乔的确看中了她性格里的这种特质,认为这恰是她的可爱之处。同时他对两位女主角火花四射的磁场碰撞也十分满意。
“伊迪娜很鲜活灵动,给人感觉不按常理出牌,这一点恰好和克莉丝汀的稳重形成对比。在台下她们几乎是两个世界的人,然而一旦站上舞台,两个女巫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是令人惊艳的。”
读本会和工作坊差不多持续了一年半,根据制作人和在场业内人士的反馈,史蒂芬和温妮又花了两个月进行剧本的润色,并把两位女主演的个人魅力注入到角色中。
当一切工作基本就绪,马克和他的制作团队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舞台上的奥兹国会是什么模样?这场旷日持久的百老汇征途究竟会带来什么?
他们决定前往大幕将启前的最后一站——旧金山。

【最后的试炼】
城外试演,是百老汇音乐剧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作品将第一次接受舞台和观众的检验,主创团队通过实际操作和观众反馈,来判断哪些设计可行,哪些效果不尽人意。整个试演的流程和周期可能令人乏累,但对于整个团队却意义重大。为了节省成本和规避风险,许多制作人事实上会放弃全本演出,但马克却决定,他们要完整呈现最一流的表演。
2003年5月28日,剧组在旧金山的科伦剧院举行了第一次售票预演。当时距离剧本创作提上日程,已经过去了三年半。剧情做了无数次修改,歌写了一遍又一遍,故事线算是成形了,但整体还未完全敲定。
主创中的几位女性在事后采访中提到,那是很孤单的一段日子,温妮独自坐在旅馆,逐字逐句地看剧本,想象这一幕在舞台上会是什么样?观众会觉得这段无聊吗?这种灯光符合当时的氛围吗?不断这样自问自答。伊迪娜则对着每天都会新改的歌词反复练习,努力去与角色建立联系,在一周演出八场的情况下,还要保持声音的状态并维持体型。
然而事后回忆起来,这段体验不仅弥足珍贵,也让她们促进了对对方的了解,收获了惺惺相惜的情谊。克莉丝汀就对温妮的才华大加赞赏:
“对我来说,温妮是这出戏真正的明星,她让整部剧活了起来。你要是看了小说就会发现,两个版本是截然不同的。不知道她以后还会不会再写一部百老汇剧本,但我希望她会!她为我们每个角色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而且一起逛街时我发现她品位也很好,爱她的理由实在太多了。”
当晚演出开始前,史蒂芬和温妮并肩站在观众席一旁,紧紧攥住对方的手,他们还从未完整看过一遍自己的作品。温妮记得很多观众入场时还戴着女巫帽,当龙钟苏醒,烟雾从舞台两侧升起,剧场一瞬间沸腾了。史蒂芬则长舒了一口气:
“我去看技术彩排的时候,许多装置和设计还很成问题,那一周我尽量回避任何人,因为我怕我一见面就会向他们发牢骚,而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我当时真的担心能不能成。而预演当天我就完全打消了这个顾虑,虽然剧还是很长,而且有些包袱没抖出来,但总体上我看到了这部戏的前景。”

伊迪娜的母亲当时赶来旧金山观看了演出,后来还在浴室里听到其他人谈论,这部剧的感染力有多强,观众们多么为之动容。“就像我派出的一个间谍。”伊迪娜笑着说,她完全能体会台下人的心情,“做音乐剧就是一个先做加法,再做减法,最后接受检验的过程,真的很有趣。回首这段过往,似乎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却也是最有意义的。”
小说原作者马奎尔也观看了首场预演,按他的话讲,他原本做好心理准备会“尴尬地缩在椅子上”。但当他看到克莉丝汀乘着泡泡船从天而降,伊迪娜笨拙地冲到台前,活像他心中那个窘迫的少女艾芙芭,马奎尔带头鼓起了掌。
“我那晚起的鸡皮疙瘩到现在都没褪,”他开玩笑,“或许这就是典型的百老汇后遗症吧。无论今后再看过多少次这部剧,我依然能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观众们如何纵情尖叫、欢呼,为西方坏女巫的风采所倾倒。”

如今,《魔法坏女巫》已走过了第十四个年头,当人们仍为当初这部世纪巨制感动不已时,或许不会想到,在这场华丽的视听盛宴背后,是一批人六年的朴素践行。正如制作人马克·普莱特所说,这场从小说走向舞台的漫漫征途,本身就是史诗性的。
2017年四月,又一批全新阵容即将带着他们的奥兹梦来到中国,向国内观众展示一个愈久弥新的奇幻世界。目前这部剧正在已经结束了上海站的演出,目前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如火如荼地上演中。而6月中旬的广州站,也将成为《魔法坏女巫》世界巡演的告别场。在《魔法坏女巫》收官之前,不妨走进剧场,亲身体验这份来自百老汇的狂欢和惊喜。末了或许还可以再驻足片刻,想想当年这场余味无穷的翡翠色探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