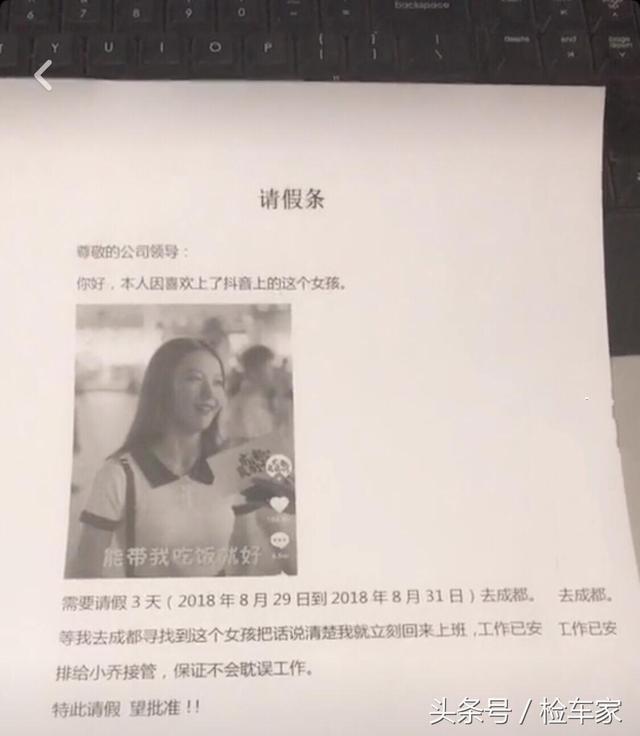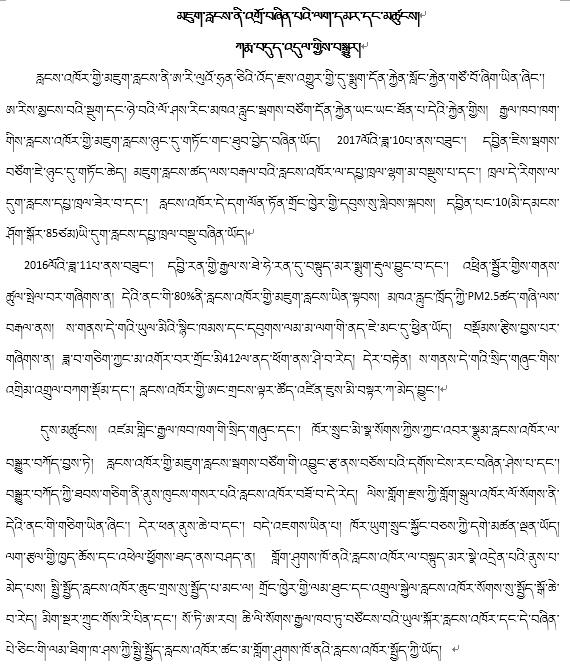哔哔救护中心的车鸣声低沉,却足以提醒到坐在窗旁值班的钱程,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车祸后的故事大全 新年的车祸民间故事?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车祸后的故事大全 新年的车祸民间故事
哔哔
救护中心的车鸣声低沉,却足以提醒到坐在窗旁值班的钱程。
又有新病人来了。
作为内、外、骨科唯一一个实习生,钱程带着值班护士快步走到门诊门口,查看病人情况。
救护车上下来的是那个短头发的圆脸姑娘,干净利落,一副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傲慢模样,有着天然的急诊医生气质。钱程和她照过几次面,但除了工作,没有聊过别的。
“心率89,血压180/110,血糖11.4,体温39.2,异常心电图,意识昏迷。”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语气中也不带有任何的情感。
她念完了手上的记录,抬起眼皮朝他点了点头,轻声说了句:“车祸创伤。”
四个字轻飘飘的,却像是个千斤顶一样砸了他一下,眼看着就是下夜班的时间,竟然遇上了棘手的病人。
“大夫,严重么?”这时,背后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
钱程回头,与那齐刘海儿的姑娘四目相对,二者皆是吃了一惊。
“学姐?”
张小宇是他上一届的同校学姐,与其不同的是所修专业为管理类,本科只有四年,所以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
和她一起从救护车上跳下来的高个子男生是她的男朋友,从相识到相恋再到毕业找工作,一起走过了四年时光,据说已经在筹备婚事,就等着房了。
“学姐,你……”张小宇和她的男朋友荣天佑是事件的肇事者这件事,他是一万个不愿意接受,不是亲但是故,他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你们放心,人我会尽力救的。”
带教医生老李这边看着心电图,从眼镜与额头之间的缝隙之间瞥了眼门外坐着战战兢兢的年轻情侣,推了推滑落鼻尖的眼睛,问道:“外面坐着的是你同学?”
他点头道:“恩,是咱们学校毕业的。”
老李瘪嘴摇头道:“这事不好办啊。”
“撞得很严重么?”
“撞得严不严重不说,关在在于,撞了体弱多病的老爷子。CT还没做完,不过,十之八九是脑出血。”他撂下手中的化验单,拿起电脑旁的电话,自言自语道:“我还是先给脑外打个电话,叫人来会诊吧。”
北方冬天的早晨,可怕的不仅仅是削骨的寒冷,更是昏朦的白雾,市区与郊区的交界路口车辆混杂,被对面私家车的大灯晃到眼睛,加上摩托车头盔结了冰霜,谁能料到眼皮底下有横穿马路的人呢?
张小宇在心里想了一万个如果,心中涌起了浓重的悔意,鼻头一酸,湿了眼眶。
为了爱情,与男朋友托关系进了一家外企工作的张小宇是个外地人,在这座不甚熟悉的城市,荣家是她唯一的依靠。每天早晨他们都要骑上一辆过时的摩托车,从城外四五十公里的乡下往单位赶,其中的艰苦,是难以和远在家乡的亲人诉说清的。
救护中心的医生遇到交通事故,第一时间除判断伤者病情外,有责任报警。
所以那些穿着深蓝色制服的警察们后脚便到了,比CT胶片来的还要快一些。
并排坐着的男女见到了警察,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并不是叫人受伤那么简单,事情的严重性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荣天佑,荣家的独子,二十五岁之前小错不断,但算得上一帆风顺。此时此刻,他脑子里一片嗡鸣,潜意识认为:自己这辈子是完了。
住在乡下家里的爹妈赶过来需要点时间,年轻人心里没底,怕因紧张乱了分寸,连忙打电话叫来了附近上班的大伯。
大伯来时,也是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可惜性质与警察有着天壤之别,乃是一位普通的蓝领。看这架势,应是刚撂下钳子就跑过来了。
钱程跟着脑外的值班医生、急诊外科大夫、带教医生老李在管片机下围成一圈,各个神色凝重。他资历尚浅,看不太懂这些黑白阴影的东西,但听着老师们的讨论,觉得双脚像是灌了铅,张小宇在外面等着他给一个确切的诊断,他却不知道怎么说出口了。
急诊和外科的大夫都是风风火火的个性,憋不住话,脑外的姚医生回头问走廊里的警察道:“家属在么?”
“还没到呢,正往这儿赶。”
“这都什么事啊?还要多久?”
“家属都在外地,没办法。急么?”
姚医生点头,“急,都马上做手术。”
一听做手术,不仅是肇事一家,就连警察都跟着出了身冷汗,案发地点在市区边上,正是该减速的岔路口,按理说车速应不快,竟然撞得这么严重。
“大女儿说再半个小时就到。”
医生穿着一身墨绿色的手术便服,和他本身气质一样利索,“半个小时啊……行,我知道了。”
下一秒他的身子就往急诊手术室走了,边走边回头嘱咐道:“让肇事者先交5000办个手续,把患者推进来吧,我们开始麻醉。”
钱程一出门诊屋子就撞见了扑过来的张小宇与荣天佑。
“阿程,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要做手术?”
“是脑溢血继发的脑疝,需要马上做开颅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他解释道。
“不过是蹭了一下,怎么会这么严重?”
他挠了挠头,用已经连续工作24小时的大脑努力思考如何通俗易懂的解释这件事情:“蹭到的大腿只是青了一块,但是病人本身有三高,血管脆弱,因为倒在了地上引发了脑血管的破裂,发生了出血,这些血液沿着脑子里的缝隙流到了一处,将原本的脑组织挤到了一边。”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你知道的,大脑是十分精密的器官,有一点差错也不行。”
“是、是会死人么?”不是很明白,但从医生们的态度上能猜到其严重性,荣天佑怯怯问道。
小护士在一边给他使眼色。
“小钱,”刚接诊一个胃痛病人的内科大夫喊道,“过来帮忙开一下B超。”
这是在警告他做医生的嘴要紧。
钱程是老实人,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那个,具体情况还是要看手术过程了,我也不是很了解……”
老头大女儿终于赶了过来,匆匆签了手术知情同意书,众人不动声色,内地里却都是捏了把冷汗。
“有钱没处花,非要自己搬出来住,吃饱了撑的!”皮草大衣金手镯,酒红色的皮包过膝长靴,身材相当不错,可惜是个龅牙,两颊长满了大块黄褐斑,粉底涂再厚都遮不住——一看就是个急脾气。“什么年代了,还有人骑摩托车。你有证么?”
荣天佑与小宇一下子就被问住了。
他们确实没有证。
是啊,什么年代了,怎么会有人去考摩托车的驾照?
原计划是今年五一结婚,男方出钱买房,女方出钱买车,摩托车是缓兵之计,哪能想到会栽在这上头?
“无、证、驾、驶?”大女儿恶狠狠指着荣天佑的鼻子喊道,“你完蛋了!”
“对不起,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自打知道荣天佑也是母校毕业的后,老李的心就已经偏到了胳肢窝。
“别吵了,事情的真相,我们现场的同事会查明的。”警察不耐烦道,“现在肇事者跟我去警察局录口供。家属留在这里。”
荣爸爸来的正是时候,晚一步恐怕就要辗转去局子看他儿子了。
钱程曾经听张小宇提起过这个中年男人,所以有意的打量了一番:因为甲亢的原因,视力损害严重,四方的眼睛有啤酒瓶底厚,还有些斜视。身材高大,衣服还算体面,只是头发花白,是该修剪一下了。
大伯怕年轻人在警察面前说话没分寸,主动要求要跟着去警察局,叫荣爸爸留下来看家属这边有没有什么要帮忙,临走前神色凝重的拍了拍荣爸的肩膀,没说什么,却像是把千斤的担子都搭在了那只肩上。
今天是新年假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家门口的福字对联都完完整整的崭新的贴着,他们来不及到单位里给同事们拜年,就注定要在上班的路上驻足了。在两个年轻人心里,是不是还抱有这样一种希望:因为忘记了今天是要上班的日子,所以在炕上赖床,这一切,不过是一场警示他们的梦境,等到走出这家医院,一切都会消失,面对他们的,仅仅是扣除今天的工资而已……
午后的阳光明媚异常,很难想象,就在今天早晨,还是看不清马路对面的浓雾天气,钱程下夜班回到宿舍补觉,再睁开眼睛已是下午四点。
心里有隐隐不安,于是打通了许久未拨的那个电话。
“学姐,你们那边怎么样?”
“挺顺利的。”一改早晨的战战兢兢,现在的她似乎心情不错,“一个亲戚是交警的厅长,能说上话。”
听上去很厉害的样子,“哦哦,那就好。”
“你呢?医院那边怎么样?”
“我今天下夜班,刚才在补觉……”尽管是事实,可话说出去,他竟有种羞愧感。“一会儿帮你打听一下。”
“……那辛苦了。”
人都知道医生赚的钱多,却不了解其中的辛苦。从昨天白天到今天早晨下班,没合过眼,到头来竟叫自己师姐觉得他是不够上心,不够义气了。
他叹着气,又拨通了发小阮青的电话。
“阿青,你是在ICU值班吗?”一米八五的肌肉男,阴差阳错的学了护理,说出来都没人信,所以被医院当熊猫一样的关在了ICU里。
“是啊,怎么?要请我吃饭?”
“你想的美。我是要和你打听个病人。”
“你说。”
“早晨急诊送过去一个脑疝的老头,现在下台儿了么?”他问道。
“你等等,”电话那边传来翻东西的声音,“哦哦,有,姓周,车祸的,手术成功,已经下来了。”
“醒了么?”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忽然大声:“醒个屁!现在醒还不得疼死,你以为是拔牙啊?”
差点忘了,这是开颅手术,做的是全麻。
“哦哦。好吧,惹怒您了。”
“这老头儿谁啊?你怎么这么上心?”
“肇事者是一个学长。”他如实道。
“啧啧啧,真是流年不利。那我留意点吧,醒了告诉你。”
“好。”
医院门诊大厅紧挨着收费处,客流量多,但也是最冷的地方,一排排灰色的不锈钢凉椅让暖色调的瓷砖地板降了几个温度,周老头的亲属挤在一起,尤为突兀。
老太太被两个女儿拥着,面色憔悴,紧闭着双眼,嘴唇一颤一颤的,似乎是在忍受极大的痛苦。大女儿嘴里喋喋不休的说个不停,一会儿安慰老娘,一会儿又转头呵斥自己的弟弟与她老公,闲不下来。二女儿是个圆脸,轮廓柔和许多,画着淡淡的妆,穿的也低调,只是轻靠在老太太肩膀上,目光呆滞的看着天花板。周老头的小儿子坐在老太太对面,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交叉,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在场的还有大女婿二女婿与儿媳妇,只是这三者脸上的担心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
病人做完手术之后还需要在ICU观察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家人见不到老爷子,心里甚是煎熬。
“姐,要不咱们先把住院办了吧?”儿子提议道。
大姐放下翘着的二郎腿,正了正坐姿,大声嚷嚷起来:“咱们?凭什么是咱们办?那姓荣的一听手术费的价格,就马上说要回家拿钱,前脚走,后脚就关机了,最后还不是咱们凑的手术费?手机没电了,五六个小时总冲上了吧?好歹也来个电话问一句啊?又不是没给他电话!咱爸手术成不成功,下没下手术,他们有人问么?想让我给这种人垫钱,门儿都没有!”
大姐态度坚决,小儿子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二姐身上。
二女儿抿了抿嘴,缓缓说道:“我看,咱们还是先办了吧,到时候荣家要真是不来人,咱爸给晾在外面,丢的是咱们的脸。”
得到了支持,小儿子面露喜色,大姐哼了一声,竟没反对。
“不过,咱们现金结算。”原来老二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是个真正的狠角色,“不用医保。咱爸的医保是全报的,不能叫他们知道,否则,别想从他们那拿到一分钱。”
“不会吧?我看这家人挺老实的。”
大姐一听这话,火又上来了:“我说老三,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二姐拍了拍她的胳膊,叫她镇定,“我刚才叫同事打听了,那小子他爸是个村官,手里应该有点钱。”
大姐一听这话,又抑制不住情绪,站了起来:“对对,现在的农村人,哪有穷的?哪一家手里没有几套房产?今天早晨他一来,我就知道条件差不了,就是穷惯了,会装,你可别被他给蒙了。”
一个是中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一个是靠天吃饭的无产阶级,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家庭;一个原本住在另一个城市里子孙满堂的老人,一个是正准备着与女朋友筹办婚事的小伙子,本来是应该一辈子毫无瓜葛的两代人;一个年后的早晨,天空下着雾,一辆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的摩托车和一个马上就要到家的老头儿,就这么发生了碰撞,瞬时间斗转星移一样,就让两家人的命运全部因此而更改,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眼看着就是元宵佳节。
荣家再是不幸,至少还都周全。
而周家呢?
元宵怕是吃不上了。
命运就是这么一个毫无章法可寻的东西,你再是遵纪守法,也不能保证一世的平安。
学校东门之外有一家田园风格的咖啡厅,因环境优雅物美价廉而成为了约会聚餐的不二之选,张小宇毕业大半年,还记着它,于是约了钱程到里面小聚。
说是要跟他咨询周大爷的病情,却叫小钱自己坐在里面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
年轻的情侣姗姗来迟,一个穿着大红色的长身羽绒服,一个套了件黑色的皮夹克,一点看不出落魄。
“听说老头子已经从ICU里推出来了?”
钱程点头:“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他们松了口气。
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你们没有去医院看看么?”
没看是没看,她竟然是摆出了一副嫌弃的表情,理直气壮道:“他那泼妇一样的闺女你又不是没见识过。我们怕引起正面冲突,托大伯去慰问,结果她可倒好,站在病房楼道里一顿大骂,门都不让进,将好好的一篮子水果全都砸坏了。”
“话虽这样说,可事实上就是咱们理亏啊。”
就算是老爷子有病身体不好在先,也是他们的失误直接直接导致了这场悲剧。
钱程见张小宇与荣天佑有些不高兴,才意识到,有些话虽然是实话,但人家不一定乐意听。
“赔偿金的事情,商量的怎么样了?”
“这事情说来奇怪,”她回道,“刚开始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好,因为拿不出那么多钱,索性关了机,可等到后来我们凑齐了手术费准备垫上时,他们又不催了。”
“手术费要多少呢?”
“还要再交一万八,我们准备了三万块钱。”
“那还好。”
“好什么好?”荣天佑插话道,“我总觉得,周家正在悄无声息的酝酿着什么不可告人的计划。”
“你们在打听周家人的底细,想必,他们也自暗地的打听你们吧?”
“那最好,”他耸耸肩,“我们家穷的一清二白的,养不起猪,烧不起暖气,这些最好都打听去。”
“我看周家不像是会因为你们家里贫寒就善罢甘休的人,尤其是大女儿呢。最后闹到法庭上就不好办了。”他看得出荣天佑是好面子的人,这种事情当然是能私了就私了的。
谁料得荣天佑正乐意他们在法院上解决问题,“遇上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主,还是得依靠法律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判决,要是私了,恐怕以后我们家就要穷的喝不起粥吃不起咸菜了。”
那日事发之后,荣家动员了所有劳动力进行全方位的法律咨询,原本都是理科出身的几个年轻一辈,都成了半个事故专家,趁着下班后晚饭的时间已经召开了好几次家庭会议,最终还是觉得事情并没有爱么严重,只不过是倒霉在老头子自己身体不好上。
“那依你之见,这件事要赔偿多少呢?”
“老头子现在病情如何,我们不清楚啊。”张小宇解释道,“周家人似乎是买通了值班大夫,我们什么都打听不到,所以,想拜托你帮个忙。”
果然,双方都经各自展开了阵仗,筹划好了战术,就等着最后的争斗了。
“这倒不是什么难事。”以学习为由,既不荒唐又不犯法,还能帮助自己的前辈,何乐而不为呢?
“依你之见,老头子恢复健康还需要多少钱呢?这种手术会不会落下病根?听说,他是个退休干部,只要是活着,每个月就有一万多的退休金可拿,要是因此折寿了,儿女肯定会找我们拼命。”她担心的说。
“脑疝和一般的脑出血不大一样,更凶险一些。”他解释道,“不过,最凶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所面临的应该是术后漫长的恢复过程。”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概述复杂而又深奥的疾病给眼前这些毫无医学常识的人,应该是所有医务人员的职业生涯中,都曾苦恼过的问题。书本上所印刷出来的概率百分比,怎样才能说出去既合理又清晰呢?而且,他们到底是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回答才肯满意,而他又该不该如实的将事情的可能性一一列出?
果然,医患沟通也是一门学问。
“对了,老爷子醒了没?”他问。
“你怎么还问起我们来了?”张小宇责备道,“说实话,我都不太记得,那老爷子长什么样。”
居然忘了,周家人一直是拒绝他们探视的。
事情有些棘手,钱程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安。
开颅手术术后存在许许多多的可能性,可不是代表你从阴差手上逃脱后,就真的自由了。
能不能重返人家,还要看你的造化。
外科病房向来是忙的。一个实习生一旦踏入了医生办公室,将面临着被当做八个畜生一样使唤的命运,小钱主动向教学秘书请缨说要献身道外科病房的工作时,教学秘书不动声色的给他开了实习同意单,心里乐开了花。
周大爷住的十五病区是高干病房,就是一般的有钱暴发户,都不能入住,看来这周家果然是有背景。
趁着早晨查房,他跟在带教老师身后,有幸见识了一番。纯木的衣柜书架,真皮沙发,56寸液晶大电视,墙角摆着鲜活的插花,墙上挂着的工笔画居然不是印刷品,框在玻璃后面,精致的叫他不敢触碰。
当日在场的是老人的小儿子和一个护工。
这样大的手笔,荣家准备五万元搞定的术后护理,怕是泡汤了。
带教老师坐在电脑前伸着脖子敲着键盘开医嘱,钱程就坐在他身边的位置上,奋笔疾书,记录着今天各个病人的情况。为了不引起注意,他需要按部就班,尽量自然。
轮到了周大爷的病历,他的心跳扑通扑通的加快了。
“老师,这个周大爷是不是病的挺严重的?”
“周?哪个周大爷?”
他看了一眼病历夹子皮,回道:“27床。”
“哦,你说的是高干27床的土豪啊?严重倒是不严重,就是不大乐观。”
“土豪?”
“恩,真土豪。”他停下手上的活,竖起拇指,佩服到,“住院居然不用医保,我寻思着没医保就给省着点开药,结果人家特意嘱咐了,必须全用进口的好药,怕国产的不安全。”
“那是要贵上不止一倍吧?”
许多药物都必须是低温避光储存,这样的环境下从国外运输到国内,还要缴纳关税,所以要比国产相同成分的药贵上几倍甚至十几倍。
“是呀,这家人差不多是一天一万块钱的护理费用,要么怎么说是土豪呢?一般人家拿拿得出这么多现金?”
“大概是外地医保,需要回家去报销吧?”钱程道。
“哪是什么外地人啊,开发区的,也不远。”
“原来是开发区的啊。”
“是啊,大过年的遇上这种事,举家都往咱们这跑,也够可怜的。”
“你说他病情不乐观,是什么意思?”
带教吃惊,“刚才查房时候想什么呢?是不是没注意听护工交待病情?术后八天为苏醒,算是乐观么?”
还未苏醒?
居然是这种尴尬的局面。
开颅手术术后最为难以捉摸的结局莫过于这种情况,一旦确诊患者进入“植物人”状态,恢复起来难比登天。
钱程觉得自己很可笑,因为在那样一瞬间,他想到的竟然是周大爷变成“植物人”后,退休金还会照常发放么。
“这么久不醒,不会突然over吧?”他担忧的问。
带教老师皱眉责怪他,“别说那晦气话,能盼点好不?他要是挂了,写死亡抢救记录的还不是你?”
闲暇之余,钱程将周大爷的情况告诉了张小宇,依他之见,老人家的病情不像想象中的乐观,荣家最好做好充足的准备,无论是心理的还是金钱上的。
昏迷现象的发生在颅脑外伤术后的病人中比较常见,不过这是个原发病一大堆的复杂病案,什么时候醒来,能不能醒来,谁也不敢打包票。
即使是接受了近二十年科学教育的熏陶,他仍不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追随者。
从医生办公室门上长条形的玻璃窗往外看去,刚好是电梯大厅,周家小儿子这会儿夹着一尘不染的黑色公文包,急匆匆的按了电梯,抬头看着电梯上的小屏幕,显得十分焦急,电梯到了,他混杂在护士与几个患者家属之中,挤了进去。
家属的鼓励与支持在病人的恢复过程中十分重要,即使他看上去正沉睡着,毫无意识。
相伴数年不离不弃最终唤醒沉睡的病人的感人例子,科学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但屡见不鲜。与专业化的护工陪护和照顾比起来,迷失在某一个异度空间中找不到回家的路的周大爷,此时此刻更需要的是家人的呼唤。
可这才几天,三个儿女就已经放弃了么?
他想起高干病房里那个全自动的独立卫生间,忽然觉得可笑无比。
这样的孝顺到底是做给谁看?
日子到了第十四天,周大爷的恢复情况可喜,但依旧是昏迷的状态。医药费终于突破了十万,金额正跃跃欲试的想要突破十一万的门槛。
科主任五十多岁的模样,短小精干的身材,被一群主治医生、住院医和学生围在中间,皱着眉头透过眼镜片看病历上的文字,住院医滔滔不绝的说着诊治过程,也不知道他听进去了多少。
主任亲手检查了周大爷的病理反射和生理反射,背着手,面无表情的淡道:“出院吧。”
“出院?”大女儿目瞪口呆,“我们,我们这人还没醒呢。”
“一般状况基本恢复正常,接下来的是漫长的护理,还是在家里进行比较合适。”他解释道,“回道他熟悉的环境中,听到家人的欢声笑语,植物人并不是没有转醒的可能。”
“这不行啊,主人。”她几乎央求着,“您得留下我们,我们这还好利索呢。”
“你们家不是住在开发区么?来回的跑也不是个办法,况且,生病的领导这么多,您们总是站着高级病房也不是办法。”主任不耐烦的说道。
医院外会有一些“山寨”的救护车,设备与装修与正规救护车别无二样,只是车型大都是国产的,价格上差了一大截,最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危重病人运输途中的安全,当然,有的时候医院里死了人,家属要求将尸体运送回老家,一般出租车是不会拉的,这时候也需要这种“黑车”出现。
周家人就是打了一量这样的“救护车”,返回了老家。
“学姐,周家人办了出院手续,走了。”钱程道。
“啊?走了?是……死了么?”她语气中难掩激动,“还是醒过来了?”
“都没有,确定是‘植物人’状态了。”
“那好吧……”她有些失望,随即又问:“那么,你估计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呢?”
又是问他这种根本说不出答案的问题,如果直接告诉她百分之多少的概率,她一定会说:“咱们都是同学,你就直接告诉我确切的结果吧,别拐弯抹角的,我又不是接受不了。”
可是,事实上就是如此,他也不清楚啊。
“短期之内,应该是醒不过来。”周家三个孩子态度并不积极,可不能排除奇迹的发生。
“唉……”她叹气,“我知道了。”
周大爷出院后的第三天,钱程终于抽出空来,打电话约出了荣天佑与荣天佑到火锅店里吃晚饭。
不到半个月的功夫,荣天佑现在家里,倒是白嫩了不少。
他开了个玩笑说天佑哥终于把毕业之后瘦下来的几斤体重补回来了,天佑与小宇都是一脸凝,似乎是高兴不起来。钱程给他们倒酒,天佑一声不吭的和他碰了个杯,仰头一口闷掉。
前二十五年一帆风顺,被爹妈捧在手心里呵护长大的小伙子,刚步入社会就碰到了铜打的壁,心里自然苦闷。
“真是狗娘养,狼心狗肺!”他红着眼睛,已然没有了前几日见时的意气风发。“张口就是六十万,当我家是土财主怎的?”
“六十万?这么多?”算上护工、医药费和来回的路费,二十万怎么也是够了。
“说什么我爸当年是村委书记,清白不了,肯定捞过不少油水,也不知道他们是哪只眼睛瞧见了。”天佑爸要不是做官清白,也不会放着严重的甲亢不舍的调护,勒紧裤腰带给天佑买的婚房。
平白无故给扣了个“贪官”的帽子,你说他冤不冤?
“就是家里老人昏迷不醒,心情不好,也不能说出这种话啊。”
“就是就是,这家人真是可恶至极。”张小宇咬着牙骂道,“以为全世界的官全和他们一样!贪得无厌!”
你不舔着脸面对悲惨的命运,就永远不知道,下一秒的生活还能多凄惨。
钱程想到这句话,又看看低头喝闷酒的荣天佑,忽然不觉得它可笑了。
“没有别的办法么?和他们商量一下,分期还钱行不行?”
“就是分期,以我们现在的能力,二十年也还不上的。”她解释道,“可不给钱,就要坐牢。”
他还那么年轻,真是可惜。
“能还下多少来,就还下多少来,然后把新买的那套房子卖了,缓缓。”
“房子不是结婚用的么?”
“这不是没办法的办法么?六十万不是小数目。”
那天晚上荣天佑是自斟自酌的喝的烂醉如泥,而张小宇则是一个劲儿的叹气没有胃口,钱程不好意思自己胡吃海塞,却没想到,那竟是他在这段时间,最后一次见到他们。
自周大爷出院销声匿迹在他的身边之后,那对倒霉的冒失情侣也再没联系过他,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学习中后,时间过的像是流水,一转眼日历就翻到了四月中旬。
海棠花都开了,春意盎然。
脱掉了厚外套,中午穿一件棉质的格子衬衫也不会觉得冷,他坐在嘈杂的食堂中抬头,发现墙上的电视居然是开着的。
事实上,食堂的电视到了吃饭时间,总是开着的,只是很少有人关注。
天气舒适宜人,学生们愿意多坐一会儿,这才有人去关注周围发生着什么。
报道的是一个酒后驾驶的长途车司机因为高速超车而导致了四死七伤的惨剧,这叫他又想起了年初发生在周荣两家的世故。
事情过了两个多月,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钱程给张小宇打电话,第二次才接,原来是在理发店里。
“最近还好么?”
“就那样吧,还不过了不成?”她自嘲道。
如果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算一算,现在的他们应该正在筹备着婚礼。
“房子卖掉了么?”
“没有,不卖了。”
“那是……借到了钱?”总不能是忽然中了吧?
“借什么钱,蹲监狱去了。”她冷道。
“监狱?”他吃惊,记得当时聊天时,又说道天佑爸为此大动肝火,扬言一分钱也不会给,难道是真的?“六十万虽是多了点,但总好过看亲生儿子坐牢吧?”
“要是六十万就好了,”她叹了口气,“人心能吞象啊,到了法庭,他们改口说要一百万,我们哪给得起?”
这不是吃人么?如果真的为此借了一百万还给周家,那天佑一家将来的生活一定生不如死。
“坐牢之后就不用还钱了么?”他问道。
“那样子就只需要担负住院所用的医药费。”
“想不到竟然是这样的结果……”他惋惜。
“当初啊,还不如直接撞死他得了……”
生活真是个残酷的老师,大学教会了我们真善美,它却在这之后不停地扇我们巴掌,叫我们红肿着脸,含着泪去面对人生的波折。他想到电视上那些衣冠楚楚的知识分子行凶杀人案子,忽然觉得他们并没有那么可恶了。
人生啊,很多事情不是你小心谨慎就能一声平安的。钱程打了个哆嗦,看了看主干道上怒放的海棠,再也瞧不出任何的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