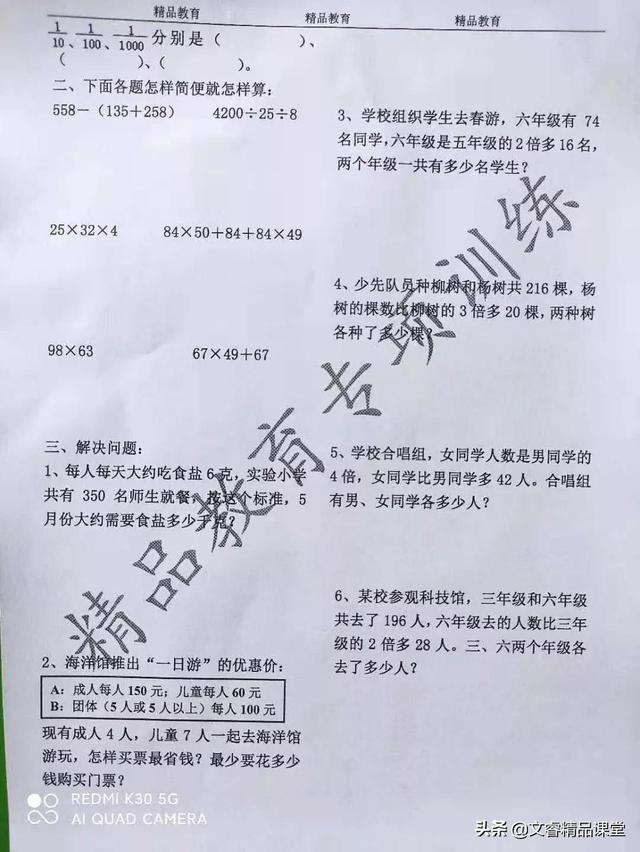原书名:『言語が消滅する前に』
原作者:国分功一郎、千叶雅也
翻译校对排版:春琦美空
注释:日语里的“言語”与“言葉”,本文都翻译为“语言”,细分而言,“言葉”更有words = 言词的意思,但在本文的各种使用语境里又不好这样翻译,索性都“语言”吧。两位作者都对德勒兹有研究,“情动”=affect这个词虽然他俩用的随意、基本是媒介研究的用意,可以理解为,“情的动”、“感动”;但应该也有德勒兹哲学的色彩(情动是对并非自身的东西的遭遇……),大家自己斟酌,译者就不多改动了。
闲聊:这本没有更多翻译了,完结撒花。喜欢请去日亚支持本书哦。
仅供学习目的,禁止商业用处,译文基于CC BY-NC-SA 4.0发布
欢迎有志者私信加入或投稿(翻译或原创):lab_on_roof@163.com
首发 网哲邻人部,屋顶授权转载
国分真的帅啊,千叶更年轻的时候也很帅
千葉 雅也(ちば まさや、1978年12月14日 - )栃木県宇都宮市出身。日本の哲学者、小説家。
専攻は哲学及び表象文化論。学位は博士(学術)(東京大学・2012年)。立命館大学大学院先端総合学術研究科、同大学衣笠総合研究機構生存学研究所に所属。職位は教授。
[千叶还获得了第162届的直木赏,所以说是小说家没问题]
國分 功一郎(こくぶん こういちろう、1974年7月1日 - )は、日本の哲学者。
東京大学准教授。最終学位は博士(学術)(東京大学・2009年)。海外の学位としてはDEA・哲学(パリ第10大学・2001年)、DEA・言語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02年)を取得している。
人类正变得不去使用语言
国分:我说点夸张的话,这难道不是和现代世界之中语言被赋予的地位问题有关系吗?哲学家阿甘本在《身体的使用》这本书里就指出了这件事,我们已经逐渐不再是由语言规定的存在了。
其实,阿甘本的这番语言好像是在否定我的著述(笑),但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分析。
千叶:嘛,国分桑是想要抵抗(阿甘本所说的)现在的状况吧。
国分:说的是呢。就像最开始所说的,我们学习了的二十世纪哲学是重视语言的哲学。这就是海德格尔试图在语言之中把握存在本身的原因。但是,我认为在这样重视语言的哲学之根底那里,存在着人类是由语言而被规定的存在这一前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对我们来说甚至是一种牢狱,正因如此,我们才产生了怎么样才能走出语言之外的想法。
然而,恍然间注意到,人类已经不再是由语言所规定的存在了。语言正变得不对我们作出规定。我寻思这一点可以从很多地方指出来讲讲。
比如,这说不定是个乏味的例子,但LINE的表情包与颜文字就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要说那(表情包与颜文字)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不使用语言的交流也是足够了的。只是在进行某种情动\情感的传递。在日常性的交流里,这样就足够了——这件事明白了。
在写邮件\消息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自己在编织语言、撰写文章,但实际上只是在对输入法智能预测端出来的选项进行选择捏。而且,这样也能够、足够写就一篇文章了。
在我们思想界里,经常谈论什么“语言的物质性”云云。语言本身就是某种的物质,于是读东西就像是触摸块状的岩石一般的物质。举个例子,就像海德格尔所热衷讨论的荷尔德林的诗、或人们所说的头脑中灵光一闪刺入的究极性语言。
但是在现代,作为物质的语言这一共识,难道不是正在消失吗?
千叶:语言已经变成了单纯的道具。只要使用就好,因此语言本身就成了完全透明的手段,不会被其牵扯劳心(引っかかる)。所以,置换成颜文字也没关系、置换成符号也没问题。语言要保持之为语言的理由,没有啊。总之,交流正变得全面化。用一个非常相反的说法,语言曾不是仅仅为了交流而存在的东西。
语言本身就是可被摆弄\改变的东西,例如,它可以变成诗歌。诗歌是自我目的式的、并非为了交流而存在。但是现如今(もはや),自我目的式地写诗,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只有一小部分的好事家还在做。一切都被交流所支配,一切的手段都变得可交换、可变换。
国分:英语教育也是呢。说什么交流啊,交流的。“HI!HOW ARE YOU?”这种一分钟左右就能记住的东西,却像拼命一般来教。
千叶:就这,也敢说英语能说会道了呢。
国分:关于这种现状,从“勤勉学习(強いて勉める)”的角度来说,有很多话想吐槽,但总之,社会被交流这种东西所支配、语言则正在消灭——这是个很大的倾向\趋势,我认为有必要指出来。这个倾向,可以从哲学层面略显困难的视点来论述,也可以从刚才所讲的LINE层面来论述。
千叶:比起推特,Instagram(小红书)正变得更有优势,也是这样呗。
作为道具的语言、作为物质的语言
国分:我想问一下千叶你佬。我自己是一个不会读诗的人——一直有这样的、某种自卑似的感觉。我觉得不仅是我,在我的世代(XX后)里也有很多人共有着(我这种状态)吧。
语言已死,变成了废墟,从那里捡起来的只有贫瘠的碎片。因为那已是碎片、没有了富饶的词语,只好加油整理好顺序、尽可能有序地书写。这就是写书之时的我的印象。我感觉自己的语言非常贫乏啊啊啊。
正因此,在七零年代的日本曾有过“请买一本我的诗集!”那样的文化,大家是被诗歌触碰到了吧?
千叶:在六零年代的日本那会儿,诗人所拥有的文化地位很高,一说“アマタイ”,就有像是偶像一般的力量呢。
国分:说的是天泽退二郎吧。但是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天泽退二郎呢?上次,我和高桥源一郎先生对谈时,我一说“我不会读诗”,他就说,确实他们自己的诗之经验大概与国分们的世代完全不一样。像高桥那样的世代,若要出版诗集、大家就兴奋得跳起来一样。
不过,在高桥先生那里作为参考的是,当时日本尚有诗的批评。大家虽然都在读诗,但没有批评的话果然还是不太清楚。诗人也有兼任批评家的,诗人之间也相互批评,读者就可以把这些汇总起来读一读。听说当时也不是只读诗歌,我还松了一口气。
千叶君,关于诗的发言还挺多呢。
千叶:我自己也会写呢。
国分:关于诗的读书体验,或者说诗体验——是什么样的感觉?
千叶:语言啊,是物质呢。所以,会读诗或不会读诗——这种说法不太对,诗啊,不是理解意思的东西。(诗)是对象啊。(詩は意味を理解するものじゃない。オブジェクト\objectなんです。)
我的表现活动,原本是从美术制作出发的,因此,我认为所谓语言基本上是物体。那是挺质朴素直的思考。所以我啊,反而不擅长为了最大限度效率地传递意思而使用语言。对于我来说,文字的物质性配置、突然看到网页时汉字看起来有多黑,这般次元的东西经常会在最开始时就想到。
我写东西的时候,会同时连结着在这种次元与意义之间的折中,所以无法放弃将语言当做道具来使用。总是把语言当作某种粗糙坚硬的东西来摆弄\改造。那也是我的弱点,说话的时候并非如此,但写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写得很慢,这是因为语言的物质性绊住了我的脚。
国分:东浩纪在推特上说过,最近因为用打字机来写作、能将文章把握到一块(ブロック,版块\区块等意思)上,我也完全是这样的。用版块或段落来把握文章。比起一句一句地读,更多是一块块地看,如果哪块的样子不对劲,就去精查内容。
千叶:诶,有趣。
国分:一个板块的下一个板块是这样的大小啊——像是建筑的结构层面有着错误一般,是这样的判断呢。千叶君说眼睛首先会关注到语言的物质性配置,我想跟这种感觉有点接近。
在我写的《中动态的世界》里,为了使阅读更加容易,增加了换行、松解了板块。但是,一看画面,这一页有很多黑色之类的,那种感觉我很理解。感觉黑色有点太多了呢之类的。然而,虽然我大概有一回进行了这样的判断(反思),但在那之后,如何传达(译者注:不确定是不是说文章的内涵\意义之传达)的压力变强,(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从上述的角度对文章进行了重新修改。
刚才听的时候想到的,千叶君,不怎么谈小说的事情吧。
千叶:小说,我不擅长啊。或者说,由于人与人之间发生了麻烦\纠纷、行为就会连锁发生起来——这种事情太呆太笨了,都没有办法。因为啊,在人和人之间产生麻烦\纠纷,很笨蛋 = 八嘎吧。因为是笨蛋,才会有麻烦。如果所有人的灵魂都上升一个台阶,麻烦就不会发生,故事什么的也没有必要了。也就是说,所有的小说都是愚妄的,因为它们是以灵魂的台阶低~为前提写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没有读小说的必要。
国分:在这里突然出现了非常激进的命题呢(笑)。
千叶:但是,在诗里没有人。只有物质。所以那很棒。
国分:原来如此。你讲的是这种意思呢。话说回来,我的书总是被说成像是推理小说的感觉。《德勒兹的哲学原理》(岩波书店,2013年)的时候,尤其被这样说。千叶君所说的,是所谓近代小说的事情吧。
千叶:嗯。若非近代小说,而是更具实验性的小说、或者更古老的东西的话,我也会觉得很有趣。
国分:我写的东西,在形式上可能确实和推理小说接近,被人家这样讲我也挺高兴。作家大西巨人曾说,任何小说都存在推理小说式的要素。要问为什么的话,因为小说都想要解开人生之迷,在这一点上不管什么小说都会变为推理小说式的。我是从(大西巨人)口中直接听到这样的说法的,虽然也许他没有写成文章。
如果这样的话,哲学的书也是解谜,所以我觉得也会有这样的一面。千叶君,你又在思考着和我不一样的做法了吧?
千叶:国分桑写的东西,因为是推理小说式的展开,所以从前面开始阅读下去是前提,是时间性的呢。我的书,是以能够随机访问(random acsess)这种方向来考虑的。所以是空间性的。我觉得我和国分你的书的区别,就在这里。国分桑,正是把生命赌在了如何(让读者)翻开书页上了呢(笑)。
国分:绝对要让你读到最后。绝对不让你跑掉,这样的感觉呢。
千叶:太厉害了捏,这种力量。
国分:但是,在《德勒兹的哲学原理》的时候,因为太直线猛攻的速度,自己来读也累到了(笑)。到这个程度,我寻思不管咋说还是挺糟糕的,所以在各个章节的最后、加入了展开的研究注释以供休息。不然的话,我觉得会变成一直在跑步机上奔跑似的读书呢。在哲学类的书籍里,可能没有多少达到这种地步的直线猛攻的书。
千叶:通常是不时曲折一下、不时中断一下追问吧。
国分:是那样的呢。但是,在哲学类的书里,那种一边绕远路一边徐徐论述,最后又一下子回到了最初的问题——这种展开的书很稀有\没有,我从前就对此非常不满。在中途虽然会散发曲折,但最后“回到了最初提出的问题”——我想品尝这种快感。但是,能满足我这一点的书很少,所以,我打算自己写一下。
……(中略)
人类已不再由语言所规定
国分:至今我和千叶君其实在好几个重要的场子里进行过数度对谈呢。但是对我而言,好像并没有一种频繁对谈的感觉。
千叶:确实是这样呢。印刷成活字的对话屈指可数。
国分:就像《キャプテン翼》中的翼君和岬君那样,偶尔会结成为黄金组合(笑)。就是这样的印象。
千叶:我个人是经常交谈讲话的。
国分:虽然经常讲点话,但在世间上只是偶尔现身呢。虽然是这样的稀有组合,但我感觉把我们两人谈的事情向世间传播也是不错的。
那么,当我考虑用什么作为(谈话的)主题时,果然还是关于“语言”吧。回顾一下,我在《中动态的世界》中尽情地处理语言,千叶君的《学习的哲学》里,最初的一章也主张成为偏重语言的人。
千叶:两者都是语言学呢。
国分:是的。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追究的是语言。首先必须要确认语言所处于的现状。因为语言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感觉21世纪式的语言状况大概已经差不多现身了。那跟20世纪式的、即我们在上世纪九零年代开始学习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千叶:说的是呢。在20世纪的思想进入新的阶段时,就如同通称的“语言学的转折”那样,首先意识到了语言(这一回事)。因此,语言意识存在于二十世纪的思想的基底处(ベースにある),这一点首先应该得到确认。因此,在21世纪如果发生了语言的弱化(弱体化),那么它(思想)将转向与20世纪式的人文学科之模式不同的东西。
在二十世纪,语言的维度比什么都重要。对文科的人来说,语言的地位相当于对理科的人而言的数学呢。
国分:如果人文学科确实变得不能依赖语言了,那可能就像物理学不能使用数学一样。
千叶:另一方面,我们如今进行的讨论,会在相当抽象的层面上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总体来处理。但大概一般的人不会以这样的标准来把握语言。一般来说,(日常里)如果谈及语言,会预期是指英语和日语等特定的某国语言。因此,提出与语言这一存在本身有关的问题,这件事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我是这么认为的。
国分:原来如此呢。那稍微展开一下千叶君提出的问题吧。这是我前面也提到的一个例子,在阿甘本的《身体之用》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片段。根据阿甘本的说法,现代哲学基本上是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研究作为超越论式主体的人类。与此相反,尼采、本雅明、福柯、本维尼斯特等哲学家试图从此脱离,并试图通过——在语言中找到规定着人类的“历史先验性(歴史的ア・プリオリ[a priori])”——来实现之。
也就是说,人类是由语言来规定的──这种从19世纪末左右开始的20世纪式哲学,并非超越论式的主体,而是说话的人、使用语言的人。这就是语言论转折的起源那样的东西呢。
千叶:稍作补充说明的话,在康德的场合里,人类的思考被认为原本是由一些抽象的规则而被约束[被设置条件]。从19世纪末那会开始,人们变得这样认为:给人类的思考和行为设置着条件的、是历史地形成了的语言。
国分:是的。“历史先验性”是福柯使用的表达方式。虽然既是先验性又是历史性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如果追溯一下我们的思考,其实存在着被历史地规定着的前提似的东西。而在语言处寻求(这个),成为了尼采以来的哲学的基本。
问题是接下来,阿甘本说,这种哲学的尝试可以说在今日达到了一个完结点。我稍加引用,“然而,又变化了的是,语言活动已不再——未经思考、原封不动地——作为一种历史先验性而发挥作用(就像规定着交谈语言的人们的历史可能性并设置条件那样)”(《身体之用》日译,第192页)。
就像这样,作为规定人类之物的语言已经终结了。阿甘本的诊断是,人类已不再由语言来规定。
千叶:所谓的“历史先验性”,尽管持有着历史性,却仍然表现出了(自身是)绝对地先行之物的双重性,因此我认为这正是为了形容语言本身的术语。
以语言把动物和人类区分开是很常见的。那么,人类的语言能力,或者说使人类的语言能力成为可能的认知能力,在进化层面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并不清楚地知道呢。但在历史层面上,这发生了(だがそれは歴史的に始まった)。然而,只要人类存在着,就有作为绝对性的先行条件的语言。那么,阿甘本是否表示,人类从其他的存在者中区别出来——这种区别的方式本身就已经结束了?
国分:是呢。确切地说就是“动物化”。
千叶:人类,作为与动物之间、在进化(光谱)上具有连续性的存在——变成这么一回事呢。
国分:在二十世纪,人类是由语言所规定着的存在,这是一个哲学性的前提。语言甚至被认为是人类无法摆脱的枷锁。但是在当代,反而有一种语言在退却、(人)从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感觉。
千叶君刚才指出了,抽象地将语言的整体予以问题化——这种事情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但在当代,这或许更加难以实现。就连哲学和思想,都将变得无法做到这一点。
直接性的唤起情动的时代
千叶:现在啊,已经不能不用道具式的语言观来把握语言了。
国分:在福柯的《词与物》(新装版,新潮社,2020年)里,在17世纪古典主义时代的叙事中,语言被视为透明的媒介,所以没有看到语言本身的存在。当进入19世纪时,就像荷尔德林的诗所参照的那般,作为坚硬粗糙的岩石般的物质之语言被发现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从那考虑的话,当代的语言看起来就像回到了17世纪。与17世纪的不同之处或许在于,交流不一定依赖于语言、而正变成相当情动式的东西。
千叶:当情动式表现出现在前面时,在解释层面上必要的语言就是多余了的呢。可以更直接地表现情动的颜文字、表情包变得风头正盛。所谓表情包(Emoticon)是由表情(emotion)和图片(icon)组成的造词,是表示表情和感情的颜文字。正如这语言所表示的那样,我认为在当代随着语言的弱化,我们正在向使用图像、直接性的唤起情动之时代转变。
国分:通过LINE和WhatsApp可以知道的是,日常的交流只需要表情包和颜文字就十分足够了。它接近于通过摇尾巴来表达喜悦的交流类型。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隐喻和无意识的弱化与此同时发生了。
千叶:说起来,语言之所以是麻烦的存在,是因为它不是直接性的表现,而总是间接的、迂回之物。当一个语言指向什么的时候,又会惹起另一个语言,意义作用会稍微偏离。语言不是直接与现实关联,而是夹在其间。也就是说,语言是直接性满足的延期,更简单地说就是忍耐。这种直接性满足的延期,是通过隐喻的存在(而起效的)。在语言活动中,总有一些讲不透的、没有达到真理的东西即不满存在着,在这些不满的周围,各种各样的语言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地展开着,由此丰富的语言形态就成立了。
然而,围绕着这般不满的语言已变得不再繁殖了。要问为什么的话,我认为原因之一是直接性满足变得越来越有可能了。虽然这是个单纯的说法,但在当代社会,被迫忍耐的情况正在减少,并变得可以立即获得快乐。也就是说,通过语言的连结而对直接性满足予以忍耐——这件事已变得不再需要。
国分:在德勒兹写给福柯的信里,欲望和快乐被对立起来。所谓欲望,是在什么和什么之间存在着。在没有被满足的状态和被满足的状态之间,正是一边忍耐一边努力的状态。与此相对,所谓快乐就是终点,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福柯的话对快乐很有关心吧,但德勒兹自己在那封信中说自己对欲望更有关心,这展示了两种异同的哲学方向(吉尔·德勒兹,《欲望与快乐》,《狂人的两种体制1975-1982》,河出书房新社,2004年)。
但是,在当代所发现的,不就是一直停留在终点那样的状态吗?这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可能。
千叶:例如,为了纯粹合理地进行自己的身材管理,可以马上在便利店购买并摄取所需要的精确到克的营养素。在那里,没有任何忍耐。我觉得这是应该恐惧的事情,虽然确实很方便。
国分: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所谓忍耐就是现实原则。因为,所谓现实原则是快乐原则之实现的延期。因为人类不能仅靠快乐原则来应对现实,所以即使不情愿也能接受现实原理——这是弗洛伊德的前提,在此,在两者的相克之中人类有了成长、这也被视作理所当然。而(如今)这变得不再理所当然了,对吧?
……(中略)
玩具般地使用语言
千叶:语言就是相对于状况的距离本身,所以语言的失落[失墜]意味着距离的消失。这样的话,敌对关系之间的距离也会消失,所以就会发生\变成直接冲突。
换句话说,语言的物质性所具有的为避免直接冲突的缓冲材料这一侧面浮现了出来。这种缓冲材料的社会性意义,也和文学或者艺术的存在意义连结在一起吧。
文学和艺术,不是道具般地直接使用语言,而是把语言当作一种语言来使用。这种元语言式的使用在日常中也存在的情况,成为了社会不走向直接情动式的方向的防波堤。
国分:感觉就像威廉·莫里斯说的,日常之中艺术是必要的。并非工业产品的杯子、而是使用不知名的工匠所制作的杯子,爱着这个杯子的同时生活下去。一边装饰着日常生活一边生活下去。对于语言,如果也用相同的思考,那就是嬉戏于语言之间(言語を遊ぶ)吧。
千叶:我在《学习的哲学》中,提到了语言的玩具式使用这回事。所谓学习,是指走出到至今为止规定了自己的生活之物的思考框架之外。而且,目前为止的生活和特定的语言的使用方式连结在一起,所以说,走出那个世界之外意味着会改变语言的使用方式。
只是在那个时候,如果只是从一个用法A转移到另一个用法B,那只不过是转移到另一种生活而已。我在那本书里所说的“深入的学习”,不仅仅是转移到另一种使用方法上,而是让自己站立于自身隶属的环境之外部。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把语言单纯地作为道具而使用、必须意识到语言自身。
在此关键的是,玩具式的语言的使用方式。通常,当我们说“帮我拿盐”或“我讨厌你”时,我们会将语言视为具有直接引发事件的力量之物[译者注:即作为行为的语言],但如果我们用从这种情况脱离开来的视角看待事情的话,语言就变成只是说说的东西而已(ただ言ってるだけのものになる)。只是说说的语言,因其被价值中立化了、所以讨论得以成立。虽然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好,但正是像这样获得这种只是说说的语言、才算是深入的学习,而将语言当作语言来操作、就是通过频道(スペクトラム)与作为语言游戏的文学连结在一起。
……(中略)
语言是 “魔法”
国分:这样的话,公共场所和非公共场所之间的分配变得更加困难。当大学开始网课时,我首先说的是,教室根本不是公共性的地方。因为不是公共性的,所以能够说喜欢的东西,出错也没关系。其封闭性对于确保教室的自由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教室太过封闭,就会出现教师变成专制君主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对于教室来说,半公共性、半私人性,既开放又封闭是很重要的。
但是,现在在讲课上说话的时候,不也变得总是不得不害怕公共性的东西了么?虽然听起来有点夸大其词,但我想起海德格尔在《人道主义书信》中指出的:“语言正在向公共性的独裁屈服”(马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给巴黎的让·波弗勒的信》,ちくま学芸文庫、一九九七年、二六頁)。我真的感觉到了这一点。
千叶:又回到了语言这个大的主题呢。毕竟,人是通过语言编织现实的。因为只有用语言这种虚构的层次(レイヤ)来包裹、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对此疏忽的话、就会损坏人性(人間らしさ)
语言是危险之物,在某些情况下,一句话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的举止。虽然人们说科学的力量像魔法一样,但我认为,对于能够制造原子弹或其他东西的科学家的行动本身、用一句话就能改变之的语言才更像是魔法呢。但是,正因如此,如果说(在日本与全世界?)现在压制文科的动向正在高涨——这可能是我太反讽性的说法——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语言的轻视也在步步紧逼。
国分:用语言打动人,可能是指对于人能够用语言创造出欲望。确实,那是“魔法”。信息和数字可以给予认识,但创造欲望必要的不就是语言吗?所谓政治,基本上是靠语言来干的——汉娜·阿伦特的这个主张,也要理解为,并非依靠信息与数字、而是要靠语言来行事。打动人的是语言啊。
千叶:刚才说过的属人性之物的忌避,也和语言的失落[失墜]有关。语言的力量太强大了,太可怕了,所以我甚至想说,(现在)不是在向着丢掉语言的那一边发展吗 [言葉をなくそうというほうに向か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
托尔金也好,勇者斗恶龙也好,我觉得虚构的世界里出现的魔法,基本上就是语言的隐喻。魔法使不是也会读旧书吗?那是文献研究者的隐喻吧。
国分:(文献研究者)只是不去使用那种作为魔法的语言、而去搞某种信息管理了吧。
千叶:信息是匿名性、系统性的,无论是谁发出的,都是一样的;但语言是与人的固有性、人的复数性缠绕在一起的。这确实是阿伦特式的说法呢。
附朋友的一则书评:千叶把 dg 对情动的态度改造成了一种历史终结的情动,认为在历史终结底下,隐喻和多义性的语言已死,让位给了一种直接呼唤情动的语言。实际上几乎是接在东浩纪“象征秩序的失堕”之后,千叶说,“语言(隐喻与多义性)也失堕了”。那么,在语言的隐喻性和多义性日薄西山却仍尚未死透的过渡时代,言葉が消滅する前に,我们应当回头重新思考语言的存在意义。“主体化”的概念仍然是今天至关重要的问题(这里基本沿用了dg的判断),即“全球资本主义解域了一切固着性,让任何事物的交换都成为了可能状态”,那么主体化的问题则在于,如何取回自己(主体)的特异性?当然,书题里 “语言的消灭” 不过是作为可能性的一种头脑风暴,但我对这个对立轴本身保留九分九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