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人天性喜欢无拘无束和自由自在的生活,但也不乏适应环境的能力:德国人很在意新鲜空气,无论在家里,还是办公室,每天都要多次打开门窗通风,而戴口罩带来的那种湿乎乎和透不过气的感觉,让他们非常不适。但是,形势逼人,不习惯也要习惯。从上周开始,商店里和公交车上,德国人也正儿八经地戴上了口罩。
按照此前商定的“两周一议”的节奏,德国联邦和各州在4月15日首次决定部分开禁之后,又于4月30日再次商议进一步开放的具体步骤(Zwischenschritte)。这次的基调与上次相比基本无异:审慎的乐观,缓步地解禁。除了要求整个社会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和卫生习惯之外,所有开放的领域都必须制定严格的防护措施。
这次新增的开禁领域包括以下几个:
1.儿童室外游乐场。这对儿童和家长都是一个不错的消息,虽然没有对开放时间做出统一规定,但社区必须制定必要的防护措施。
2.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展览馆、画廊和纪念馆等场所。除了遵守既定的卫生规定外,这些场地(特别是面积较小的)还必须控制好每次进入的人数,同时还要避免排队。
3.宗教集会可以恢复举行,但教会等举办方必须严格遵守防控要求。
餐饮业、旅游业以及其他一些文化设施则还需要耐心等待。联邦和各州决定5月6日之后再议。其间,相关部长会先制定方案,提出建议,但默克尔强调,何时以及如何开放这些领域,将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在学校和幼儿园如何开放的问题上,联邦和各州尚无法达成一致。默克尔宣布,5月6日会就此问题再行商议,届时将明确规定学校和幼儿园开放的顺序和方式。
8月31日之前,民俗庆典、有观众的大型体育赛事、大型音乐会、庆典活动、乡村和猎手聚会、年度集市等大型活动将继续被禁止。至于何时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恢复小型或私人活动,这次的联席会议没有作出决定。鉴于这类活动(特别是大型活动)的易传染性,政府将根据疫情未来的发展情况再作决定。
关于夏季度假问题,默克尔指出,夏日欧洲旅行问题这次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外交部针对全球范围内的旅游警告已经延至6月14日。这个日期之后不久,德国有些州的暑假即将开始,所以政府将在此前作出决断。
联邦和各州的联席会议只是商定一个大的框架,各州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措施。因此,这次会商结果刚宣布,各州便开始“各行其是”了,其中下萨克森州(Niedersachsen)、萨尔州(Saarland)、萨安州(Sachsen-Anhalt)和萨克森州(Sachsen)解禁的步伐迈得最大最快。从现在的趋势看,原先的“联合协商,整体部署”节奏似乎很难继续保持了。
疫情中采取的限制措施,导致各州企业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企业状态不好,又意味着地方的财政收入大幅缩水;而财政收入的减少,又会影响各地政府的运作能力。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是解禁过程中各州步伐不一的主要原因。
对权力的不信任
新冠病毒给德国劳动市场的冲击远远超出经济学家的预计。截至4月26日,德国共有约1000万人申请“短时工”(Kurzarbeit),而专家们此前的估测最多为300-700万之间。
“短时工”制度是德国处理经济危机时屡试不爽的一把“利器”,始于上世纪初的帝国时代。最近一次“短时工”高峰是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时,当时有330万人提出了申请。
劳工市场有“春季复兴”(Frühjahrsbelebung)一说,所以,每年四月一般是失业人数下降的月份,但新冠疫情让德国经历了战后首次“不降反升”的局面,企业的招工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6.9万。
因此,今年的“五一节”其实有足够的理由为劳动市场担忧。换作往年,德国的大城市这一天会出现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可是新冠病毒让这个有着130多年历史的国际节日变得无比“安静”:引领五一游行的德国主要工会,这次也只能各派一名代表在首都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前举牌“刷存在感”,真正的活动全部由街头转入网络。

在线庆祝五一,图片来源:推特截图
没有街头游行的示威活动,有点像观众台空无一人的足球比赛,让人感觉怪怪的。当然,非常时期要求非常方式,劳工们虽然无法走上街头,但口号还是少不了的。今年的“五一”口号是:“团结起来不孤独”(Solidarisch ist man nicht allein)。
“口号”不仅是一种高度浓缩后的纲领性表述,也是政治组织及其代表显示自己存在和作用的“广告”。
以这次疫情为例,执政党有足够的“用武之地”,不必用“口号”来提醒选民和显示自己并非无所作为;在野党的处境就不同了,面对政府颁布的“面面俱到”的各类抗疫救市措施(不管是限制性的还是放宽性的),反对党能施展的空间的确非常有限。于是,他们渐渐告别开始时做出的与执政党“共赴国难“的姿态,回归找茬和反对的“老本行”。民主政治也的确离不开反对声音,哪怕这些声音有时显得“苍白无力”和“鸡蛋里挑骨头”。
眼下,社会上担心政府会钻“紧急状态”空子的声音越来越多,也有人开始思考联邦制和法治体系的种种漏洞,但笔者很难相信,德国联邦及各州政府会借着疫情大肆揽权,并在疫情缓解后尽量拖延放还为应对疫情而收拢的权力。然而,回顾历史,人们的担心或许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
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于1991年设立了一个新的税收名目,并赋予其既通俗易懂又名正言顺的名字:“团结税”(Solidaritätszuschlag )。顾名思义,一般人都认为“团结税”只是为了分担统一造成的巨大财政压力,其实不尽然。根据当时的决定,该税还有其他两个用途:一,填补海湾战争给德国财政造成的漏洞,当时德国用花钱(169亿马克)的方式,即所谓的“买单外交”(Scheckbuchdiplomatie),来换取不派兵参加那场由联合国授权和美国领导的战争。二,支援欧洲中部、东部和南部财力不足的国家,但笔者不清楚这是与统一后的德国在欧盟中承担的义务有关,还是涉及欧盟的东扩计划。
总之,这个本来只是为期一年的措施后来“稀里糊涂”变成了“无限期”(unbefristet)。之所以说“稀里糊涂“,因为大部分人都以为是为了统一大业,因此觉得义不容辞,并无怨言。由此可见,“名目”很重要,该税因“团结”二字一下子实行了29年,每个有工作的人都必须缴纳收入中的5.5%来支援统一和东德地区建设。
有道是,开源容易节流难。这个当时看来“名正言顺“的税收的确给政府增加了不小的财政回旋余地,所以,统一后德国的历届政府都不愿意主动放弃这笔收入。随着民众对该税越来越不满,现届联邦政府才决定从明年(2021)起逐步放弃“团结税”。
了解了这段历史,就容易理解人们为何担心政府有可能不会很快放弃和归还因疫情而集中在手中的权力,譬如业已扩大了的《感染保护法》(Infektionsschutzgesetz)就强化了卫生部的职权。
西方的政治制度正是基于对人性不善的那一面而设计的,因此,德国人常爱说:“信任是不错,监督更重要”(Vertrauen ist gut, Kontrolle ist besser)。
西方媒体的报道方式
4月17日,武汉订正了当地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数和死亡数的统计数据。感染人数从50008上调至50333,增加325例;死亡人数从2579上调至3869,增加1290例。
这个数字变化的原因似乎也不难理解:1)早期检测和收治能力不足,有些患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死后并未按照新冠肺炎致死病例上报;2)疫情初期一些医疗机构未能与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实现有效对接,疫情数据统计和信息报送工作没有与医疗机构扩容收治进度保持同步。
本来,面对如此规模和凶险的瘟疫,官方在上述瓶颈和不足之处得到改善和修正后对数字进行调整是很正常的,也是强化抗疫“透明度”的一个具体体现,但是,中方此举却被有些人用来作为质疑的“依据”。
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认为中方此举“令人担忧”,并敦促北京“增加透明度”。他在接受《图片报》(die Bild-Zeitung)采访时表示,有些问题总要给予回答的,今后几周内,中国领导人有机会证明自己在疫情中的透明度。德国《明镜》将报道马斯观点的新闻冠以“批评中国”(Kritik an China)的标题,并称武汉死亡人数的上调“出乎预料”(überraschend)。
4月29日,英国正式将死亡人数从21678上调至26097,增加4419例。原因是此前的数字只显示在医院确认死亡的人数,并不包含在养老院和家中的死亡人数。对此,马斯至今未作表态,是工作忙忘了?还是对自己过早评论武汉数字上调“不好意思”了?笔者先放下不论,只谈谈《明镜》的表现。
《明镜》在报道英国数字变化时倒未写“出乎预料”。结合它对武汉新数据的评论,一般人会立刻认为这是《明镜》“双标”的表现,可以理解,因为《明镜》在过去的确做过“双标”的事情,但这次并非如此。它对英国上调数字一事之所以未写“出乎预料”,因为它的确没有感到意外。
早在4月16日,《明镜》就专门针对英国政府的疫情报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滞后的受害者”。文章导读一针见血:“在整个欧洲,养老院的居民深受新冠病毒之害,唯有一个惊人的例外:英国。但是,官方的数据正在欺骗和掩盖几十年来的疏忽。”文中详细分析了英国在这方面的症结所在,并未因为与英国的价值观相近而“笔下留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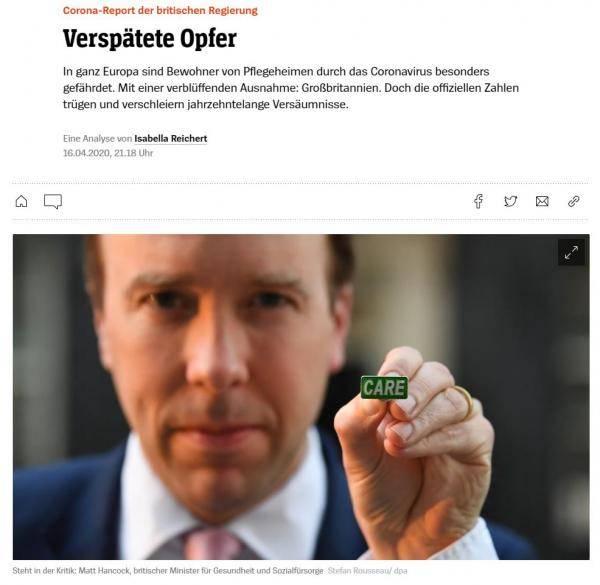
图片来源:报道截图
那么,《明镜》对武汉上调数字感到意外,是否就意味着它此前对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一直深信不疑呢?如若真是这样,那就该轮到笔者感到“出乎预料”了。
众所周知,西方媒体看中国时一定是戴着“意识形态”眼镜的。但是,仅仅知道这点还不够,还应该去了解它为何如此。这点很重要,因为了解差之毫厘,结论就可能失之千里。
对西方媒体的有些观点作出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关键在于如何反应。快速反击很容易,也很过瘾,但过快扣动“扳机”,也容易打偏甚至误伤。
德国媒体的主要读者群是德国人,而作者绝大多数也是德国人,因此,无论是封面,插图还是文字,难免会带着德国人看世界(包括看中国)的视角、观点和立场。无论作者的发心是恶意的,还是调研粗糙疏忽,还是出于傲慢与偏见,都属于“可预见”范畴,一时恐怕也很难改变。
笔者在德国工作生活了不少年,但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依然还有许多漏洞。西方驻外记者在海外驻地的时间有限,可以想象,这种“暂时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深入了解所在国的文化精髓和思维方式。更何况,他们获取的知识养份多是经过自己文化圈过滤过的信息和认知。所以,他们在报道异国事件时,必然会在“主观镜头”之上再加上一副“有色眼镜”。有鉴于此,出现“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等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各国的媒体其实主要面对本国国民,不少标题也是为了吸引国内读者的眼球。写到这里,笔者在想,西方媒体中的“反华”言论都是外文信息,中国国内的百姓又是如何大面积获悉的呢?这是否与华文媒体对西方言论“事无巨细”和“有来必往”的批驳有关呢?反过来,笔者很少看到德国媒体将中国对西方的“负面报道”搬到自己的平台上来逐一驳斥,因此,德国人并不知道中国对他们的看法和评价。
以《方方日记》为例,笔者去网上搜索过,除了预购广告外,德文直接报道该书的媒体文章寥寥无几;反观海内外华文媒体,对《方方日记》的关注“经久不衰”。对这样的结果,最高兴的恐怕是那些书商了。
还有,西方的有些作者和编辑对所谓“事实”的把握和拿捏相当老练,一般不会轻易被人抓到“把柄”。再以《明镜》为例:它的专栏作家库兹马尼(Stefan Kuzmany)前一阵就“新冠病毒”写过一篇文章。笔者把其中涉及到中国人的一段文字翻译过来,以“飨”读者:
“如果您对中国人久存狐疑,那现在不妨可以好好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 现在不是克制的时候,毕竟,拜这些黄皮肤的小眯缝眼所赐,我们很可能不久于人世。他们干嘛总要喝蝙蝠汤,咬断蛇头,并在集市上用耗子血洗澡?他们若不生病,那才叫奇怪呢。”
这些作者大多很“油”,如果文中含有刺眼的词语或指桑骂槐,他们会在标题下标明是“讽刺文”(Satire)。意思就是,我事先声明了,如果你看了不舒服,千万别来找我。“裤子骂你”(作者姓氏的“讽刺”译法,咱也来幽默一把)使用的就是这个手段。
为了客观起见,笔者专门请两位德国人来读这篇“讽刺文”,结果,他们的读后感大相径庭:其中一位觉得,作者是用讽刺的手法,故意“强化”那些偏见,以此来告诉读者不必那么夸大;另一位则认为,作者用词太过分,竭尽侮辱之能事,一派胡言,读后令人反感。
德国人的读后感尚且存有云泥之别,更不用说让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和体制之中的华人去“正确”理解了。
我们必须承认,同在华夏大地生活的中国人之间都有很大的区别,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日韩之间都存在那么多的不同,同一部《古兰经》都能让穆斯林分成逊尼派和什叶派,同为耶稣基督的信众,还会分裂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更何况中国人和欧美人的彼此认知呢?
面对不同的“解读”,特别是面对恶意的攻击,我们在必要的情况下当然要提出抗议和批驳,以正视听,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沟通和交流。这次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向外界提供的中德双语版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关于中国的16个谣言和真相》就非常好,有理有据,不打“口水仗”,让事实说话,包括引用外国知名专家的观点等。
官方信息如果一时不易被采信,那就多通过民间来加强接触,增进理解,譬如,促进并支持人文社会学方面的学术研讨和项目;在西方国家内多与记者交朋友,提供更多的采访和了解中国的机会;促进学生和年轻人之间的互访;争取知名学者的理解和认同,还有那些已离职或转行的政治名人,他们虽然不在位,但影响力尚在。
西方必须适应中国崛起的“新常态”
在中国的国际份量越来越重之后,西方媒体就加大了关于中国的报道。这次疫情中,笔者明显感到,虽然德国媒体或避谈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或用自己惯有的视角去分析和评论“中国现象”,但无论涉及工业产品的供应链,还是各种抗疫物资的生产和援助,还是对国际组织的支持,中国其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这次疫情中国首当其冲,西方当时“隔岸观望”,觉得病毒离他们还远,甚至根本就不会到来。这种过早和过于乐观的心态造成的结果,现在正在令欧美人伤透脑筋。不仅如此,关于抗疫中的经验教训,就因为它们源自中国,西方要么不接受,要么认为不合适,这也是欧美一些国家延误“战机”的原因之一。
德国这次抗疫中最突出的成功和失误是:“疑似”和轻症在家自我隔离,避免出于恐慌而涌向诊所,造成医疗挤兑(成功);严重低估了口罩的作用,造成这一抗疫“战略物资”的严重短缺(失误)。而这两个方面似乎都有中国的“影子”:前者汲取的是武汉的教训,后者是承认了中国人戴口罩的益处。
面对西方媒体的某些“反华”言论,用智慧和事实去驳斥反击当然需要,但有时幽默的效果或许也不错。
《明镜》1977年第31期的封面标题为“度假胜地意大利——绑架、勒索、街头抢劫”,配图是一盘意大利面条上放着一把左轮枪。
图片来源:《明镜》
面对如此贬低和轻贱的“封面故事”,平常比较容易情绪化的意大利人却没太在意,或许他们知道无法和患有“洁癖”的德国佬讲道理吧。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的回击颇为幽默:“在这件事情上,《明镜》只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封面上那把左轮枪和文中描述的不一样。第二,那盘面条煮得太烂啦。”
根据笔者的观察,在西方社会中,经济界是最现实的,有钱挣就行;政府是相对现实的,因为它要解决涉及国内外的各种棘手问题;学术界是最超脱的,因为来自那里的建议基本上都标明“仅供参考”;最投机的是议会中的反对党,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执政党拉下马,然后自己上台;唯有“第四权”媒体最“油盐不进”,因为它几乎不受任何权力利益的牵制和捆绑。
由此不难理解,给政府穿“小鞋”的为何主要是后两者。譬如,去年的香港乱局中,美国共和党总统川普开始并不热衷于介入,但国会中的反对党却积极推动干涉香港事务法案的通过。德国总理默克尔吸取了2015年难民潮的教训,不再轻易开启国门,媒体却又借着前一阵埃尔多安打开通往希腊(欧盟)的边界而频频报道难民生活如何不堪,指责政府缺乏人道精神。
实际上,西方媒体最爱“折腾”的对象并非外国政府,而是国内的当权者。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与媒体关系好的政治家凤毛麟角:川普没少骂媒体制造“假新闻”(Fake news),德国前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直接称《明镜》是“狗屎刊物”(Scheißblatt)。
当然,这反过来会让人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以“针砭时弊”和“监督权力”为己任的西方媒体为何只盯着当权者个人,却很少质疑或思考“体制”问题?其实,这是个误区。
首先,在西方,无论“当权者”还是新闻媒体,都在一个公认的体制内各司其职。也就是说,媒体基本上不会质疑给予它自由发声的宪法框架和价值体系(如自由、民主、人权等)。相反,媒体认为,维护这个体制不受权力、金钱、欲望等因素的侵蚀,是自己的神圣责任,因此,他们会紧盯那些有可能犯错的政治家和政党。
其次,西方人虽然对自己的体制颇自信,但也深知体制和人性的缺陷。因此,一旦出现问题(违法违纪案例、大的政治和金融危机),媒体在不触动“宪法框架”的前提下,也会揭露体制中出现的种种具体漏洞。
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欧洲也深受其害。当时舆论就热议过放任资本带来的害处(金融和经济体制)。在舆论的压力下,政府也意识到国家以往对资本的监管过于松弛,并做出了相应的补救措施,如加强对金融的监管,银行必须有“风险储备”等。
1999年,已经退出政坛第一线的前总理科尔被揭在任时卷入“黑金”丑闻(Schwarzgeldaffäre),媒体不仅对其本人大加鞭挞,也质疑当时的“政治献金”规则(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最后,政府对规则进行了调整(譬如降低申报义务的额度等)。
最近,美国著名“深夜秀”(Late-Night-Show)节目主持人梅耶斯(Seth Adam Meyers)在谈到本国疫情中救死扶伤还漫天要价的现象时说:这是“资本主义最糟糕的一面”(“This is capitalism at its absolute worst”)。
最后,所谓“西方媒体”是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因为即便在西方世界里,国与国的体制也不尽相同,譬如,在英美两国,强调市场和资本运作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及“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盛行;而德国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Sozialmarktwirtschaft)体系当初在设计时就已经剔除了美式资本主义的“糟粕”,强化了社会保障等元素。这两种体制也反映了德国人和美国人不同的“民族”个性:前者注重保险和安全,后者敢于冒险和创新。因此,他们彼此其实都“看不惯”对方:德国人一听不少美国人要打几份工才能养家就唏嘘不已,也不理解怎么能选特朗普这样的“疯子“当总统;而美国人则对德国人那副亦步亦趋的“死翘翘“的样子颇为不屑。但是,两边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彼此也就多了一份尊敬与合作的基础。
综上所述,“体制”问题在西方并非媒体的“禁区”,他们捍卫或不质疑的其实只是宪法框架和价值体系。而在中国,某些媒体人骨子里可能是质疑中国的宪法框架与价值体系的。
有些扯远了,现在回到德国的疫情上来:
在上周五联邦和各州的商讨会上,默克尔总理不得不公开维护遭到“非议”的科学家。
背景情况是这样的:从抗疫开始到现在,面对“新冠”这个至今尚未完全了解的病毒,科学家和诸多专家在专业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看法,可他们偏偏又肩负着向政府提供咨询的责任,政府的许多决策都仰仗他们的知识和判断。目前,联邦政府有自己的专家班子,各州的政府又有各自的专家班子。科学家们意见不一,势必导致民众无所适从,政治家决策的难度也因此而增加。
那么,各州自行决定究竟是联邦制的决策短板,还是因地制宜的优势呢?这是德国舆论目前热议的话题之一。现在,民众中已有人开始质疑“无所不能的政治家和无所不知的科学家”,并将此质疑引申到政府措施是否得当和正确的问题上。
毫无疑问,专家们之间不仅存在业务上的意见分歧,也还有显而易见的个人竞争和角力。已有专家公开抱怨默克尔过于相信某位科学家的看法,这里所指的是柏林的病毒学家德罗斯腾(Christian Drosten)。
冷静而耐心的德罗斯腾本人对此的感受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这份压力不仅来自政府的信任和同行的“相轻”,甚至还包括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
根据德罗斯腾本人透露,他收到过各种仇恨信息以及死亡威胁。他在接受英国《卫报》(The Guardian)采访时说:由于他对开禁持审慎态度,并警告第二波疫情可能带来更大的冲击,所以被许多人视为经济瘫痪的“罪魁”。这段时间,他常常睡不好觉,因为很多人给他写邮件述说他们对未来的担忧。
责任越大,压力越大,德罗斯腾的日子不好过啊。
- 未完待续 -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