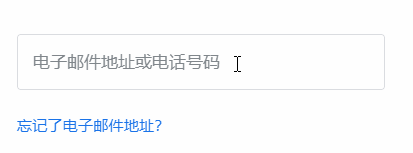麟游血条面

在关中地区纷繁的面食中,有一个另类——血条面。
听说此面已经很多年了,但因它的流布地远在麟游山区,交通不便,因而迟迟未能品尝。上一次去麟游是在2015年,其时交通已经便利,但还是由于诸事干扰,没能吃着。回来之后,心心念念,遗憾万千。

可以说,对于吃惯各类面条的关中人而言,此食的引人之处,自在于“血”。虽然大抵可以想来,此食应是牲血与小麦面相合所做的面条,但对其种种细节仍是疑惑在心,难解其详。尤其是一想到这血呼刺啦的面条会放入口中,总是有一种期待而畏惧的复杂心理。



我和一些朋友讨论过,关中人的饮食虽然固守“五谷”观念,守则而自持,但血还是吃的。比如我小时候吃过的血粑粑,以及现已传遍长安城的粉汤羊血,都说明此地人并非排斥血食。但对于血条面,不少人还是潜藏着心理上的膈应感。一想到屠猪的惨烈场景,再想到鲜红的猪血与霜白的面粉相拌,然后那如旗帜一般摊开的血猩色,心念里总是会被那种张扬的野蛮和暴虐感所充斥。
古人尚血是出于对生命的敬崇。他们发现,这种红色的体液一旦流尽,动物的生命就会枯竭,然后身体腐烂,一切归零。因此,在混沌的原始思维中,血是与生命等同的。在尚血者的观念中,血具有某种既特殊又神秘的功能和效用。它既能避邪、驱鬼、福佑人类,又会带来种种祸害,故视之为血灵,故而才能成为祭天礼地的最高表达。在皇家的祭祀仪礼中,通过燎疳和掩埋,由血液象征的生命则会与天地共融,归于大千。而在更多原始和民间的祭祀中,血和肉通常是要被吃掉的。因而,血祭亦即“血食”。《韩非子·十过》中就说:“嗣子不善,吾恐此将令其宗庙不拔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因此,追本溯源来看,血食或血祀才是牲祭的本义。所谓血食,也就是“食血”。人类在狩猎阶段,茹毛饮血是自然的事。虽到后来,社会文明不断发展,但饮血习俗依然在一些后进民族中保存下来,他们认为,喝动物血,能使动物的力量传到喝血者身上。用动物血与其它食材相混加工而成的食物则是饮血习俗的文明化转向。


麟游当地的文化人也一直在做这种猜想:血条面或许是匈奴族汉化之后的结果?这是他们将面条作为农耕民族的食物,将食血视为游牧民族传统的一种思维,但他们也知道,这仅仅只能是无法靠实的遥远猜想而已了。
麟游是山区县,八成以上皆为山地,以县城的所在地来看,西南皆山,东部为塬,西北方是覆土的山岭和梁峁,因此,地处县城西北方向的两亭和酒房一带,过去的农家人在春节时有做血条面的传统,但最为地道的,还是要数页(麟游人读xue)岭一带的农户,因为此地田土相对平阔,小麦种植较多,故而才更盛行此食。
平原年岁短,山中日月长。尤其是山里的冬季,霜雪覆盖,道路阻隔。人们需要亲友和食物的陪伴,才能度过这漫长的封冻时光。十几年前的麟游山区,冬菜是极其缺少的,百姓能够储藏的菜蔬也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这时候,幸好有喂养了一年的家猪,将会给他们青黄不接的味觉期许带来安慰。杀年猪是中国人的普遍习俗。因为在春节里,亲友相聚,祖先的亡魂也要归来,和族人们一起感恩天地,共话丰年。猪也便成了祭祀和宴请仪式里的重要角色。


入冬以后,屠夫走村串乡,开始忙活,农家人的烟囱里不间断地冒出炊烟。那是妇女们在烧开水,男人们则协助屠夫安妥家猪。这时节,气氛一度是紧张的,在猪惨烈的嘶叫声中,不少的小孩子已经被吓哭了,在紧张、忙乱而刺激的氛围中,时空是乱叠且杂灰的……直到那如同火山熔岩一般的猪血从伤口里喷涌而出,咕咕冒泡,这时,孩子和猪才都停止了叫喊。
短暂麻木的思绪被重新接通,人们像是经历了一场梦。
在这种场景里,老年农妇的利索和冷漠是惊人的。看吧!平日里慈祥的老太太,面对带猩红的血液却丝毫没有惊诧和畏惧。她们麻利地将猪血端到一边,将手放进去不断搅拌,因为若不及时,猪血就会在寒冬里很快凝固。经过搅拌的猪血还需用网罗过滤,将其颗粒状的杂质清出,然后再加入适量的食盐和调料,且加入适量温水,再行搅拌,等血液的红色变得匀匀而有腥绒之感时,便可以停下来了。


过去做血条面,是用三色以上的小麦粉相合,麟游人的经验是,面阳山坡生长的红小麦最好,为使面食蓬松而劲道,十斤面可放一钱碱,然后将备用的猪血徐徐倾入,一边用手不断搅拌,先拌后搓,以稍硬为宜。因为血液里加了盐,胶着感增强,因而此面也就比其它的和面要费力,血液与面粉的比例也很关键,它不仅关乎韧度也关乎颜色。面和好后,通常需要醒三十分钟,然后再进入揉面环节。关中人讲,“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在血条面的制作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正是这不同力道的千搓百揉,再加杖擀,才使得面粉具有了意想不到的劲韧口感。手拿擀杖的农妇们显得比平日里更要神采奕奕,一遍一遍的碾压,直至面片不足一毫米薄厚为佳。在幽暗的农家厨房里,血色的面片被扬起,满含着生命的张力。


面擀好后,要用热化晾温的大油反复擦拭,直到不相互粘连为宜。这时候,面可以一反一正相折叠,用大摆刀将之切成细条,越细越好。刀工了得的农妇们,此刻正是炫技的好时候,在其娴熟且谨慎的快刀下,血与面的邂逅与缠绵才真正促使了血条面的产生。
与关中诸多面条生面沸煮不同的是,血条面属于蒸面。富有经验的老太太将血条面半斤一坨,稳稳码放在甑笆上,铁锅旺柴,高笼厚盖,二十分钟后,半熟的血条面便可以出锅了。
这时候,守在一旁的小孩子们早已经迫不及待了,趁热拈起来就往嘴巴里放。不过别急,少了后面制汤的环节,血条面的真实魅力尚无法完全展现出来。
做汤首先要制菜,麟游人把这些菜统称为搭头菜。搭头菜有三种:底菜、漂菜和臊子。做底菜所用的食材是红萝卜、蒜苗、黄花菜、豆腐条和黑木耳,切丁后旺火略微翻炒即可。漂菜所用的则是鸡蛋饼、蒜苗和韭菜,这种方法在西府地区甚为流行,摊好的鸡蛋饼被切成指头蛋大小的菱形状,蒜苗或韭菜则被切成碎渣。臊子的做法是将肥瘦切小片分开,先将大油入锅,旺火热化,然后将肥肉丁倾入翻炒几分钟,等油脂泛出后的肉丁有了不少汤油,再将瘦肉丁加入翻炒,等肉炒至七成熟,再将醋、食盐、五香粉和辣椒面一一加入,文火略翻十至十五分钟。


搭头菜做好后,就可以烧汤了。先放少许菜油热锅,然后生姜末、葱花或蒜苗丝略炒,然后加入适量肉汤(这种肉汤以当天现杀的“项圈肉”熬煮的为最好),稍微加热再倒入清水,烧至煎沸,然后再调入臊子、食盐和醋等(切记少醋多盐),一锅香喷喷的汤头便大功告成了。这时候,早已放凉的血条面需要在热汤里冒一下,通常三分钟左右,但面要放的很少,一两筷头为宜,和西府地区的“一口香”近似,接下来,冒些热汤,撇上漂菜,放入豆腐条,然后再将底菜加入。于是,黑、白、绿、黄的鲜亮之色群英荟萃,在血条面深红色彩的映衬下显得热烈而炫耀。
据老人们讲,传统的头道血条面,大多是配着杀猪菜来吃的。当日尽管有槽头肉(项圈肉,猪脖子那一圈)炖菜、炒心肝等的新鲜肉菜,但在嗜面的关中人的习惯里,血条面才是作为主食的真正主角。你想想,在粉妆玉砌的寒冬里,一碗碗热腾腾的血条面端上来,再抓一个热馍馍,绵柔稀和的血条面,劲道温软的白馒头,一吸一咬,边吞边喝,实在是饕餮酣畅,舒服无比啊!



麟游的温度要比关中低至五六度,因此才能在隋唐两代成为皇家的避暑胜地,但对当地的老百姓而言,在漫长而寒冷的正月里,最好是少些劳动的细节为宜,因此,颇耐储存的血条面可以陪伴农人们从入冬一直到来年的春天。
可如今,在城镇化的浪潮中,麟游农村的空心化已经非常严重,大量的农户迁居城镇,养猪的农户也就极为罕见了,因此,不仅是传统的手工制作血条面的技艺已改为机械加工,而是这种食物所赖以存在的精神空间,也已经越来越稀薄了。那种众人欢聚共食的场面,是农耕文明中熟人之间的默契表达。

血条面主要是用猪血,也有用羊血和鸡血的,据说鸡血所做的血条面最滑腻可口,但因鸡血难得,因此很少有人能吃到。近几年,麟游血条面开始走出本土,向它地蔓延。另外,由于麟游县境旅游业的渐兴,血条面的馆子也多了起来。因此,该食也必然会逐渐突破自身的旧有传统,在时空次序和工艺手法上都有所改变。虽然食物愈来愈唾手可得,但不少的人们都在慨叹,现今的诸多食物已经很难寻觅到旧时的那种本味了,但其实,食味的体尝不仅在于食材本身,也在于我们种植、喂养、期待、收获、加工、品享,以及由此而连接起来的族群记忆,甚至是与实际气候和故乡土地的情感关联。因此,一种食物若是越来越沦为口舌之欲的“吃食”的时候,即是印证了与之原本契合的农耕文明的无奈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