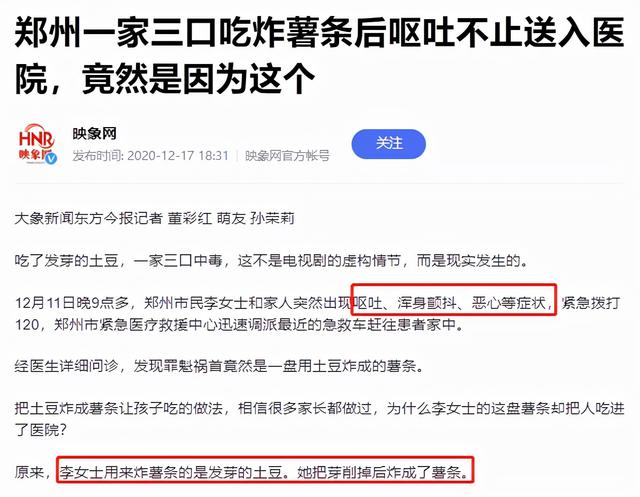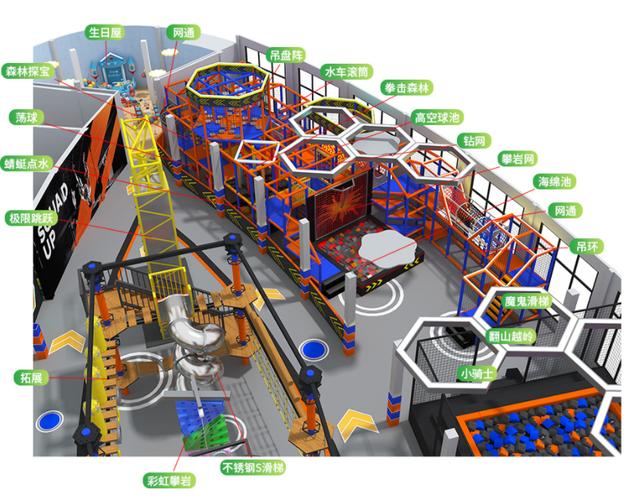文 | 张艳芳
母亲节那天,朋友圈都在向母亲祝贺,我却发现母亲已经离开我们两年了。
记得小时侯,学习英雄人物的事迹,在作文中写到,英雄虽然牺牲了,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实际上,对于有些英雄我已经淡忘了,但过世的母亲一直在我的心中。母亲去世后,我们姐弟四人回忆起母亲,对于一些社会性的话题,我们经常从母亲的角度说起。这件事咱娘会怎么说,这个人咱娘会怎样评价。我们的谈话,使我觉得,母亲活在我们心中,永远。
母亲生于1936年,1949年建国的时侯,已经14岁了。对于建国以来农村的变化,她都亲身经历过。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大炼钢铁,人民食堂,人民公社,一直到包产到户。说起这些事情,她还会说一些当时她的看法,还要加上具体事例。
母亲小时没有上过学,建国后,得益于国家开展的识字班扫盲,使她可以看书看报。由于祖父和父亲都在外地工作,她还能够给他们写信。虽说信中夹杂着一些错别字,但是每封信都能把家里的事述说明白。有时,还会为别人代笔写信。大约我上到小学三四年级时,能够写信了,她就不再写了。她的文化水平,同时代的人中,可说是高水平。
建国后,我们国家一穷二白,我国工业化的基础薄弱,都是靠全国人民的人力辛苦劳动干出来的。对母亲这一代人来说,那是一个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的时代。她们这代人,付出的体力劳动是最多的,尤其是她这个年龄的女人。她们的上一代,因为小脚的限制,无法从事一些体力劳动。而她们,没受过缠脚的折磨,使她们能拉地排车,能挑起扁担。由于父亲和祖父在外地工作,家中没有男劳力,母亲更比其他女人付出的体力更多。
母亲在我们家族中,是数得着的能干,里外一把手,把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生活虽劳累,忙碌,但在我们的记忆中,她从没有过灰头土脸,垂头丧气,唉声叹气。她的一生是体面的。在生产队,是劳动能手。我记得她在四十多岁时,还被评为村里的先进,奖励了一把锄头。一直到了老年,她还是很乐观。她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想起什么来,就笑死我了。”她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是爽朗的笑声。
母亲最能干的一件事就是种棉花,再把棉花变成布,给我们裁成衣服,整个过程她都能做下来。而大部分的妇女,只能做其中的一个过程,比如单纯的种棉花,纺线,织布,做衣服。她能参照着别人家的布料,织出同样的花格。她喜欢织布,而且织得又快又好。现在想起她坐在织布机上,梭子左右来回交换,两个踏板交叉上下,织布机有规律的咔嚓声,真有点和谐的舞蹈和优美的音乐的味道。可惜我们没给她留下织布的照片。
家里有一块专门种棉花的地,那是生产队分给每家一块猪饲料地,那块地离家很远。种棉花比种庄稼麻烦,下种,间苗,打农药,去顶心,去杈子,去边心,定期采摘,投入的劳动最多。但棉花能做棉衣,被褥,还能纺线织布,这是它更大的成果。正是由于母亲的勤劳,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每人只有几尺布票日子里,使我们穿的、铺的、盖的相对富足。我们姊妹穿的衣服也比其他人家的孩子体面些。
母亲还能做一件大部分妇女都干不了的活,就是扬场。扬场这活,对于男人来说,这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更不用说女人。每年麦子到了场里,脱下麦粒,借风力把麦糠和麦粒分开,就是扬场。需要会借风力,还要把麦粒均匀地洒开,还要落到固定的麦轮上。母亲那谐调的扬场动作,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母亲走后,我丈夫曾说我,你们姐妹三个加起来,也赶不上你娘。是呀,我们不如母亲会干的活多,也不如她干得好。她永远是我们生活中的榜样。

作者简介:张艳芳,山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退休职工,小学一级教师,2020年荣获山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志愿者。
壹点号山东金融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