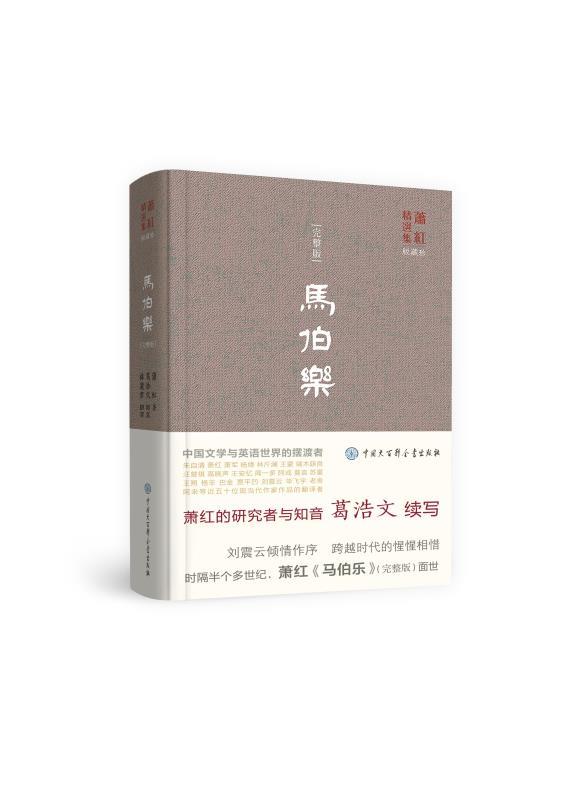萧红最好的两部作品,是在她生前最后的岁月写出的,是在她身心最为煎熬的情况下写出的,一部是《马伯乐》,一部是《呼兰河传》。地点是香港。
《马伯乐》没有完成,萧红就去世了,时年三十一岁。临终前两天,她在纸条上写道(此时她的喉管动了手术,无法说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这是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九日的事。
七十六年后,著名汉学家、同时是萧红的研究者和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先生,呼应了萧红的心语,给《马伯乐》写了续篇,就像高鹗给《红楼梦》写了续篇一样。萧红写那句话的时候,想着或许会有一个“别人”来做这件事,或许没有;就算有,她也不知道这个“别人”是谁,什么时候出现;但有一点她一定是知道的,如果这人出现,肯定是她的知音。
现在完整版的《马伯乐》(萧红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前九章,和葛浩文的续篇第十章到第十三章),联袂呈现在读者面前。

刘震云
因续篇是用英文写的,萧红的第二个知音就出现了,把作品由英文译成汉语的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女士。
续篇是不好写的,因为它受已有作品人物关系、人物性格的限制,受已有情节和细节的限制,受已有人物语言特征和叙述语言风格的限制。落笔之处,处处得有已有篇章的来历;或者,已有的因,如何结出现在的果。如果是结出不出意料的果倒也不难,读者也能认可,但续篇作者的创造力又在哪里呢?还需在故事结构、人物命运、人物关系的发展上出现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布局,这就考量续篇作者的想象力和文学表达能力了。
在萧红的创作生涯中,《马伯乐》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在萧红的其他作品中,如《呼兰河传》,还有另外两部写得较好的作品《生死场》和《商市街》,作品的灵魂或立足之处是真情实感,但到了《马伯乐》,却突然改成了荒诞和幽默。当然,在《呼兰河传》《生死场》和《商市街》里,萧红也不时显露出她幽默的本能和才情,但这些幽默还停留在作品的语言、细节和情节层面,到了她最后一部没完成的作品《马伯乐》中,她的幽默突然上了一个层面,即幽默开始体现在作品的结构上。这就出现了整体的荒诞。作品中的主人公马伯乐,生活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残酷岁月里,马伯乐是这个人口众多而实力弱小的民族的一员。日本军队一步步占领中国,马伯乐唯一的选择就是逃避。而且,一开始,是抛下家庭独自逃避。他从青岛逃到了上海。马伯乐本应盼着侵略者晚些来到,但他却盼着他们能来的快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上海把钱花光了,如果日本人占领了青岛,老婆就会带着孩子来上海找他;而老婆来了,老婆带的体己钱也就到了。这种民族大义和个人企图的悖反,也即“大”和“小”的悖反,就使作品在整体上出现了啼笑皆非的荒诞。接着,他带着家庭由上海又逃到武汉。他逃跑的足迹,就是侵略者的铁蹄接着踏来的地方,也算对“大”和“小”合拍的讽刺。
能把幽默上升到结构层面的作品寥寥无几,《马伯乐》算一个。
葛浩文是懂萧红的,是懂萧红创作的历程和变化的。他在创作《马伯乐》续篇的四个章节时,紧紧把握了这部作品的灵魂:幽默和荒诞。于是,他让马伯乐带着一家人又从武汉逃到了重庆。这是萧红在现实中的足迹,也是马伯乐继续荒诞的跟随。重庆是当时中国的陪都。在《马伯乐》续篇里,葛浩文出色地写出了一个民族“首都”的生活的喘息(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从全国各地逃来不计其数的难民),而马伯乐的喘息,又与生活和民族的灾难多么不搭调啊。一片乱象和哀嚎之中,马伯乐整天想的是如何卖包子,把包子卖给难民和底层劳动人民,相当于审时度势,发一点国难财——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卖几个包子,还能发财到哪里去呢?而且,任何事情都有两种可能性,包子或者卖出去,或者卖不出去;如果包子卖不出去呢?马伯乐也不发愁,他自己把它们吃了。大轰炸间隙,马伯乐喜爱躲开太太和家庭去街上闲逛。闲逛之中,路过一个礼拜堂,碰到一些山东老乡,相同的乡音之中,马伯乐感叹自己多舛的命运并不独特,难民便当得心安理得;闲逛的时候,他碰到一对日本夫妇,接着认识了另一个日本女人绿川英子,开始跟她学世界语;妄想用世界语来推广世界和平,这与当时的环境又是多么格格不入啊。一次出来闲逛,他把二儿子约瑟丢了。马伯乐声嘶力竭地喊叫和寻找,原来约瑟掉进了日本飞机炸出的大弹坑里。个人与民族的命运,总算在这里碰撞了。葛浩文是懂幽默的,通过这些人物关系、故事和情节的演进,马伯乐的命运一步步得到了荒诞的提升。
作品的结局是最难写的。马伯乐的出路在哪里?是这部作品在结构上的重中之重。葛浩文尊重萧红对作品架构的整体设想,让马伯乐带着二儿子约瑟从重庆又逃到了香港。因为从作品第一部和第二部前九章的框架考察,萧红对作品整体设想的关键词是:逃。萧红自己的足迹,也是从重庆去了香港。马伯乐和约瑟逃到香港之后,又经历了种种荒诞的事情。在种种荒诞中,葛浩文突然转折和正经了,让马伯乐和萧红在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的集会上见到了。这真是神来之笔。逝去的萧红,怕也不会想到在续篇里又与她作品里的主人公重逢吧?葛浩文在结尾处的最后一笔也力透纸背,将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合拢。但马伯乐结局究竟如何,留给读者自己寻找答案。
还有语言,萧红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那时的语言特质——含生活语言、文字语言和文学语言,均与现在的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有所不同。续篇的文字,却一板一眼地回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与萧红的文字水乳交融。这,显示了续者和译者深厚的国学功底。
《马伯乐》(完整版)这部作品是幽默的。大家知道,喜剧的底色一定不是喜剧而是悲剧,幽默的底色一定不是嬉笑而是悲凉。萧红写作状态最好的时候,是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临终前回溯自己短暂的一生,“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好在几十年后,还有一个研究者和译者,一直在表达对她及她作品的深情厚谊。正如葛浩文先生在序中所说,如萧红地下有知,当明白这情谊用心良苦。
惺惺相惜,说的是一种境界。对创造同一部作品的两个不同的作者而言,生活和文学的认识,能站立在同一个层面上,实属难得。
萧红尊重的鲁迅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诚哉斯言。
相惜不易。相惜是一种力量。
(本文为作家刘震云为《马伯乐》(完整版)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