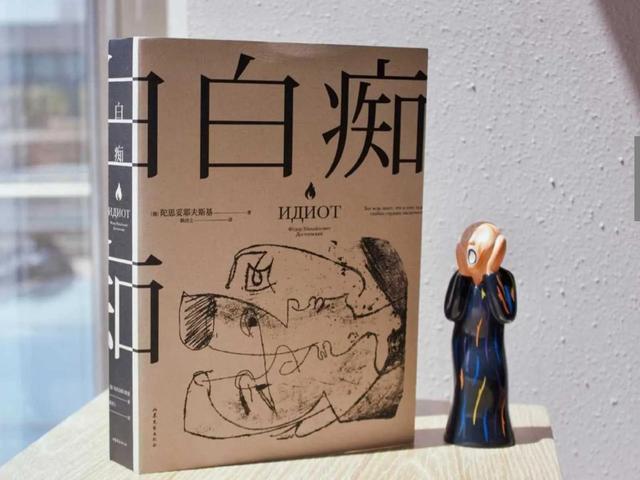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俄罗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就国际影响力而言与列夫·托尔斯泰难分轩轾,处女作《穷人》一鸣惊人,奠定了他的文坛地位,其后更以《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痴》《赌徒》《少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长篇杰作饮誉世界文坛。

传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文学成就及其传奇的人生经历,引发了传记作者对他持久的关注和探究兴趣。“探索人的奥秘”是陀氏一生的文学志业,而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奥秘”则是每个传记作者殷切企及的目标。传记将作家本人视为一个“人”——包括文本内外虚实相映的两个维度——的“样本”来观察和研究,这个“样本”的重要性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奥秘”恰是隐秘的人性之光的折射。
陀氏文学创作所触及和呈现的人性的广度与深度,是其备受关注和揄扬的主要原因。纪德曾谈到:“从思想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心理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虽然他首先是小说家。”作家在如此宏博的思想土壤上培植他的文学森林,其虬曲盘结的根系向着人类灵魂的幽暗深邃处执着钻探,将包括作家本人在内的潜意识和无意识中的劣根性曝光。
贯穿陀氏创作过程的自觉、自省、自我拷问是如此难能可贵,赢得了知音的广泛赞誉,如鲁迅所言:“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出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兼三职,既是“审问者”,也是“犯人”,更是以虚构的形式记录指控和辩护彼此盘诘的“写实主义者”。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与创作的认知和探索,是一个延续至今的“考古”和“拷问”的庞大工程。众多的陀氏传记作者,以独辟蹊径的观察和切入角度、个性化的叙事、鞭辟入里的剖析、逻辑严密的推理,对传主的人生经历、精神世界、文学创作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深入开掘,涉及他的穷困窘境、情感历程、对农奴制和民粹主义的看法、拯救弱者的善行和理想、文学观念的嬗变,等等。这些传记成为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和文学世界的最佳向导。
尤·谢列兹涅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领域有很重要的地位,“它终结了历史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曲解、误读,开辟了对陀氏研究的新纪元”。这部将近五十万字的传记可谓资料详尽,生动展示了陀氏历尽劫难、奇瑰非凡、悲欣交集的一生,特别是在两次面对死神的时刻——死刑考验和弥留之际,对传主心理活动体贴入微的描摹,使读者顿生震撼和共情,并引发对惘惘的命运感的沉思。
安德里亚斯·古斯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对陀氏的主要作品进行了精彩解析,将作家的人生和创作放在时代背景、现实境遇的时空坐标系中加以探讨,在历史、社会、美学等批评层面的交叉回环中,读者对陀氏其人其文的认识获得了更加开阔、新颖的视角。
多米尼克·阿尔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永恒的作家”传记丛书的一本,该书图文并茂,言简意丰,最大亮点是关于陀氏“复调独白”叙事艺术的阐发,时有独出机杼的心得和见解。
列昂尼德·茨普金的传记小说《巴登夏日》被誉为“狂热天才的编年史”。作者是一位医生,挚爱并痴迷于陀氏的文学人生,搜集阅读了与之相关的各种资料,甚至实地踏勘陀氏的生活游历之地,以小说的形式与陀氏展开一场异时空的心灵对话。《巴登夏日》属于“抽屉文学”,几经周折在纽约发表。发表一周之后,作者突发心脏病逝世。十年后,苏珊·桑塔格在伦敦街头“偶遇”此书,一见倾心,推崇其为“二十世纪最后一部伟大的俄语小说”。小说以其理智运思和心理揭秘的力度和深度,使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呈现出别具一格、耐人寻味的“虚构的真实”。
流放
众多传记尽管侧重点不同,但都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际遇的“关键词”,诸如贫穷、债务、死刑、流放、苦役、疾病、赌瘾、爱情,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一个经济拮据却注重教育的多子女家庭,16岁时,奉父命与哥哥米哈伊尔去彼得堡报考工程兵学校,他的官费资格被营私的校长剥夺,在亲戚资助下于次年入读此校。从此,陀氏进入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变局中开启了波谲云诡的命运征程。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为《祖国纪事》《俄国导报》等刊物撰稿,还自编《当代》和《时代》月刊,出版《作家日记》,创作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小说,逝世前一年出版的四卷本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氏的扛鼎之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两次远离俄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远行,一次是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而被流放鄂木斯克,四年苦役加六年兵役,十年后才获准移居彼得堡;一次是与安娜结婚后出游欧洲,四年后才回国。一次东行,一次西行,对陀氏的文学人生有着决定性影响。被流放前,陀氏因《穷人》受到别林斯基的激赏,一夜成名。流放十年间,没有作品问世,但生死劫难的考验为他积累了特殊的小说素材,被誉为“流放文学”鼻祖的《死屋手记》等作品皆取材于此。此后,他的每部作品几乎都围绕着流放期间开始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政治、文学、哲学、宗教等领域,歧义纠结,充满悖论,繁奥难解,陀氏备尝其苦却又不辞其苦,作品中揭示出的人性的复杂和灵魂的高蹈,恰恰来源于这种“形而上”的痛苦。
债务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深陷债务危机,他偿还兄长去世后留下的债务,负起寡嫂及其子女的抚养重任,为医治第一任妻子玛利亚的肺病,不得不频频举债,玛利亚去世后,还要无限期地供养继子的生活所需。凡此种种,令陀氏本就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几近崩溃。
他在给出版商亚历山大·克拉耶夫斯基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困境:“我像拉奥孔与蛇缠斗一样和我的债主们周旋。”“预支稿酬”是作家应对财务危机的主要办法,这种先拿钱后付货的交易方式迫使陀氏不得不“贱卖”作品,忍受出版商的苛酷盘剥,乃至更加剧了“钱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债务的枷锁愈箍愈紧,作家深陷泥淖,难以自拔。同时,为了在仓促的交稿期限内凑足印张,他无暇精心构思和推敲词句,有的作品难免文字啰唆、冗长,情节重复、拖沓,人物塑造潦草、粗疏。尽管总体上保持了一定水准,但作家疲于奔命、心力交瘁的状态还是严重影响了小说创作的质量。显然,这样的结果与他的才华和志向背道而驰。
疾病
身心承受的沉重压力无时无刻不在摧残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经,他患上了严重的癫痫病。据安德里亚斯·古斯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述:“从1861年起,他开始对自己的癫痫发作病史定期进行记录,并按发作程度划分为轻、中、重三种。在他去世前二十年里,按照这份记录,他一共发作过一百零二次。根据其他资料计算,数量比这个还要多二十多次。每次癫痫发作的间隔短则半天,长则半年,平均算下来大约是每月一次。每次癫痫发作都是在长时间的疲劳和抑郁状态之后,并且通常都有固定的先兆,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说的‘无法描述的狂喜’,不过,持续时间仅有短短几秒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借梅诗金公爵之口,详细描绘了这种源自本人的真实感受,“那一刻,我感觉和自己,和整个世界都达成了和谐。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和甜蜜,为这短短几分钟的极乐,我甘愿付出十年甚至整个生命”。“癫痫发作”对陀氏而言,是一把利与弊均极酷烈锐利的“双刃剑”,这种将疾病的巅峰体验和神秘感知充分文学化的处理方式,增强了陀氏小说的感性色彩和心理描写的深度。这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专属”标签,他人无从模仿。
赌瘾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金钱和财产的态度非常矛盾,他家无恒产且不善理财,却不拒奢华,挥金如土,几乎对所有人——从亲朋好友到街边偶遇的乞丐,一概有求必应,慷慨解囊。他拒绝继承父亲的庄园遗产,却为争取姨母的遗产与兄弟打官司。他为避债远赴欧洲,抱着大赢一把以还清欠债的妄想流连赌场,却一再失手,难以为继,陷入当无可当,甚至筹措不到回国路费的境地。
在他妻子的《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和《一八六七年日记》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豪赌”和不可救药的“赌瘾”有多处详细的描述。这一劣习使陀氏表现出明显的“人格分裂”和“信用危机”:作家对自己沉迷赌博深感“羞耻”,但他虚构的小说人物却在为赌博的“正当性”辩护,实际情况是陀氏被内心深处“冒险”的渴望和侥幸发财的期许结结实实“绑架”了,彻底沉沦,无法自赎。他一次次跪倒在妻子面前,不顾尊严地忏悔加赌咒,直到把安娜手上的“婚戒”也抵押出去,才在山穷水尽的绝境中,靠亲友的接济踏上返回俄罗斯的旅程。伴随陀氏多年的赌瘾不断耗去他艰苦写作得来的报偿,唯一的积极效应是催生了长篇小说《赌徒》。这部极具自传色彩的小说令读者看到陀氏真实的赌徒心理——赌博对他而言有一种“刺激和麻醉”的效应,“把自己的身家和性命都当作赌注”,这是写作与赌博在陀氏身上极为一致的反应。
爱情
毋庸置疑,“苦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的主旋律,它的频繁造访使作家如同置身“炼狱”,幸好与“苦难”相互激荡、缠绵厮守的还有“爱情”这一不乏甜蜜的副歌。马克·斯洛尼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3次爱情》是一本别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爱情传记,作者言道:“我的目的十分明确:只想尽可能全面地追述这位伟大作家对待女性的态度,坦诚地叙述他的追求以及他的两次婚姻,剔除对于事实真相的羞涩的沉默和常见的‘涂脂抹粉’。”因此,这本书的核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交往的史实钩沉以及对他的女性观、爱情观的深度剖析。
陀氏情路之坎坷一如他人生的一再受挫,除了两位妻子,他至少与帕纳耶娃、苏斯洛娃姐妹、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姐妹产生过超越友谊的情愫。特别是苏斯洛娃,不仅俘虏了陀氏的感情,还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两人交往之初,充满柔情蜜意,她首次写信向陀氏表白:“我对你的爱是美好的,壮丽的。”但分手时彼此留给对方的是身心的累累伤痕。苏斯洛娃在日记中写道:“每当回忆起两年前的生活,我便开始憎恨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第一个扼杀我信念的人。”但陀氏对苏斯洛娃的“无私的爱慕”,无论对方如何变化,始终初心不改,他在小说中将苏斯洛娃塑造成傲慢、叛逆的典型形象,《赌徒》中的波利娜、《白痴》中的纳斯塔西娅、《群魔》中的丽莎、《少年》中的阿赫马科娃、《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卡捷琳娜等人物大都以她为原型,在现实生活中,陀氏便称呼她“波利娜”。
如果说,苏斯洛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交往的具有独特文学意义的异性,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他更需要一个志同道合、同甘共苦的伴侣,给他日常的情感的具体支撑,给他漂泊孤苦的心灵以抚慰与呵护。幸运的是,他迎娶了安娜,一个善解人意、宽仁明理、持家有方并甘愿为之奉献一切的姑娘,使他得以排除琐事干扰,全力以赴投入文学创作,终于在有生之年完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巨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笔下的“人”,无不是善与恶、美与丑的角逐场,作家被苦难浸泡的身心从未失去抗争的意志和力量,他只怕“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怀着满腔悲悯,跋涉在文学的崎岖之路上,为自己、为所有人探寻救赎之道,不惜因之耗尽心血、燃尽生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魅力和无私情怀,召唤越来越多的同道踏上这条求索之路,这也是陀氏文学作品赢得的最为久远动人的回响。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川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