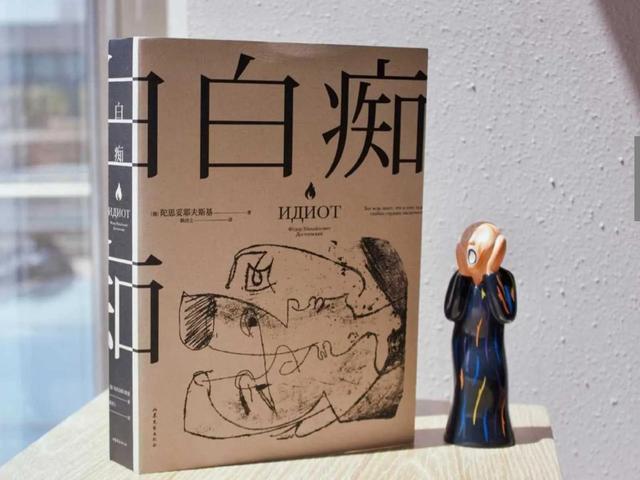《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长篇小说之一,它不像《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兄弟》那样出名,但依然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情怀与自我忏悔、自我惩罚和自我救赎的思想一部优秀的小说。
小说塑造了一个基督式的主人公梅诗金公爵,他无限的基督式宽容最终毁灭了一个爱他的女人、一个他爱的女人和他自己本应该得到的幸福,又不停地论述他是多么的宽容,以至于会原谅罗果仁那样的为美色疯狂的杀人犯。

梅诗金公爵自幼失去双亲,由帕甫里谢夫抚养。因为精神疾病和癫痫症,他被送往瑞士进行治疗。
数年以后,26岁的公爵乘火车返回彼得堡这座对他来说其实陌生的城市,物质上身无分文,精神上对俄国首都交际圈复杂的人情世故一窍不通。
但他这种绝对真诚、善意和宽恕的走直线态度反而深刻地穿刺进了其他人物毛线团一样盘绕的关系网当中。

公爵有一颗“基督”般的心,他并不愚笨,相反,他所见、所感如同X光线一般直照他人内心。
爱众生太难了,所以有了“白痴”。
公爵的爱是仁慈的博爱,他的同情是广泛的同情。
爱有等差,同情作为人最基本的美德,也不是无限的,它有边界、有阶级壁垒、有大小差异。
公爵的同情、博爱则不同,跨越了种族、阶级、善恶,是一种广泛的同情。他的爱可以给予每一个人,不管那人是否有罪。
这大概和陀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时所见,哪怕最罪恶深重的人也会向上帝忏悔有关,公爵也相信俄罗斯民族就有这种根植于基督信仰的民族性。
因此,每个人都能得到宽恕,只要他能够忏悔,做灵魂的自我检讨,不断校正自己的行为,都可以重回心灵的纯洁性和单一性。公爵所作的也正是这种言传身教的感召。
然而正是这种对所有人都敞开而坦白的一腔热忱,让公爵失去了他这个身份应有的,属于贵族的分寸感,尤其在登报构陷他却依然选择宽恕众人,和打破花瓶当众失态两章中表现明显。
前者印证他是个标准的基督圣徒,后者呈现他是个天真狂热的爱国青年。
譬如梅诗金公爵从一开始看到纳斯塔霞的照片,就因其看到了痛苦而想要救赎。因此当他看到那个从小就遭受痛苦的纳斯塔霞时,他以一种骑士的悲悯精神,一种悲悯的爱,一种对可怜的孩子的爱,想要救赎纳斯塔霞。
而纳斯塔霞不断地在戏弄梅诗金公爵与罗果仁,对梅诗金公爵的感情像爱情又不像爱情,就像我一位朋友说的那样:“很像一个罪人在面对圣人时的感受。”
罗果仁家财万贯,一心喜欢纳斯塔霞,也一直被纳斯塔霞抛弃,在最后书的结尾处,他杀死了纳斯塔霞,公爵却觉得罗果仁是个可怜人。
还有伊波利特,他贡献了全书最华美、最揪心的章节,那是临死之人的自白。
“既然这不知何日方休的筵席一开始就唯独认为我是多余的......就连此刻正在我身旁一道阳光中嗡嗡作声的小苍蝇,也是这筵席和合唱的参加者,也知道其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它也热爱这一席之地并感到幸福,唯独我被淘汰出局.....”
《白痴》这部作品是一场极致救赎的失败,梅诗金公爵并没有能撼动这张根深蒂固的网,他并不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仍然回到他那瑞士的净土。
当善良成了白痴,仁爱变成无用,狂暴显示为力量,怯懦装扮成理性,美命定了要被践踏和毁灭,恶却愈加肆无忌惮、扰乱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