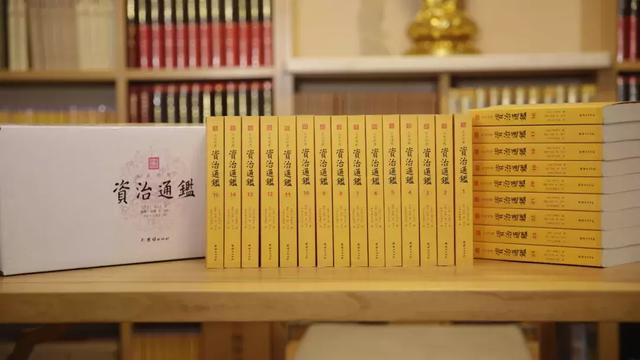司马光像。 (资料图/图)
从高中时开始陆陆续续读《资治通鉴》,后来考入大学读了历史专业,遂经常重读,养成习惯,转眼四十多年了。不敢自诩有什么真知灼见,不过要聊起《通鉴》,还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说说。
《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1019-1086),生前身后知名度甚高,童年“砸缸”的故事广为人知。近年曾有著名收藏家与北大教授在电视节目上争论此事真假,归结为司马光的时代有没有缸。其实无论《冷斋夜话》还是《宋史》的记述,司马光砸的都是“瓮”。这里所说的“缸”是大口的陶器,有釉,而“瓮”小口大腹,是瓦器,无釉,属粗拙的陶器,两者制作有所不同,今天在陕晋豫各地仍可看到“瓮”。“缸”“瓮”一字之差,当年两位专家的讨论跑偏了。
司马光一生最成功的事业,主要不是政治家,不是创造历史,而是书写历史。他用十九年时间,编成了354卷的《资治通鉴》(正文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记载了从东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这1362年间的历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作品。一部二十四史,《通鉴》涵盖了从《史记》到两《五代史》的十九史,总体来说,其价值不在正史之下,这是无人能及的成就,是今天的专家学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资治通鉴》得到著名学者钱大昕、王鸣盛、陈垣、陈寅恪等人的好评,也得到政治家曾国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高度重视。政治家读书,多揣摩形势策略,斟酌得失利弊。学人则侧重《通鉴》的史料价值和历史眼光,讲究拿《通鉴》和正史、文集、碑碣、野史对照,一是比较《通鉴》哪些写了哪些不写。比如灾异天象,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所记较多,《通鉴》正文里大幅减少,有些则移入《目录》,反映了汉宋时期对“天人之际”的不同认知,也反映了司马光的史家视野里对于人事的看重。更重要的是《资治通鉴》突出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传统长期延续,政治传统有变动有继承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对中长时段的重视,不局限于一时一事的记述。这样中长时段的历史书写,笔则笔,削则削,与大量史料之长编自然不同。《通鉴》呈现了中国历史的厚重感。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手卷,现藏国家图书馆。 (资料图/图)
就具体记载而言,如《通鉴》永徽六年(655)记萧淑妃诅咒武则天“愿他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蓄猫”。此条颇为人引述。然同书长寿元年(692)云:“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如能通观《通鉴》前后,可知“宫中不蓄猫”之说不可信,读《通鉴》者应不至于断章取义。
又如贞观二年(628),《通鉴》记“畿内有蝗”,“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细读该条,可知此处实为沿袭唐人旧说,属于唐史官阿谀本朝先皇之历史建构,见于唐人吴兢所著《贞观政要•务农》,以及《旧唐书•五行志》《唐会要•螟蜮》《册府元龟•感应》诸书。但是同样记载再多,也没有说服力。虽然《贞观政要》云“京师旱,蝗虫大起”,《通鉴》作“畿内有蝗”,笔法有所收敛,但“蝗不为灾”之说断不可信,不必讨论。从常识出发,即便不参考有关各书,也应该不会轻信《通鉴》所述唐太宗吞蝗虫的故事。
又比如,《隋唐嘉话》卷上:“太宗尝止一树下,曰:此嘉树。宇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常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头谢曰:南衙群官,面折廷争,陛下尝不得举手。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有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帝意复解。”《新唐书•宇文士及传》略改一二字。《通鉴》则只记太宗批评宇文士及之语,而删去士及辩解之辞。司马光修史之意在劝谏,且暗寓褒贬,其不取宇文士及巧言善辩之例,对史料加以裁剪,熔铸成一段记事文字。虽不加议论,读者于此可以深思。
贞观之治流芳青史。贞观四年(630)书“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这是在贞观“元年关中饥,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的前提下取得的转折性丰功伟绩,只是转速过快,十分生硬,显然是贞观年间为政治要建构而成的政绩。“终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可以取此后与之对比,一是贞观七年(633)记,“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可知四年死刑二十九人之说太假,司马光《考异》已予质疑。七年三百九十人死囚如期“自诣朝堂”之说亦不可信,自造佳话自我吹捧的痕迹太过明显。还可以对比贞观二十三年(649)十月:“上问大理卿唐临系囚之数,对曰:见囚五十余人,唯二人应死。”以及开元二十五年(737):“大理少卿徐峤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不栖,今有鹊巢其树。于是百官以几致刑措,上表称贺。”凡是唐朝需要歌颂太平景象,死刑数量特少就变成一个基本指标,一再用来渲染本朝德政之深入人心,教化大成。《资治通鉴》对贞观之治有很高评价,成为后世读者贞观想象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通鉴》又记述了贞观历史的若干疑点,供读者参详。司马光未必是有意并列这些材料以示存疑,但他客观述史的态度,使他有意同时保存了旧史中这些有趣的类比,包括李世民君臣粉饰太平的努力与做作,而不是盲从某一书某一事的旧说。所以说,历史是历史,史书是史书,也不可能将二者简单等同起来。
目前《资治通鉴》读本有邬国义点校简体字本,据宋本整理,并有《通鉴考异》三十卷的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版,2017年新版,点校精审。元初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则有古籍出版社1956年的整理本,由史学前辈顾颉刚先生领衔,据清朝胡克家翻刻本整理标点,附入民国初年章钰据宋元明诸本作的校勘记,可谓集宋元明清诸本之长,颇便读者。古籍社本经中华书局一再重印,成为今日最通行的本子。学术界承认的援引格式遂署“中华书局1956年版”,其实并没有这样一种版本。中华书局1976年以后的印刷本吸取吕叔湘等先生的部分意见,改订一些标点断句不当之处。2011年中华书局第2版,电脑排版,清晰便读,可惜没有参考吕叔湘先生等意见全面改订,因为排版原因还新增若干错讹。今年中华书局已经启动《资治通鉴》标点本修订工程,新版本指日可待,是读书界之大幸,吾辈翘首以盼。
今年适逢司马温公诞辰一千年,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孙文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