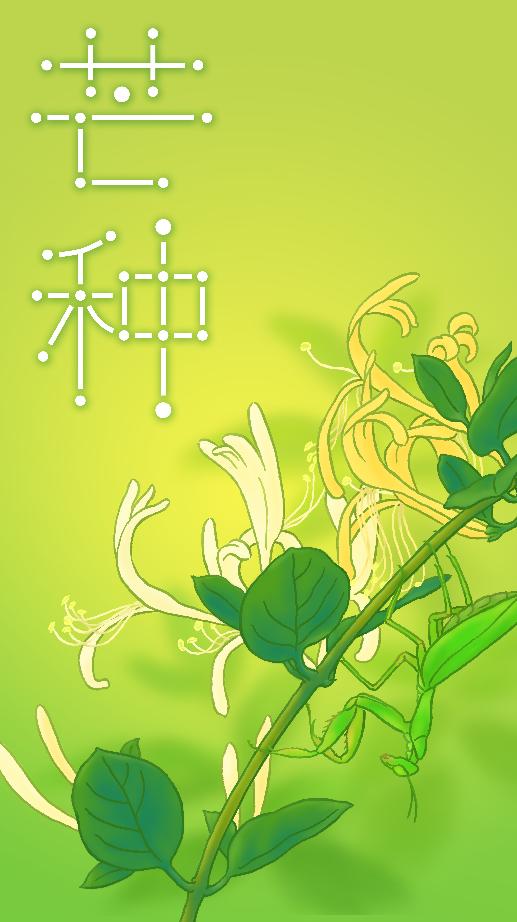曾仕强频道 王道管理咨询
中国式管理企业服务中心,用中国式管理帮助企业固本培元。

日习经典 开启智慧
原 文
长沮、桀溺①耦而耕②,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③焉。
长沮曰:“夫执舆者④为谁?”
子路曰:“为孔丘。”
曰:“是鲁孔丘与?”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
桀溺曰:“子为谁?”
曰:“为仲由。”
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yōu)而不辍⑤。
子路行以告。
夫子怃然⑥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注 释
①“长沮、桀溺”是楚国的两位隐者,失其姓名,以其居渡口,所以称“沮”“溺”。
②“耦而耕”即并耕。
③“问津”指询问渡口。
④“执舆者”指在车上执辔的人。
⑤“耰而不辍”为覆种而不停止。
⑥“怃然”是怅然失意的样子。
义 释
《四书集注》:时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济渡处。执舆,执辔在车也。盖本子路御而执辔,今下问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数
周流,自知津处。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犹与也。言天下皆乱,将谁与变易之?而,汝也。辟人,谓孔子。辟世,桀溺自谓。
耰,覆种也。亦不告以津处。怃然,犹怅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当与同群者,斯人而已,岂可绝人逃世以为洁哉?天下若已平
治,则我无用变易之。正为天下无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圣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张子曰:“圣人之仁,不
以无道必天下而弃之也。”
《四书蕅益解》:菩萨心肠。木铎职分。
《论语新解》:长沮、桀溺:两隐者,姓名不传。沮,沮洳。溺,淖溺。以其在水边,故取以名之。桀,健义,亦高大义。一人颀
然而长,一人高大而健。
耦而耕:两人并头而耕,谓耦耕。或说前后递耕谓耦耕。
问津:津,济渡处。
执舆者:执舆,执辔在手也。本子路御而执辔,今下问津,故孔子代之。
是知津矣:言孔子长年周流在外,应知津渡之处也。
滔滔者:滔滔,水流貌。字亦作悠悠,即浟浟,同是水流之貌。水之长流,尽日不息,皆是此水;因在水边,随指为喻。犹今俗
云:天下老鸦一般黑。
谁以易之:以,犹与也。言一世皆浊,将谁与而变易之。
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而指子路。辟读避。辟人之士,指孔子。避世之士,沮、溺自谓。人尽相同,不胜避,故不如避世。
耰而不辍:耰者覆种。布种后,以器杷之,使土开处复合,种深入土,鸟不能啄,以待时雨之至。耰而不辍者,亦不告子路以津处。
怃然:犹怅然,失意貌。
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与者,与同羣。孔子谓我自当与天下人同羣。隐居山林,是与鸟兽同羣。
丘不与易:孔子言正为天下无道,故周流在外,求以易之。若天下有道,则我不复与之有变易。隐者之意,天下无道则须隐。孔子
意,正因天下无道故不能隐。盖其心之仁,既不忍于忘天下,亦不忍于必谓天下之终于无道。

今 译
长沮和桀溺两人一起耕田,孔子刚好经过,叫子路去问渡口在哪里。
长沮问子路说:“在车上拉着缰绳的是谁?”
子路说:“是孔丘。”
长沮问:“是鲁国的孔丘吗?”
子路说:“是的。”
长沮说:“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
子路又向桀溺问渡口。
桀溺说:“你是谁?”
子路说:“我是仲由。”
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
子路答道:“是的。”桀溺说:“天下都一样混乱,谁能改变呢?而且你与其跟随逃避坏人的人,倒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逃避社会的
人。”说完,不停地犁土覆盖种子。
子路回来向孔子报告。
孔子怅然地说:“鸟兽是不可能同群生活的。我不和这人群居处在一起,又和谁在一起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图谋改革了。”
主 旨
孔子周游天下,却被隐者讥讽。
引 述
“辟人之士”意思是逃避坏人的人,是桀溺对孔子的称呼。“辟世之士”意思是避开乱世的人,是桀溺对他们的自称。从桀溺的角度来
看,“辟人”还不如“辟世”来得干脆而彻底。因为天下到处都是一样的混乱,哪里都有坏人,实在避不胜避,还不如避开整个乱世,不
必再到处奔波、忙碌。孔子的看法则是,像桀溺这样的态度,简直是哀莫大于心死。和鸟兽一样,只有生物性的生命,缺乏对文化性
生命的关怀。孔子坚持“辟人”而不“辟世”,永不放弃对行道的期望。不得不隐的时候,依然寄望于天下有道的可能性。天下太平的时
候,孔子根本用不着操心。反而是天下不太平时,孔子才需要想办法加以改变。就算到处都有坏人,也要明知其不可而为之。毕竟任
重道远,仍然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才能促使人类的文化生生不息。
子路向长沮请问渡口在哪里,长沮回答孔子一定知道过渡的地方,是一种讽刺,也是表示轻视的意思。桀溺更直接反问子路,为什
么偏要追随“辟人”的孔子,却不知道和他们这些“辟世”的人在一起。两人都不告诉子路渡口的位置,用意即在刺激孔子,暗示孔子不
如放弃“辟人”,转而“辟世”。

生 活 智 慧
(一)曲高和寡,层次较高的人,往往要承受层次较低的人,某种不明事理却又自以为是的批评和讽刺。经过长时间的考验,我们
才明白孔子对人类文化的关怀,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
(二)站在不得不隐的立场,实在不得已,才暂时退隐。仍然随时注意机会,永不放弃济世的心愿。始终怀抱和人类在一起,共同
奋斗不懈的心情,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慈大悲,蕴含着无比的深情。
(三)孔子的退隐思想,是“辟人”而不“辟世”。有改革的理想,却不肯屈从无道的君王。因此不想隐却不得不隐,我们可以称为“道
隐”或“时隐”,与一般的隐者大不相同。
建 议
有机会造福人群,不应该放弃。客观环境若是不允许改革,也不必凭着一股狂热,横冲直撞。因为纵使头破血流,甚至牺牲性命,
也无济于事。孔子主张有机会好好表现,没有机会也不必自怨怀才不遇,而心生不平。看似消极实际上也是十分积极,这很值得大家
参考。

別 裁
长沮和桀溺,是两个隐士,一对好朋友,在并肩种田,孔子经过那里,不知是有意或无意的,教子路去问路,问过江的路口,
这“问津”是这篇文篇的“点题”,我们中国以后的文字上,所谓“指点迷津”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长沮就先反问子路,你替他赶车的
那个老头子是谁?这是明知故问。子路说,坐在车上的是我的老师啊!鼎鼎大名的孔丘。长沮说,就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子路说,是
啊!就是他。长沮说,既然是孔丘,他当然知道该怎么走,还要来向我们问路吗?他这话答得很妙,子路问的是车子应该走向哪里的
路。长沮答的不是车子走的路,是人生之路,长沮的意思是说,这个周游列国、到处还要传道的孔子,他现在“路”都不晓得走吗?他
这个话是很妙,很幽默的。
子路问不出道理来,就转过头来问桀溺,桀溺却反过来问子路,你是什么人?子路说,我名字叫仲由。桀溺说,你就是鲁国那个糟
老头孔丘的徒弟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滔滔是形容词,现代语汇就是潮流,当潮流来时,海水一涨,
浪花滔滔滚滚,不管好的坏的,统统都被浪头淹没了。天下皆是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浊浪滔滔,一股浑水在流,这情形又有谁
能够把它变得了,那洪水泛滥的时候,时代的趋势来了,谁都挡不住。并且他告诉子路:“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
哉?”这句话中的“辟”就是“逃避”的“避”;“辟人之士”,是指孔子,避开了鲁国,鲁国政治太乱,自己的国家他救不了啦!为了想实行自
己的理想,到处去看,是避开乱的社会,另外想找更好的环境,为“辟人之士”。桀溺是告诉子路,你跟着孔子这样的“辟人之士”,可
是人是避不开的,如现在的和尚出家,神父的入会,反正都没有离开社会,不过换了一个生活。哪里出得了家?真出家谈何容易?真
出家就是桀溺说的“辟世之士”,连这个时代都抛开了。离开这个社会,跑到深山里去,不和任何人打交道,这就是出家吗?永嘉禅师
曾经说过,当你的心不能平静的时候,跑到深山都没有用。不要以为到了山里,就是出家修行,有时候看到风吹草动,心里都会烦起
来。如果把自己的心修平静了,在任何热闹的地方,就和在山林中一样的清净,这是基本的道理。所以这一段桀溺对子路说,其实时
代是逃避不了的,你与其跟着孔子一样,觉得这里不对,就离开到另外一个社会,还不如像我们一样,自己忘记了这个世界,忘记了
这个时代,种我的田,什么都不管。他说到这里以后,再不说话了,拿起锄头,还是不停地种他的田。
子路碰了钉子,就回去把经过报告孔子,孔子听了心里很不惬意,脸色变了,很落寞也很难过的样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后世
自命为儒家的人,抓住这句话作为把柄,认为道家这些隐士都不对,说孔子在骂他们是禽兽,这些人没有国家的观念,不是人,是禽
兽。这是后世的解释,但我否认这种解释,后世的儒家根本解释错了。我的看法,孔子非常赞成他们,孔子这句话不是骂他们,因为
上面有句“夫子怃然曰”,孔子心里很难过,很落寞的味道,所以告诉子路:“鸟兽不可与同群。”鸟是飞的,兽是走的,而且鸟是海阔
天空由他飞,兽类之中,绝大多数野兽都在山林里,不在人类的社会中,飞的与走的不能摆在一起,换句话说,人各有志,各走各的
路,远走的就去远走,高飞的就去高飞。孔子接着说,其实我很想跟他们一样,走他们的路线,抛开天下国家不管,我还不是跟他们
两个人的思想一样的。换句话说,都是在忧世的,担忧这个国家,担忧这个时代,担忧这个社会,这种忧都是一样的,问题只是做法
两样。他们可以丢下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不管,只管自己种田去,可是我丢不下来。假如说国家社会上了轨道,我又何必来改变它
呢?就因为时代太乱了,我必须要牺牲自己,来改变这个社会的潮流。这就是孔子!所以我们知道孔子走的路线,比这些隐士们走的
路更难。明知道这个担子挑不动的,他硬要去挑。
我们这里引述历史一件事来补充说明:宋代王安石上台了,苏东坡这批人和他的意见不同、分歧,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党祸”,而王
安石所用的人都非常坏,所以这班正人君子都纷纷辞职。当时有人主张最好不要辞职,因为王安石下面这一批人,将来一定要把事情
搞坏的,你多占一个位子,使他们少搞坏一点,这就做了好事。这就说明挑这种担子很难,明知道要坏,可硬是不走开,占住一点,
少坏一点,虽然不能积极的挽救,也是消极的防止,孔子走的是这个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