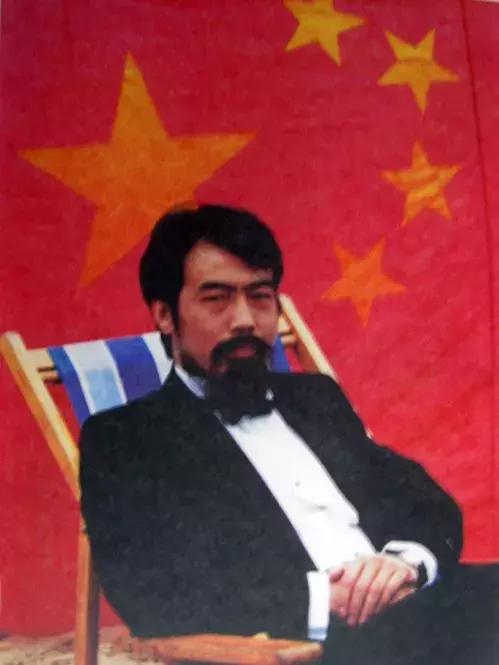(本文由Sir电影原创:dushetv)
《妖猫传》后,中国影迷圈的那个谣言应该破了——
嗯,Sir说的是,“《霸王别姬》是陈凯歌之父,陈怀恺代拍的”。
并不是说《妖魔传》有《霸王别姬》的高度,而是《妖猫传》的回勇,再次让我们看到曾闪耀在陈凯歌身上那种炙热。
“陈凯歌好的电影其实是有鸦片气息的。”
这句话来自影评人 @梅雪风。
雪风是Sir第一任主编,是我入行的引路人,他的影评极具洞察力,尤其是写人,往往寥寥几笔,就看到根上。
他写冯小刚,《冯小刚的成功学:笑的都是别人》。
这是一个矛盾体:一个油嘴滑舌的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眼睛常含热泪的理想主义者。他的行为和动机往往有一种有趣的对应,他往往用诚实来掩饰他的现实,也经常用油滑来掩饰他的善良。
他写周星驰,《周星驰的残忍一般人看不懂》。
周星驰才是个真正的愤青,但他隐藏得太好了,以至于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李安说周星驰讲的都是小孩子的东西,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为什么?一个人为什么如此孜孜不倦地执着于童话,在于他对于精神和物质匮乏的印象太过深刻。知道童话如此遥远的人才会真正地喜欢童话,但他在制造童话的过程中,却不由自主地将某种底层生活的惨烈杂糅其中。
所以,Sir今天特别邀请他,聊聊陈凯歌。
左起:王家卫、陈凯歌、侯孝贤、蔡明亮
还是八十年代,《棋王》横空出世,阿城倾刻间成为文坛新星,有一次两人骑自行车遇到了,陈凯歌喊住了阿城,慢条斯理地说:“听说,你也会写小说啦。”
这些段子中,当然也包括那个最耳熟能详的——
当张艺谋因《红高梁》获柏林金熊奖后,陈凯歌正在如厕,坐在马桶上冷笑:“丫不就是我一摄影师么。”
我们不是当事人,当然不知故事真伪,但这种桀骜不驯,却与人们因他的电影而对他的想象相当吻合:
这是一位气吞山河的导演,是一位有着洞察、重述中国人文化密码野心的导演。
在与他齐名的导演中,张艺谋拍的是人欲,讲的是人的底线需求,人应该是舒展地活着,而非被体制压成畸型儿和侏儒。
《红高梁》《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大概如此,《活着》更是在为“活着” 这两个字张目,原著小说作者余华曾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张艺谋伸张的,是最基本的人权。
《活着》
姜文拍的是革命的幻灭,宏大叙事背后的一地鸡毛。
《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都是这样,所以革命少年成年后最响亮的称呼就是SB,那些满怀壮志的归国华侨们,则用上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配合。而《鬼子来了》,则是对正统叙事下抗日战争及人民的解构,那颗带着反讽微笑的头颅在滚动中,才明白这一切都不过是自食其果。
《鬼子来了》
陈凯歌与张艺谋截然相反——
张艺谋拍活着,他拍人应该怎样活着,怎样有尊严地活着;张艺谋拍人委屈求全的惨烈,而陈凯歌则拍个体与世界硬碰硬的张扬。
与姜文相比,两人有相似之处,但他比姜文更偏执:
姜文是呈现幻灭,而陈凯歌却拍的是即使幻灭,但幻灭的烟火也好过平庸而无声息地活着,就算是个SB,那种不管不顾的疯魔也有一种超越常人的诗意。
简而言之,姜文是为幻灭心痛,而陈凯歌是爱幻灭;姜文是动物伤感,而陈凯歌则是悲壮的哀歌。
他在这种幻灭中,看到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慷慨,一种极致的单纯、一种向死而生的壮烈。
左起:姜文,陈凯歌,冯小刚
2
所以在他的电影中有着两种不同的情绪,一种叫虚无,一种叫沉溺。
虚无指向甚广。
它指向理想,在《荆轲刺秦王》中,秦王的理想最后成了他野心的遮羞布。它指向中国的传统文化,《边走边唱》中弹断千根琴弦就能治疗目盲的药方只是一张白纸。它指向爱情,《妖猫传》中,所谓的生死同穴的爱情故事只是自私而又精巧的权力伎俩。
其实陈凯歌的世界里一片虚空,他不相信祖宗所留下、现世所信奉、将来所希翼的——所有这些都透着一点即破的漏洞。在陈凯歌早期的电影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种处处踏空的愤懑,是一种穷追不舍的批判。
但从《霸王别姬》开始,他开始找到了他的解脱之道。
他的解脱来自相信,这是一种相当空幻却又有禅机的说法,却是解读《霸王别姬》之后大部分陈凯歌电影的法门。
它在《妖猫传》中,是李白那悲喜交集的一滴泪,他感受到了美,也感受到了美背后的苍凉,但他仍然愿意去礼赞它。也是杨贵妃的冷眼赴死,她看到了唐玄宗想推脱责任的小伎俩,却愿意用死来掩盖那些龌龊,用生命来完成他们的诺言。
它是《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这个审美至上者,坚守“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少一分一秒一个时辰,都不是一辈子”,但最后他发觉所有的坚持只能是戏时,他真的在舞台上拔剑自刎,用死把自己活成戏剧。
它甚至是《荆轲刺秦王》里的秦王赢政,“一统天下的大愿”激励着他攻城略池,让他义正言辞地杀人,但他渐渐发觉这并非自己所想的那么纯粹,他坑杀赵国儿童是内心虚弱的泄露,而荆轲最后的嘲笑则让他不能逃避。但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举起“一统天下的大愿”这个幌子死扛,即使它已经变脏。
他们都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空洞,却用一种近乎西西弗斯的徒劳无功为他们信奉的东西献祭。
在这里,理想主义的意义,不在于理想的正确、伟大,反而在于它极致的空洞——
为了这种空虚而浪费终生,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美。
3
这是一种极度充血却又极度空虚的状态,所以陈凯歌好的电影其实是有鸦片气息的。
而他最好的角色也有着吸食毒品后的精神状态。
这里面包括《荆轲刺秦王》中李雪健饰演的秦王、《霸王别姬》中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以及《梅兰芳》中孙红雷饰演的精神孪生兄弟邱如白,包括最近上映的《妖猫传》中辛柏青饰演的李白、《十分钟年华老去·百花深处》中冯远征饰演的疯子,还包括同样由张国荣饰演的《风月》中的忠良。
他们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处在现实与幻境的分界上、在理想与欲望撕裂的地方、在黑暗与光明相互吞噬的所在。他们的浪漫与悖谬,脆弱与强悍,都混然一体。
陈凯歌热爱这种撕扯,清纯的理想与浊重的欲望相遇,灵魂飞升,但沉重的肉身却在下降。
他们在毁灭中自我完成,在自我完成中毁灭。而陈凯歌在旁边泪眼婆娑,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所以他对日常是没有感觉的,日常不能给他带来那种超越凡俗的情感强度。
这也是他的电影总是有着一种浓厚舞台腔的原因——
因为他要的不是现实,他要的是现实基因的乌托邦,所有人都纵情地生、纵情地死,无忌地爱、无忌地恨。
这也是巩俐在他的《霸王别姬》《风月》《荆轲刺秦王》中都不出彩的原因。
她原本在张艺谋电影中厚实的质地,在陈凯歌电影中,成了一种过于现实的笨拙,因为她能扎根,却不能飞翔。
4
陈凯歌的悲剧是——
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个平庸且越发平庸的时代,而且是个在价值观上欢呼平庸的时代。
陈凯歌本质上是个现世的反对者,或者说他是个所有时代的反对者,只有在这种反对的撕扯中,他才能真正指认出他自己身上、他自认为高贵的芳香。
我得有一个让我仰慕的人
活在这部电影里头
这些显然不是以“屌丝”“佛系”自居的现代人所感兴趣的——他们的痛苦是不被这个世界接纳,不能成为现世价值观中的成功者。而非陈凯歌近乎没事找事的精神洁癖,以及所带来的刻意跟这个世界及自我的找碴。
以前的众星捧月,到《无极》的众矢之的,也许让他很少经受挑战的骄傲真正遭受到了挫折,让他在《搜索》《赵氏孤儿》《道士下山》中完全失去了方向,这部最近上映的《妖猫传》,他似乎才稳住了心神。
陈凯歌在现实中经受了少许他电影中主人公所要经受的孤独之苦,而审美意义的痛苦和现实的痛苦还是太不一样了,他后期电影中所有的摇摆可能源于这种真实呈现在他现世中的落差。
他其实是个养尊处优的圣徒,用他虚构的丰盈痛苦来献祭他的志向与报负。
当然这并不是批评。
因为正是这种隔岸观火的虚构,才让那些精神的痛苦如此澎湃如此诗意,而如果过于逼近真实,那也许就会变成充满无法辨认的浑浊,以及一潭死水的麻木。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Sir电影原创,微信ID:dushetv
微信搜索关注:Sir电影
微博搜索关注:毒舌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