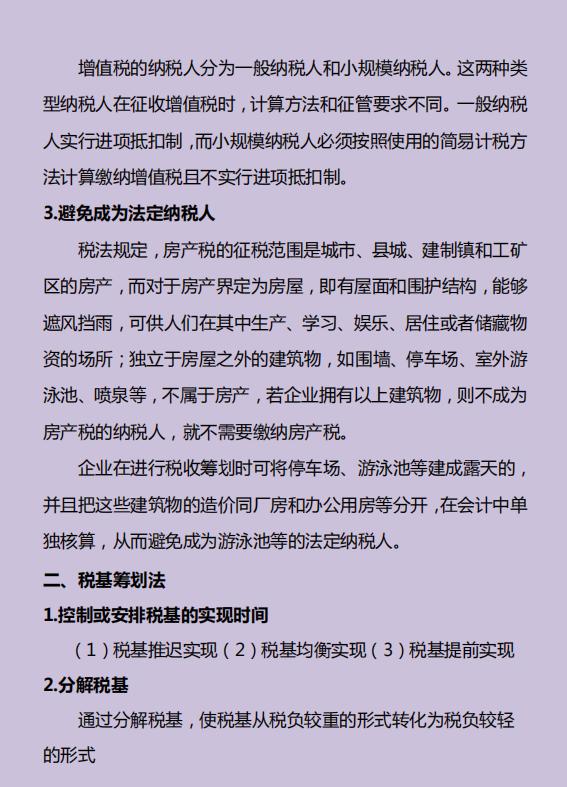作者:杨建平不管病毒在全球如何四处乱窜,春天还是如期而至,该开放的花儿依然姹紫嫣红,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梨花院落溶溶月打一动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梨花院落溶溶月打一动物
作者:杨建平
不管病毒在全球如何四处乱窜,春天还是如期而至,该开放的花儿依然姹紫嫣红。
百花种种,我最喜梨花。老宅子里那棵硕大的梨树梨花盛开,满树白云飘飘,满院花影重重,四处香气蒸腾,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秋季来临,那挂满树枝的脆梨,半红着脸庞,向我们摇头晃脑,至今想起,我还是垂涎三尺。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陕塬,也就是远古的周成王“分陕而治”的那个陕塬。那块“分陕石”如今还在我们市里博物馆当“震馆之宝”呢。有历史学家说,陕塬就是华夏民族人文历史的“肚脐眼”,陕西就是因为在这个陕塬以西而得名。高高的丘陵,似乎象山,但登上去之后,却是一马平川,又似平原。
我们陕塬人,祖祖辈辈都居住在一种叫“地坑院”的民居里。这种民居,不知始于何时,打我记事起,老人们就说我家的院子有百年以上。全村没有一间瓦房,全是平地挖个四方形的深坑,再在深坑的截面上横向掘进,呈圆拱形的土窑洞,用土胚或者砖在窑洞入口处砌上窗户、门,窑洞里用土胚还要砌上火炕,就可以居住了。一个院子有十孔窑、十二孔窑,其中一孔是门洞:连接院内到院上通道,人们出入院落,就必须从门洞沿着斜坡上上下下。门洞里安装有大门和闭锁的机关,以防外人侵袭,非请莫入。其它的窑洞又根据中国的阴阳八卦把它确定为主窑(上房)、次窑、伙房、磨坊、厕所等等功能不同的用项。一所院子又会根据周围的风水,定其上下左右,尊卑主次,有所谓的动宅和静宅,细分还有西兑宅、南离宅、北坎宅、东震宅等说法。这里的学问玄而又玄,只有村里的“先生”才说得清。
这种民居,因为就地取材,建设成本最低;又因为冬暖夏凉,运行成本低;一把黄泥一抹就焕然一新,维修更新成本低;深宅大院,门洞里一门紧关,既可高枕无忧,安全系数高。当地老百姓喜欢,建筑学家惊叹,外国人也常常来看稀罕。目前已经是驰名海内外的热门旅游景点。
日本人对这种建筑最青睐,曾经反复考察,叫它“生土建筑”,说它最节能。但这种建筑有两个关键的自然条件,一是土质,必须有厚层的结构稳定的白粘土,否则无法深挖洞后还百年无恙;二是当地的年降雨量不能太多,否则,地坑院内排水就会出问题。当然,除了优点外,这种民居的缺点是通风和采光不好。
我家的老宅,是一个拥有十孔窑洞的地坑院。院里一棵大梨树枝繁叶茂,长出院落地平线好多,好像高高撑起的一把巨伞,覆盖在院落的头顶。农村没有街道门牌,我们家在村里,就被称为“梨树院”。你是哪家的孩子?我是梨树院的孩子。你去哪里?我去梨树院。如此一说,大家都明白。
我在这梨花院落里出生、成长,又在这里结婚、生子,村子里每个院落的形状、位置,户型之间的距离,我都烂熟于心。黑夜里疯跑,也不会失足掉进院落。院落里每个犄角旮旯我都能闭着眼睛走去走回。黑夜里进出门洞、上茅房、喂猪、挑水、劈柴,啥都不耽误。
但外地人到这里,就很不适应。我记得中学时一个外地的高级知识分子下放到我们村里教书,满村子一个一个地坑院落,晚上走路险象环生,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深宅大院。这个老头为此专门买了一个手电筒,晚上照明。可是有一次晚上大雨瓢泼,手电筒照明效果不佳,他直挺挺走下深宅大院,摔断了腰,从此回城疗养,不再回来。多年后,我进城上高中,又遇到这位老师,说起这段往事,他立马摸着自己的腰,说:心有余悸、心有余悸啊!
我家院子附近是全村唯一一个篮球场,全村就一个篮球,宝贝似的,我想摸一下都够不着。一天我正在梨树下吃饭,忽然篮球嘭的一声掉进我家院子里,我扔下筷子就跑过去,抱起篮球一边拍打,一边大笑,院子上面沿口上围了许多人喊:快把球扔上来、快把球扔上来。我才不搭理他们呢,自顾自地可劲玩儿。几个青年气急败坏地从门洞跑下来,从我手里抢走篮球,跑了。
此后,只要篮球场上有人打球,我就呆在院子里盼着篮球掉下来,只要掉下来,我就狠狠过一把拍球的“瘾”。有一次,我一看篮球掉下来,就先把大门关上,然后再拣起篮球玩,气得跑下门洞来拿球的小青年一个劲地踹门。最后还是哥哥出来,从我手里要过篮球,一甩手扔给院子顶上的人。
还有一次,我正在院子里守株待“球”,篮球掉下来时碰上老梨树的枝丫,几个来回反弹,结果球砸在我的头上,我不顾两眼冒金星,还是抢上去捡球玩。等球被人家取走后,我才呲着牙喊疼,奶奶一看都起了包,急忙拿筷子从香油瓶里蘸一点香油涂在鼓起的包上,那香气弥漫得我连连哄鼻子。
不过,要说香,最香的还是每年春天满院扑鼻的梨花香。从院里看,花伞如盖,花影斑驳,香气缭绕,尤其是月光下,坐在院子里赏花,使我遐想纷纷,醉眼朦胧,许多神话故事都好像眼前飘过。从院外看,只见花团锦簇似一大朵祥云飘在地平线上,不见树干,不见院落。如果是傍晚时节,院子里升起袅袅炊烟,蒸腾在梨花朵朵之间,夕阳照射下,那种仙境,我想海市蜃楼不过如此吧。
我儿时特别爱吃梨,而且只吃我们家里树上的梨。村子里别人家的梨,我总嫌弃不脆、不甜、汁少、肉粗。秋天的中午,我一丝不挂地坐在树下的小板凳上,大口吃梨,梨汁顺着嘴角,顺着手指流淌,苍蝇便围绕我四处偷袭,我一边吃,一边赶苍蝇,一边还念念有词地骂道:这些死苍蝇,为什么老吃我?我身上的肉香?好吃吗!奶奶见状就走过来拿大蒲扇帮我赶苍蝇。吃完了,浑身已是汗水和梨水混合淋淋,妈妈就拿脸盆过来洗澡,抱我去睡午觉去。
一次围攻我的苍蝇群里混进了马蜂,我在驱赶和谩骂时,惹恼了马蜂,蛰得我扔掉梨子哇哇大哭,妈妈跑过来问是咋回事,我只说屁股疼,也不知道咋回事。妈妈一看才知道是苍蝇群里有马蜂,小屁股已蛰得肿胀起来。奶奶跑过来大骂“马蜂坏蛋”,同时拿起缝衣服的针就往肿胀处挑毒刺,我疼得又踢又打,挑完毒刺,妈妈又拿肥皂水洗了屁股,才消停完事。
爸爸在外地教书,很少回家,因此我对他总有陌生感。一次晚上全家在树下围着小饭桌吃饭,爸爸回来了,我远远躲在奶奶怀里看他说话。和大人说完正事,爸爸问了哥哥的学习,就开始逗我:你和谁最亲?我指指妈妈。还和谁亲?我又指指奶奶。还和谁亲?我再指指哥哥。还有呢?我不吭声,也不指了。这时,爸爸笑着拿起自己的挎包,掏出一种水果说:“我这里有香蕉,谁和我亲,就让谁吃。”我立马羞怯地一头拱进奶奶的怀里,哥哥高声叫喊着吃开了,我却死死地往奶奶怀里拱,不肯接妈妈递给我的香蕉。还是奶奶替我接了香蕉并抱上我进屋里炕上,又让我躲进被窝偷偷吃。
长大上学了,因为我家这棵老梨树,我在学校人缘好极了。
每当梨花满院时,一放学,同学们就会争着和我一起到我们家院子写作业。于是,梨树下的大石头上时常爬满写作业的同学。风吹落的梨花,我们会抢到手里,反复闻香,也会夹到书里。结果鲜花的汁液把书渗湿弄皱了。
到了秋天,香梨挂满枝头,同学们更是争先恐后往我家跑,奶奶、妈妈知道小朋友那点心思,就用捶布的棒槌,扔上树梢,打落一地梨儿,让我们解馋。也有淘气的小朋友要爬上树去摘梨子,奶奶和妈妈是坚决不同意的,不是怕他们吃梨,而是怕万一从树上掉下来,无法交待。我记得我们家这棵梨树的果子都是这样陆陆续续被人吃了去,从来没有摘了卖钱的心思。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那年冬天,我和哥哥都参加考试,哥哥录取了,我差一分未被录取。第二年夏季,我又参加高考,考中了。半年时间,这个梨树院接连考上两个大学生,也是村里唯一两个,村里人都说“梨树院风脉好、出人才”,有四邻跑上门祝贺,妈妈就摘下树上的脆梨,让人家吃,如果有孩子跟着,临走还要给孩子口袋塞上几个。
等我离家上大学时,满树梨儿早已光光。在收拾行李时,妈妈从一个陶罐里拿出几个梨子塞进我的行囊,说专门给我藏起来的,带着梨儿离开家乡,就不会留恋不舍,就会志在四方干成大事。
大学里我读的中文,看到“梨花一枝春带雨”“千树万树梨花开”“落尽梨花月又西”“梨花满地不开门”等诗句,脑子里总是闪现我家那棵花开满枝的老梨树,这一幕过完电影,才能进入诗句的理解,才能欣赏诗词的意境。当看到宋代晏殊写的“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时,我一下物我两忘,深深掉落进这诗情画意里,久久不能自拔。这就是描写我的梨树院,这就是我心中的诗句、梦中的情景。
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住进高楼大厦,总觉得没有老家的地坑院冬暖夏凉,接地气;见识了桃花、杏花、樱花、海棠、玉兰、丁香、桂花等等,但这些花只能“入眼”而不能“入心”。我心底里最美的花依然是梨花,而且是那棵老梨树上的梨花。每当女儿暑假,我总喜欢带她回到那座梨花院落,重温旧梦,几次醉倒在“梨花院落溶溶月”里。
到北京工作后,女儿也长大出国留学了。回老家也越来越少,忽然大哥在电话上说,新村改造,老宅子被推平,规划盖瓦房了。我急忙问:那棵老梨树呢?大哥回答:也已经刨掉,梨树木质细腻,正准备做几个做饭用的案板,有你一个。我听完,心里空落落的,也不知道大哥还说了什么,我只是“哦哦”几声就挂掉了电话。
前不久,回到老家,到处是新盖的瓦房、平房,还有两层小楼,许多人的门楼高大气派、瓷砖闪亮,但门头上的字却是“依玛内利”而不是“耕读传家”。我几乎不认识路,回自己的家也是东拐西绕,才找到。我梦中的梨花院落,已经淹没在一群新房之下,了无踪迹。梨树做的案板,我倒看见在新厨房正派着用场。
最近听到网红歌曲“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我就不自主的改词“我心中最美的花,白白的梨花香”。原本轻松的歌曲,我的改词原本也是搞笑,不知怎的,我唱着却出了“哭腔”、流了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