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己亥年。这一年,对于中国政治而言,似乎并无什么大事,但对于中国文学而言,这个己亥年却几乎成了一位中国文人的专属年号,因为就在这一年,一个叫龚自珍的文人,几乎以一天一首的速度,创作了315首诗歌,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己亥杂诗》,在当时,一个文人出本诗集也许不算什么,但时隔一个多世纪之后,我们发现,《己亥杂诗》更像是一支火把,照亮了这一年中国文化的天空。
龚自珍在己亥年的大爆发,其实缘于两点,一个是深厚的家学渊源,一个是抑郁的文人心境。龚自珍生于浙江钱塘县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之家,作为当地望族,龚氏自随宋南渡至清,已历四百多年,而龚自珍的家谱更值得炫耀,远的不说,从其曾祖父开始,已是四代功名,他们要么被封为朝议大夫,要么在内阁军机处行走,不仅都是官居上品,而且皆是饱学之士,而龚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更是了得,一部《说文解字注》,已经足以让其傲视学林。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龚自珍的文学发韧自然是占尽先机,而像祖辈那样功名卓著,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龚自珍从少年时代就立下的志向。然而,中国文人的大悲哀也正在于此。背负着家族的厚望,自己又是博览群书,志在必得,残酷的现实却让龚自珍陷入了巨大的痛楚之中。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龚自珍首次赴京参加会试,到道光六年(1828年)春,他连续八年参加会试,都接连败北,打击可想而知。也正是在科举失败的这八年间,龚自珍对封建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扼杀有了深入痛彻的思索,在他看来,以抄录四书、五经的注疏为圭臬的八股取士标准,绝对不能检验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学,而只能使天下学子“万喙相因”,“疲精神日力于无用之学”。正基于此,在道光三年(1823年),龚自珍连写三首《夜坐》,以“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直接对封建专制淫威下暮气沉沉的用人政策发出怒吼。这个夜中孤坐辗转难眠的江南才子太想找到求取功名的出口了,但这个出口于他而言,更像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

道光九年(1829年)三月,对龚自珍而言是难忘的,因为就在这一年,已经三十八岁的他在第六次参加会试之后,排名第九十五位,有了参加朝考的机会。对于这个机会,龚自珍看得很重,面对“安边绥远疏”这道天子考题,龚自珍更是动用了自己所有的才思,他根据当时的边防状况,大胆提出“以边安边”“足食足兵”的主张,以洋洋千余言,表达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然而,这纸答卷最终却以“楷法不中程”为由,未列优等,再次被朝堂忽视。尽管此后龚自珍也算在京城做了闲曹小官,但毕竟与其胸怀的凌云之志相去甚远,二十年的岁月蹉跎,最终却因书法不合规范而失去成为宰辅之材的可能,龚自珍只能拭一把热泪,徒唤奈何。
时间走到己亥年,这一年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北京城乍暖还寒,时年四十八岁的龚自珍抖一抖身上的寒霜,挂印辞官,悄然离开了他生活了二十年的京城。“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悄然离京的龚自珍看似走得很匆忙,其时心中的去意已盘桓多年,据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说:“先生官京师,冷署闲曹,俸入本薄,性既豪迈,嗜奇好客 ,境遂大困,又才高动触时忌,……乃乞养归。”这段文字基本可以看作是龚自珍辞官离京的原因。

“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己亥杂诗•其五》) 这首诗是龚自珍离京南下路上写下的第五首诗,虽然脱离官场,但龚自珍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以此来表达他至死仍牵挂国家的一腔热情,他不会想到,自己的这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日后会成为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名句;而更让龚自珍不曾想到的是,当摆脱了功名利禄的羁绊,当归隐林泉一路南下,这位大志难申的诗人,已经在文字中找到了可以任意驰骋的天地,他的目的地是杭州老家,一路上,他经河北,过江苏,出淮浦,入扬州,几乎无日不为诗,无物不入诗,完全将诗歌作为自己抒发胸臆的载体,尤其是在江苏镇江,龚自珍更是面对滔滔江水,濡笔立成,写下了这首千古传唱的佳作。“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 《己亥杂诗·其二百二十》 )这首诗,堪称龚诗中分贝最高的作品,在奔涌的文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面对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发出的响遏行云一般的呐喊,这种呐喊卷集着层云,夹带着风雷,而他的出发点,决不是出自对个人命运的自哀自怜,而是出于对家国命运的大关怀,出于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盼,他希望的是,“天公重抖擞”,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这种大情怀,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回溯一千年前,与在破蔽的茅屋中吟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形成对应,都是时运不济的诗人,都是一生漂泊的思想者,两人站在历史长河的两端,已经用他们声震寰宇的呐喊,完成了精神的对应,掀起了巨浪狂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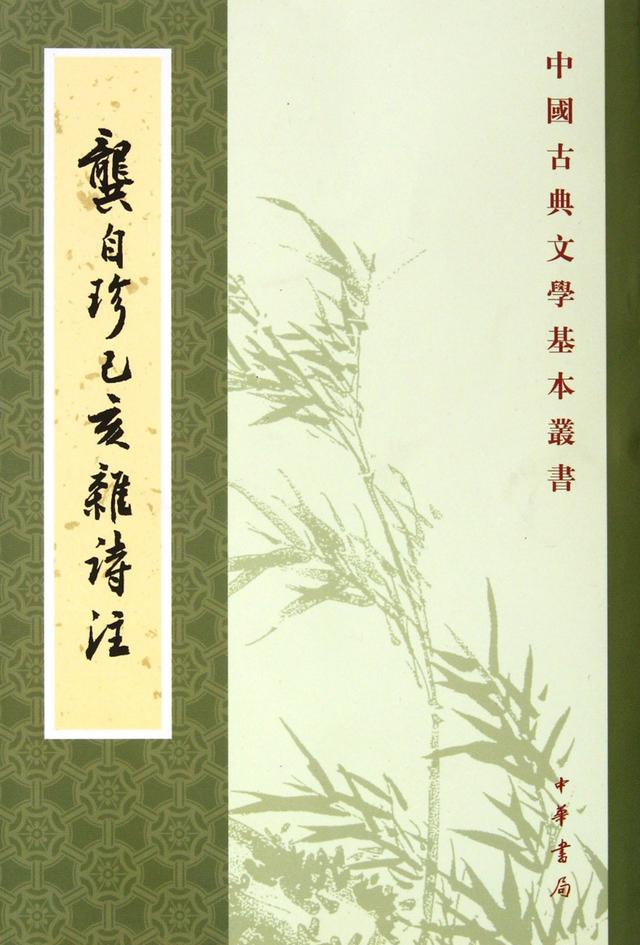
由此,“己亥”,注定成为诗人龚自珍专属的年号。在己亥这一年间,龚自珍先是辞官南归,继而又接眷南归,往返九千里,伴着九千里路云和月,龚自珍曾自言,“忽破诗戒,每作诗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于账簿纸,投一破簏中,……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发簏数之,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中有留别京国之诗,有关津乞食之诗,有忆虹生之诗,有过袁浦纪奇遇之诗,刻无抄胥,……乃至一坐卧、一饮食,历历如绘。”可以说九千里征途,对于龚自珍是一个自省的过程,是一个叩问的过程,更是一个将心绪由郁闷转向平和的过程,他将诗歌创作完全当作了自己羁旅行役的心灵之约,一个个跳动的文字,腾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的各个路口,最终构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数量最多并独领风骚的大型组诗。当龚自珍为自己这部创作于路上的诗集以《己亥杂诗》定名,他也许不会想到,在那个诗人寥落万马齐喑的时代,自己已经将“己亥”变成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年号,这个年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龚自珍死在49岁的盛年,彼时,他刚刚归乡不久,《己亥杂诗》也才修订完成,但就在一切归于平静之时,他却神秘地暴毙身亡。关于他的死因可谓众说纷纭,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却几乎是一致的,他被史家誉为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是他清醒地看到了清王朝已经进入“衰世”,是“日之将夕”,自他之后,波及魏源,中经谭嗣同、康有为、蒋智由、再到南社诗人柳亚子、苏曼殊乃至秋瑾和早期鲁迅等人的诗歌创作,都在以倡言变革、呼唤风雷、冲破藩篱为诗歌的轨迹。“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梁启超对龚自珍做出的这番评价,决非过誉之词,而是源于一份发自心底的尊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