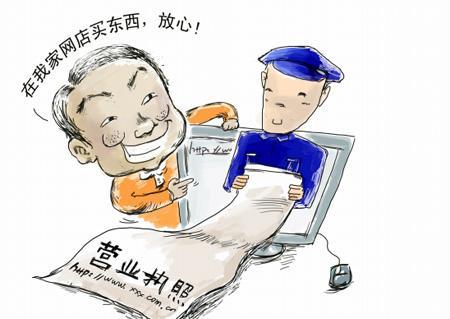引言
夷夏两族的长期冲突和交融,逐渐演化出中华文化蜕变的枢纽,正是从那时起,中华文化逐渐从早期的信仰鬼神发展成为更加理性的人文精神。自新石器时期,就不难看出夷夏两部族文化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二者长年累月兵戈相见,试图以武力的胜负来压制对方的文化繁衍。
商朝的族源正是东夷族,那里的人天生信仰鬼神,在他们心中上帝就是至高之神。也正是因为这样,商朝的统治者才十分信赖天命,坚信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之后,周王朝灭商建立新都则坚定地摧毁了这种信仰,建立起了别具一格的“德性天命观”。这不仅是朝代的更迭交替,更是中华文化发展蜕变的至要枢纽。自那以后,人们不再过度迷信鬼神,而是认为一个人的努力才是事情成败的关键性因素,中华文化也就此打开了理性之门。

秦统一六国之前,夷夏两族文化始终处于激烈冲突与融合的状况,等到六国统一之后,才彻底改变这种格局转而向南北两大文化格局发展。可是,不管是南北冲突还是东西冲突,本质都是长期从事农业或者畜牧渔猎的人们及其生活方式的争夺,并最终在某个时间点达成和解共生。其实,夷夏两部族的交战自新兵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二者都试图想通过战争的胜利来定义谁是共主。
某种意义上来说,商人可以称为是东夷人的后人,二者颇有渊源。不仅各种历史文献里显示商人与东夷人之间有着血缘关系,而且其祖籍部落——少皞部落就是东夷族里最有名的“鸟夷”。后来周人常常对商人称做“夷”,同样也证明了商人是出自东夷人。商人和东夷人彼此之间的紧密关系,除了他们都有着游牧渔猎的生活风俗以外,也体现在其长期生活范围的重叠性上,例如商朝王室子孙所居住的宅基地附近,也都同时住着大批东夷人。
而周朝则可以说是黄帝民族下繁衍生息、分化出来的一个部落,而黄帝部落又是夏族的前身。历史文献上显示夏朝最初的创立者禹就是黄帝的玄孙。当初随着黄帝民族逐渐壮大、聚落渐渐扩大,禹独立分划出一个支部——夏族,而在历史的发展之中,后期夏族的发展势头逼迫原黄帝部落,成为西方农业民族新一届的领导者,而周朝人就属于夏部落的成员。
当初,夏族独立分划出去之后就改为农耕,其政治统治的能量日渐强大,大部的黄帝部落慢慢都开始归顺于夏,成为一个诸夏部落集合,而剩余未归顺的黄帝部落则继续过着原有的游牧生活,这也就是“戎”与“狄”的早期源头。因为周朝人与夏族有着几乎相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周朝人常常自称为“夏人”,更把自己视作夏文化的传承者。

周超人和其他归顺的大部黄帝部落一样,都共同向夏族人学习如何转型成为农牧民族。周朝自身的农业十分发达,该族的创始者后稷自小就敏于农事,后稷去世后三次传位至公刘。公刘可谓是决定周族兴起的关键性人物,是他带领部族由原来的漆水流域向南转至渭水流域生活,而他的儿子庆节就开始建国于豳。
公刘死后第九次传位到了至古公亶父,《史记》记载,古公亶父再次从事后稷、公刘的事业,不断发展自身的农业。他的一生勤于政绩、行善积德更是频繁,国人都很爱戴他 。周
可当时部落内有一个积累已久的大问题,就是其部族长期处在与戎狄生活在一处,彼此之间大小争执不断。后来古公亶父发现一味的忍让终究是无法换来和平,所以最终决定带领所有子民转移至岐山脚下。虽然此地也并非全然没有戎狄,但是这里的空间足够广阔,可以保证周人不与戎狄完全混居。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古公亶父开始明确周人原有的风俗,并与戎狄文化进行明显的区隔划分,诸如修建自己的宫室、房屋以及明确规定各阶层政府的制度。这些使得周族进一步地扩张了立国的规模,百姓们也安居乐业。不仅如此,周族虽然常年与戎狄杂处,但是其始终坚持不废农事,并且其部落领导人很擅长因地制宜,利用地理来取得生活资源并不断扩大发展,这也使得百姓们可以不断蓄积自身财富。

根据上文的介绍,我们已经可以推测商朝的文化就源于东夷的文化系统,所以在商文化中才有着浓厚的鬼神信仰氛围。上至天子、下到黎民百姓,其信仰的对象揽括大自然的各种层面,比如河神、山神或者日月星辰等等,与万物有灵论的萨满教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而位居各种鬼神之上、处于最高位置的角色就是上帝,这也是商超最崇拜的至高神,而且他们还认为商人的祖先去死后就与上帝相伴。
《礼记》中曾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整个商超礼仪的架构都是奠立在对鬼神的信仰崇敬之上,也表明了商超是个率领百姓来信奉鬼神、将神权与王权相结合,以此来解释世间所发生的各种现象的国度。
而且,商超王室十分相信自己是由上帝派来人间的,自己是根据上帝的旨意来统治万民的。上帝会一直不变地保护商王朝,而对与商王朝以外的国家或民族,则是持不仁慈和不庇佑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些民族或国家都不是“上帝选中的子民”,这也就给予了商人对于残杀“异族”的理由。

这种观念也被人定义为“血统天命观”,自商汤开始就成为商王室的信仰,这也是商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特征。这种被上帝眷顾的强烈自信也给商王朝埋下了灭亡的种子,自第二十四任商王祖甲之后,历任商王都只耽溺于享乐,而不再顾及百姓维持生计的艰难困苦。他们认为上帝始终会保佑商朝江山百姓平平安安,所以他们才毫不在意百姓的苦痛,甚至觉得那些过得太过贫苦百姓就是未被上帝选中的子民,这是他们自己该承担的宿命。
据相关文献记载,周文王打败黎国使,曾有商臣祖伊快马奔告于商纣王,他认为上帝想要终止商朝的天命,以前会告诉吉凶祸福的灵龟都不作法了。其实百姓并不希望商王死亡,而商纣王却始终坚持自己拥有天命,大言“我生不由命在天”,他并不相信周文王能奈何得了商朝。
“我生不有命在天”这句话就明确地反映了商纣王“血统天命观”的思维,然而在商臣祖伊看来,商朝的灭亡其实就是纣王整日淫戏、不务正业的结果。上帝放弃了长期蒙天眷顾的商超,只是因为朝廷不被人民信赖,所以人事奋勉才是王朝兴衰的关键因素。其实这种理性启蒙思潮不仅流传在周国内,而已经是商末时期社会普遍的认识。

虽然周朝也认为自己能够灭掉商朝是老天对新朝的“授命”,但不同的是周朝认为天命不会恒常永在,需要朝廷始终保持德性,统治者要始终坚持体察民意,否则就会重蹈商朝覆灭的后果。以此,我们可以看出周在承袭商文化影响的同时,懂得剔除糟粕。这时人的意识层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这种思潮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德性天命观酝酿的源头。
在人情时事后,周公旦亲自亲自带领部队出征。一路上每平定一个区域后,就让所随行的周人带着商朝遗民一同实施农耕,以此来彻底改变商人游牧漂泊的性格。整个战争和拓垦工程极为辛苦,周公耗费近三年的时间才完全稳住国内局面。
之后,他杀掉武庚、管叔,又将蔡叔流放,东建新都雒邑。不仅如此,周公还启用商朝王室后裔的微子启和卫康叔,由他们带领剩下的殷遗民分别建立宋国和卫国,以此来保存对商朝祖先的祭祀。这种不将遗民变奴隶 的生动地反映出周公对商周所拥有的祖先信仰的尊重。在周公看来,他不想建立一个只征服了人的国家,而是要建立一个征服人心的王朝。
由周公率先发展出的天命呈现出跟过去完全不同型态,因为周公生于忧患,所以他开始产生和思考“天命靡常”的道理。周人相信只有统治者始终怀有德性,广施善政普惠百姓,王朝才能才能长久地承蒙天命的眷顾。终于在经历过数百年的激烈斗争之后,“德性天命观”成功取替了“血统天命观”,继续指引中华文化迈向崭新的里程碑。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华文化的理性源头可以说就是来自西周,因周公旦建立新都后获得的人文精神。人们都说孔子之于中华文化的重要性至高无上,但周公与之相比,其政治位置与所开启的文化意义都要更加具有意义深刻的影响。
从商朝最看中的上帝,转为周朝看重的上天,同样是宇宙终极的存有,但是人们赋予其的含义却大不相同。虽然上天相比上帝,其意思变得更加模糊,但是其所代表的范围却更愈加宽泛,正所谓“天道远人道迩”,所以天道难测,朝廷要努力把握住人道以此来体察天道。由此看来,周朝推翻商朝并不不仅是政权的一种更替,而是彰显着中华文化由“盲目的鬼神信仰” 迈往“理性的人文精神”。

以前,商王朝凡事都要占卜问卦、告问上帝从而做出决策,他们坚信上帝只会保护商朝人,但其结果却是国亡朝灭。所以,周王室决定要更加真实地认知上天,他们感知出上天会保护天下所有的子民,尤其会善待于那些勤勉努力、乐善好施的人们。伴随着个人思想的蜕变,杀人殉葬的习俗也随之消失,这象征着中华文化成功地破除了以往的蒙昧,而去努力地拥抱理性的人文精神。
虽然人文精神产生在商朝探索天意无果后的挫折感之中,但是它并不是要人们从此对天产生怨怼,也不是无理地对眼前的困难加以指责,而是始终安处在自己的位置和情况中,努力、踏实地保持奋勉和动力,只有这样天命才会降临在你身上。
周公正是深刻领悟到这层道理,才得以制定出“制礼作乐”的大人文工程,让百姓透过知礼习乐的方式来通习天意,这个作法也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长久地影响着中华人民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周公把勤勉的对象从上天转至人民,自己也始终怀有诚意来面对政事、招徕贤客,共同架构出具有理想文化视野的盛世!
结尾

现在的社会不断地受到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的侵蚀和牵引,人们逐渐成为具有产能的螺丝钉。在这背后,不仅人文精神在逐渐沉沦,人的生命价值也在持续低落。人文精神的恢复急不可待,我们应该认真回顾周公是怎样将百姓从商朝时期信仰鬼神,转型到周朝的人文精神。在缅怀先人创业艰辛的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对比当前人类文明的斗争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在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背后所蕴藏的理想与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春秋左传》
《诗经》
《东夷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