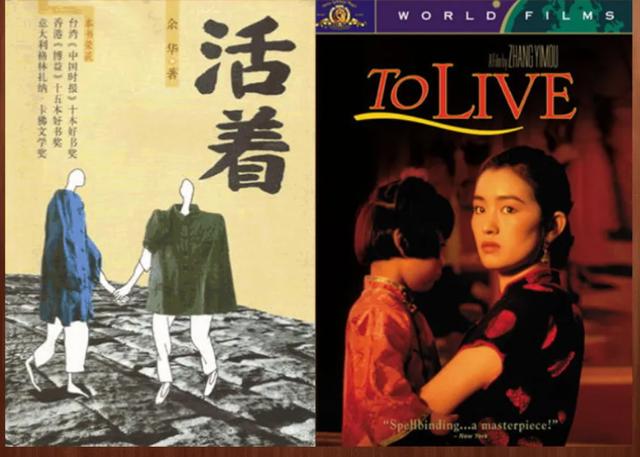前段时间,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对“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神学”这一观点提出了批判,否定了“科学没有哲学和神学高明”的说法,在朋友范围内引发了一次小小的辩论,我感觉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再做一些深入的探讨。
首先,我仍然坚持认为:“神学和哲学是有尽头的,但科学没有尽头。”
神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就走到了尽头,有哪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敢于否定基督耶稣?有哪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敢于否定真主安拉?又有哪一个虔诚的僧侣敢于否定释迦牟尼?甚至,如果把儒教泛化为神学,也没有一个中国的读书人敢于否定孔子。神学,诞生即完美,创始者的话语就是“圣经”,随后的任何神学研究,只能算是对“圣经”的解释。
而曾当过神学“仆女”的哲学,自从康德完成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部著作之后,就进入了“黄昏末法”时代。当代再无拿得出手的哲学大家,也没出现什么能引发普世共鸣的哲学理论。可以这么说,如今能流行的哲学只不过是一种伦理学,一种关于“道德”的学问,一种关于“价值观”的学问,完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西方最早的一批科学家大都是传教士出身,可以说科学其实也是神学的“女儿”,只不过这个“女儿”格外叛逆,彻底颠覆了神学的血脉,独自开创了一片天空。相信每一个人都不会否认,人类能走进如今繁华昌盛的时代,离不开牛顿、爱因斯坦和薛定谔这样的科学巨匠;而人类的未来命运,也许就掌握在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技术狂人手里。
其次,之所以“神学和哲学是有尽头的,但科学没有尽头。”是因为哲学和神学的本质逻辑是演绎法,而科学的本质逻辑是归纳法。
所有的哲学都存在着自己逻辑上的“大前提”,被其创立者称之为“第一性原理”,其整个哲学体系是基于这个“第一性原理”演绎推理出来的。被称为西方“哲学之父”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以“水是万物之源”为第一性原理,创立了伊奥尼亚学派;被誉为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勒内·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为第一性原理,搞出了一个骑墙派的“身心二元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受推崇的保罗·萨特,以“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为第一性原理,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人道的存在主义。
如果你不否定他们提出的第一性原理,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哲学很有说服力,而且由于演绎法的特性,他们的逻辑是严密而完备的。可问题就在于,任何一种哲学的所谓“第一性原理”,都不是绝对真理。如果逻辑的大前提都是不正确的,逻辑推理过程再正确又有什么用呢?
泰勒斯和萨特的第一性原理存在显而易见的谬误,我们就不深入讨论了。不妨就单说说这个大家都觉得无可辩驳的“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认为,世界既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的,而是有“心”和“物”二元共同组成的。也就是说,人的心灵和肉体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存在。既然如此,“我思”中的我和“我在”中的我,就不是同一个我,而是两个独立的我。“我思”中的我说的是心灵的我,而“我在”中的我说的是肉体的我,“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其实就犯了偷换逻辑的错误。而要使得“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在逻辑上正确,就必须使得这句话中的两个“我”统一起来,要么统一在“唯物”上,要么统一在“唯心”上,而这又恰恰驳倒了笛卡尔自己提出的“身心二元论”。
至于神学的第一性原理,当然就是“存在一个或多个无所不能的神”。而它们包含的逻辑悖论其实也非常显而易见,无所不能的神能够创造一个连它都不能改变的事物吗?无论它或它们能不能创造这样的事物,都证明神并不是无所不能的。
与哲学和神学不同,科学是不存在第一性原理的,真正的科学家从不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科学的方法是,先通过观察客观存在的现象,找出其中的规律性,然后提出科学假说,并通过可以被重复的科学实验来检验科学假说,使之升格为科学理论。无论是科学假说还是科学理论,都是对个体的归纳,因而在逻辑上是不完备的,是可以被证伪的知识。但也正因为如此,科学始终具备着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不断推陈出新,永无止境。
第一性原理不是绝对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真理不存在。因为如果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这句话本身就会成为绝对真理。只不过,也许是因为绝对真理包含了太过繁复的信息,以致于当前人类的大脑还不能容纳下它。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发现了绝对真理,那必然也是通过那条没有尽头的科学的道路,而不是通过已经走到了尽头的哲学或神学的道理。
最后,作为一个喜欢读哲学书的理工男,尽管我习惯用科学的方法思考和解决问题,但我从来都没有完全否定哲学的想法。在我看来,科学尝试回答的是“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而哲学尝试回答的则是“我是谁”的问题。对于世界的未来而言,科学更为重要;但对于我们自己的人生而言,哲学可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