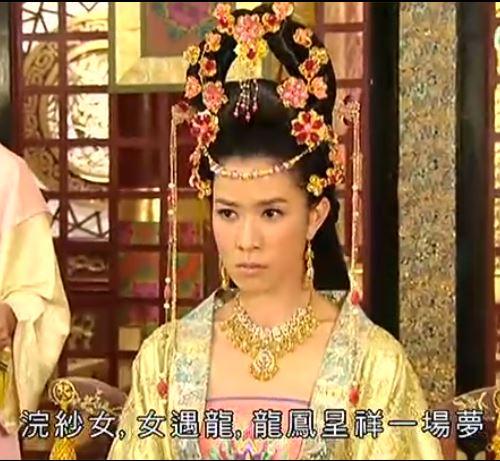文/行在阳秋
建文改制并未失败,只是被朱棣的军事胜利和暴政暂时终结。明朝中后期的制度转型,正是朝建文帝规划的道路上回转,因此带来了社会文化经济的大发展。朱棣把这个大发展推迟了上百年,可以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带来深重的灾难。

建文改制失败了吗?
1
建文改制是失败还是成功?它给明代以至后世留下了什么?
当然,就政治史而言,建文改制已经随着建文朝廷的覆灭而灰飞烟灭,于事实上确已失败。不过,建文朝的覆灭极其偶然,它亡于军事,并非亡于政治。以建文朝失败而推出建文改制失败的结论,无疑属于事后归因谬误(post hoc,ergo propter hoc fallacy);此外,以建文改制作为建文朝失败的原因,无疑又是过度简化因果谬误(causal oversimplification fallacy)。
对建文改制持负面态度的论者,多半坚持这两种论调。

建文改制并未失败
陈建、高岱、何乔远便认为建文改制失败了,朱鹭也认为建文改制是悖逆太祖祖训。《明史》也认为,“时井田虽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度,无济实事,为燕王藉口。论者服叔英之识,而惜孝孺不能用其言也。”晁中辰等现代论者,也认建文改制为不切实际,间接导致建文朝的失败。
建文朝确实亡于军事,不过军事上的失败亦极其偶然。实际上,朱棣军队在建文四年,仍然遭遇了小河之战的重挫,朱棣本人甚至对前景都并非乐观,赖朱能劝阻方坚定南下决心:
进战小河,为敌所乘,稍却,诸将遽请班师。独王(朱能)力劝上行,曰:“用兵未必常胜,岂可因小挫系自沮?项羽百战百胜,竟亡,汉高屡败而终兴,自殿下举兵以来,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置意,但当以宗社为重,整兵前进耳。”上抚掌叹曰:“尔言深合吾心。”遂行。
南京的陷落由一连串偶然因素导致(陈瑄、童俊的水师叛降,李景隆、谷王打开金川门)。政治上,建文朝并未失败。顾起元《客座赘语》载:
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纪法修明之后,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几等于三代。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礼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於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顾氏的说法容或有夸大之处,但这段文字能够证明:建文四年内外施政颇得人心,且成效斐然,“四载宽政解严霜”。
军事上的失败不能抹煞政治上的成功。如果以军事上的失败而否定建文改制,显然不能成立。问题逼到这一步,第一个谬误,不证自明。
笔者认为,以建文改制作为建文朝失败的原因也不成立,并且犯了过度简化因果谬误,这则需要多费笔墨证明。攻击建文改制者多以建文改制为不切实际、书生误国,然持此论调者,亦不免多发空论,说服力有限。
改制的效果如何,前引《客座赘语》足以说明。第二个论调若以“建文改制在政治上失败,建文朝亡于政治”作证据,已经不成立。那么,“建文改制影响了军事,而招致建文朝覆亡”,这个证据需要认真对待。
有一点是站得住脚的:建文改制重文轻武,卒使武臣寒心,扬州、镇江镇守将领叛变,多投效燕王,与之相关。在逻辑和事实上,它都成立。因此,以建文改制作为建文朝军事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可以的。
但如前所述,这属过度简化因果谬误(causal oversimplification fallacy)。事实上,改制对军事上的影响有限。军事上的失败,多半还属于作战策略之误:
撤徐辉祖还京,犯兵家有进无退之大忌;主要兵力驻守淮安、凤阳而被朱棣绕开,徒费兵饷;使李景隆、谷王守城,则根本是用人不当。决策接连失误,造成了南京陷落的小概率事件。
准此,第二种论调也不能成立。
建文改制本身成功;建文改制间接导致军事失败,不过对其影响堪称微弱;建文改制因军事失败而间接失败。——这就是笔者的结论。
如前所述,建文改制虽然本身的运行尚称良好,但仍因军事上的失败,而连带失败了。
除了朱棣保留的部分制度,建文改制还给明代制度留下了什么遗产?
郑晓曾总结道:
靖难后,复洪武旧制,惟存大理寺,不设断事官及断事司。正统(明英宗年号)中复京卫武学。
郑氏其时不能读到《明太宗实录》,故而对朱棣保留的制度,只看到大理寺的存续。而后世又向建文回转的制度,确有正统中京卫武学的设立。不过,笔者以为,就明朝制度而言,对建文制度的回转,还不止于此。
建文制度正是明朝的发展方向
2
笔者以为,就制度条文而言,建文改制确实已随着建文朝的覆亡而消亡,不再留存。明人在公开场合对建文改制几乎不提,明代官方政书正德《会典》、万历《会典》,都不载建文制度。建文朝特有的机构名、官名,甚至终清末,再未出现,也不再引人注意。近年来编纂的大型辞书,也见不到这些新设的官名。
笔者遍检《历代职官表》、《中国官制大辞典》、《中国历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均没有哪怕一个字涉及到“文学博士”、“资政上卿”、“通政寺”等建文新制。
制度条文上,建文改制成果迅速瓦解,并未给明代留下遗产。准此,笔者尝试用“抽象回转”,来形容建文改制对明代制度的影响。必须首先郑重声明的是,在本项研究中,这个论断实证性有所缺乏,只是笔者的一点推测,证明它的工作,还需要继续努力才可告成。
相较于明前期,明中后期发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变革,简直如同两个朝代。这体现在:
内阁制逐渐有真宰相之势,政治制度已经深刻转变;白银货币化,商品经济发展;海上贸易兴盛,工商业勃兴;人身依附减弱,赋役制度变革;科学技术进步,西学东渐开始;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开放,异彩纷呈,斗奇炫博的时代来临,完全扫除了明初的“古拙”之风。
“晚明”既区别于明前期,也与清前期有着显著的区别。“明中后期”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单元。
若将明代中后期巨变与建文改制合观,我们无妨说,“明中后期”对洪武永乐鲜明的反动,恰恰属于向建文改制的“抽象回转”。
法定制度,也即制度条文上,建文改制的成果固无存世者。不过,制度外缘第一圈——制度运行状况、制度外缘第二圈——经济、文化社会状况,这制度的另外两圈均已几乎完全从洪武、永乐制度中“抽离”。洪武祖制、永乐“复旧制”均已名存实亡,起码是面目全非。
《南都繁会图》
明朝中后期的的大变局与建文制度相合
准此,明中后期之巨变,恰可与建文改制相合:
建文帝提高六部品秩,令翰林官得参国事,在事实上已经向丞相制回转。建文朝于中央决策机构之重组,虽然没有形成永乐时固定的内阁制,但确然已经造成大臣柄政的事实,齐黄二人的权力决不下于丞相,对比明中后期,确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其一;
“苏州的豪族自明初开始受到了严厉的镇压。……明初的苏州如此劫难不断,不仅在经济上,文化上亦受到弹压。”建文朝苏州的短暂复兴,为朱棣夺位所中止。不过,明中后期江南社会经济大进,江南势力勃兴,苏州成为明代典型城市,这均于建文朝可寻到先声:建文改制,取消苏松重赋,令苏松人仍得官户部,政权之本位落在江南。甚至在宣德、正统年间,况钟、周忱居官苏州,即已用平米、济农、兑运、折征等经济政策,曲折实现了向建文改制精神之回转,此其二;
明中后期,宗藩制度名存实亡,濒临崩溃,朝廷不断推出新政策(如嘉靖朝修订《宗藩条例》、万历时始准宗藩应试入仕)建文削藩,早着先鞭,此其三;
依据现有的史料,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明中后期之巨变,差可视为向建文制度之回转。易言之,因靖难战事之失败,建文改制之愿景推迟了一个多世纪,方缓慢显现。
《儒林外史》有言:
邹吉甫又道:“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
这反映民间长期流传对建文朝的观感,以及于朱棣的贬斥。
永乐“继统”,使建文改制这一历史趋势遭遇了一大回旋,延缓了建文改制之大趋势。有明一代,建文改制之势虽遭逆转,却仍缓慢回归。其势之至,则需要一百多年的潜滋暗长。
建文改制,实际制度条文虽然鲜有留存,但制度外缘的实际运行状况,再外缘的经济、社会、思想状况,这些建文改制的施政目标和制度规划目标,均于明中后期产生。质言之,建文改制在明中后期完成了“抽象回转”。
朱棣终结了华夏文明自我刷新的希望
3
人亡政息。短短四年的建文改制,与建文朝廷一起淹没于靖难的硝烟中。如何评价这场改制运动?
笔者尝试用“思想史上的三大特色、制度史上的三大概念”作结,庶几可作为本项研究的结语,对建文改制的论断。
建文改制,可称者多矣。首先,就思想史而言,建文改制有三大特色,这三大特色均非常突出:
建文改制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儒家理想主义改革运动,自此之后,再无出现。建文改制,堪称绝响,此其一;
吾国历史上,道统、政统之最末一次合榫。质言之,如若“道统”、“政统”的解释效力仍然成立,那么在建文改制中我们看到,政统并非操纵、亦非利用道统,道统亦非俯就、屈从、谄事于政统。“君臣际遇”之合作,自此再无出现。儒学士大夫再无机会取得君权的奥援,开展理想主义色彩剧烈的政治改革,以期实现他们心中不绝如缕之“回向三代”政治理想,重建合理的人间秩序,此其二;
史上历次《周礼》改革运动中,建文改制与新莽改制、北周革典、熙宁变法相比,具有绝无仅有的自身特质:与新莽改制之华丽铺张、不切实际相比,建文改制呈现出合理化之实用色彩;与北周革典之粉饰虚张、“阳傅阴适”相较,建文改制又展现出笃实切当之特质;与熙宁变法之务求财用、富国强兵对勘,建文改制又具备了“义利双行”、藏富于民之衡平特点。此其三。
朱棣才是损害文明前途的暴君
笔者尝试从制度史角度,提出三大概念以论建文改制:断裂,连续,回转。笔者看来,建文改制实已涵盖了这三大概念,而又不仅限于其中的每一个。当然,这三个名词所指代的内涵和本身的语境并不完全相同,将它们并列到一起,只是出于排比概括的需要。
断裂。就明史而言,如果我们接受“明前期”、“明中后期”的历史分期法,认同这两个时期的巨大断裂,那么,若将建文朝四年置于“明前期”之内的话,建文朝无疑是洪武以至正德、嘉靖百余年“古朴”历史中的一段短暂插曲。这四年时间里,士大夫阶层进入权力核心、经济社会政策宽放,均与“明前期”的其余任何时段显著相异。可称“断裂”。
连续。仍从明朝一朝内部,如果纵向观察,如前所述,建文朝实际上接续了洪武末期的种种演化趋势。洪武一朝,朱元璋不断创设、更迭制度,既否定前人,也在否定自己,有自我作古、上承三代之意。他晚年的诸多做法,已是为嗣君留下有利的政治环境,以实现安民求治之愿望。建文朝改制,毋宁说是对朱元璋晚年政治的连续和完成。
回转。方孝孺曾说:
至于近世,惟宋之俗为近古。尊尚儒术,以礼义渐渍其民。三百年之间,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内庶官顾养廉耻。
若将建文朝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纵向考察的话,它无疑是一次回转——向宋代文人政治、以及秦汉以前“三代”的回转。
特别是后者。以“回向三代”为己任的政治理想,自秦汉以来始终荡漾于历代儒生心中。建文改制,遂成为近世之前,儒家理想主义的最终一次机会,最后一次努力,最末一次实践。
燕王篡位,方氏喋血。这个夙愿终告彻底落空,在帝制时代它便永告失败了。
欢迎关注文史宴
专业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专业
熟悉历史陌生化,陌生历史普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