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唐朝名将,人们首先会想起的是李靖、李世勣、薛仁贵、郭子仪、李光弼这几位。
但是,唐玄宗朝有一位名将,文武双全、智勇兼备,帅才将略绝不上以上几位之下。
之所以名气不扬,主要是生长于承平之年,而其本人又忠厚低调,悲天悯人,心怀苍生,不忍建功而轻动兵刀而已。
他,就是曾手掌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大印的中唐名将王忠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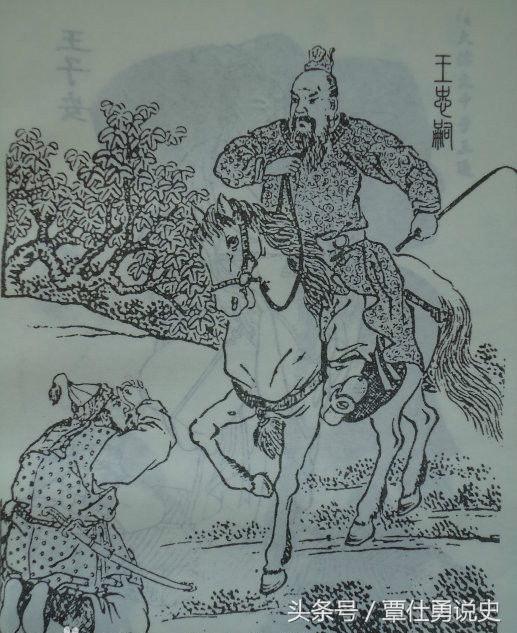
古今名将,似乎都是为战争而生的,在战争中体现自身价值,在战争中燃烧自我,在战争中升华生命的意义。
但王忠嗣似乎是个例外。
王忠嗣的人生目的,不是为战争而生,而是为消灭战争而生,为和平而生。
这样的将军,应该冠之以“伟大”二字。
李光弼、哥舒翰等人都是王忠嗣一手提拔起来的名将。
某次,李光弼试探性地问王忠嗣,公何不学习卫青、霍去病出塞开边,建不世之功业?
王忠嗣淡然一笑,说:“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
说到这,有人以为,王忠嗣非不屑为,乃不能为也。
其实不然。
我们来简单看看王忠嗣的作战能力吧。
先说个人武力。
说起个人武力,大家赞誉最多的是汉末三国的将领,似乎遍地都是个人武力奇高的猛将,除了赫赫有名的飞将吕布之外,还有蜀汉五大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曹魏大将夏侯惇、夏侯渊、许褚、典韦、张郃;东吴孙策、太史慈、甘宁、周泰等等。如果拿王忠嗣跟这些人比,王忠嗣大概会列在哪个位置呢?
撇开小说演义史不提,单以正史中记载这些人在单场打斗中亲手毙敌人数论,姜维算比较牛的。
姜维单人杀人纪录最高的一次,是假降钟会后,煽动钟会谋反,事泄,与敌拼死一斗,《三国志.钟会传》记载:“姜维率会左右战,手杀五六人,众既格斩维,争赴杀会。”
姜维仗剑迎敌,亲手杀了五六个人,可谓厉害。
这方面,典韦堪可比肩姜维。
宛城之战,典韦为保曹操脱险,力战而死。《三国志 典韦传》记载:“韦双挟两贼击杀之,馀贼不敢前。韦复前突贼,杀数人,创重发,瞋目大骂而死。”
典韦在危难之中,杀了数人,也同样厉害。
但姜、典二人与东吴大将凌统比起来,又逊色了不少。
合肥之战,凌统为了保护孙权,力战杀敌,《三国志 凌统传》记载:“统复还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
凌统的手下全部战死,他自己身上挂彩,却杀了数十人,让人惊骇。
曹魏五子良将之一的张辽也是个极狠角色,在其代表战——威震逍遥津之战中,《三国志.张辽传》记载:“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同样有手杀了数十人的纪录。
但凌统和张辽还是没完成传说中的“百人斩”。
统观整部《三国志》,能完成“百人斩”的人是吴将丁奉。
魏国大将文钦投吴国,孙峻和丁奉负责接洽,眼看敌军咬尾紧追,《三国志.丁奉传》记载:“奉跨马持矛,突入其陈中,斩首数百,获其军器。”
丁奉单人闯阵,斩杀数百人!
当然,最有名的,还是常山赵子龙在长板坡救主的一战。但该战,《三国志》并未记其杀敌数,所以没法比较。
说回到王忠嗣这边,《新唐书》记,王忠嗣跟随河西节度使杜希望讨伐吐蕃,“吐蕃大出,欲取当新城,晨压官军阵,众不敌,举军皆恐。忠嗣单马进,左右驰突,独杀数百人,贼众嚣相蹂,军翼掩之,虏大败。”
看,王忠嗣“独杀数百人”,纪录与丁奉相当。
也就是说,如若王忠嗣生在三国,绝对可以跻身一流武将行列。
不过,个人之勇不足为惧,万人之勇方可震天下。这里说的万人之勇,是指用兵打仗的军事才能。
在王忠嗣很小的时候,唐玄宗就把他当作霍去病一样的人物来看待。
王忠嗣的父亲王海宾为丰安军使,战死于武阶之战。
那一年,王忠嗣才九岁,作为烈士孤儿,被唐玄宗召见。
王忠嗣入到宫中,见了唐玄宗,伏地号泣。
唐玄宗心生恻然,抚摸着他的小脑袋,爱怜万分地说:“此去病孤也,须壮而将之。”收之为义子,接到宫中抚养。
王忠嗣在宫中与忠王李亨关系非常好,年龄稍长,雄毅寡言,有武略。
某次,唐玄宗和王忠嗣谈论兵法,王忠嗣应对纵横,皆出意表。

开元十八年,王忠嗣出任兵马使,随河西节度使萧嵩出征,在玉川战役中以三百轻骑偷袭吐蕃,斩首上千级,俘虏四千余人,缴获牛羊上万头,吐蕃赞普仓皇逃命。
此战,堪与霍去病800骑兵夜袭匈奴之战媲美,王忠嗣也一战成名,随后接替王晊担任陇右节度使。
初唐边患除了吐蕃为祸最烈之外,契丹也给唐廷造成不小的麻烦。
唐朝曾经五次北伐契丹,但五次均以失败告终。
武则天时代,这位铁腕女皇还曾下令征全国囚犯组成军队讨伐契丹,但同样劳而无功。
到了开元年间,契丹已成唐之大患。
开元二十六年,王忠嗣率十万骑兵北伐契丹,出雁门关,于桑干河三战三捷,将奚和契丹的二十万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奚、契三十六部全部向唐军投降,之后几十年不敢作乱。
王忠嗣威名大震于天下。
天宝初年,突厥余众共立判阙特勒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唐玄宗遣使谕令乌苏内附,乌苏不从。
王忠嗣奉旨出征,一路势如破竹,直抵萨河内山,雷霆猛击,攻破突厥东部军事力量,取乌苏米施可汗首级至长安。
至此,曾经称雄北方一百余年的突厥汗国黯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天宝五年(746年),唐玄宗命王忠嗣兼任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节度使。
一人佩四镇之印,拥兵近三十余万人,掌控万里边疆,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也在这一年,王忠嗣发动了对吐蕃的青海湖会战,大破吐蕃北线主力,并乘胜追击,在积石会战中全歼吐蕃残部,斩两吐蕃王子,俘虏了八千名依附吐蕃的吐谷浑军,迫使吐谷浑降唐。
自此,吐蕃在青海地带对唐朝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其对河西地带的威胁已基本解除。王忠嗣又千里奔驰,击败吐蕃、大食联军,吓得大食从此宵遁,不敢再来招惹唐军。
这一时期,大唐威震八方,四海畏服。
不过,诚如前文所述,王忠嗣憎恶“一将成名万骨枯”的武将成名之路,毕生主张“以持重安边为务”。
《新唐书》载,王忠嗣本人随身常带着一张重150斤的漆弓,但从不轻易使用。
王忠嗣的军事思想是“以武止戈”,他的军事武力,更多体现在一种强大的精神震慑之上。这种思想,与唐玄宗的想法是大相径庭。

唐玄宗在执政后期,妄自尊大,穷奢极欲,和喜欢穷兵黩武的汉武帝有得一拼,不断对周边地区动用武力,一心想征服世界。为此,张说、张九龄等名相相继被贬,中央已经没有什么人敢去稍加遏制唐玄宗那颗自我膨胀的勃勃野心了。
唐玄宗对王忠嗣以静待动、不喜欢折腾的作派产生了不满。
古语说:“自古忠贤,工谋于国则拙于身。”
王忠嗣就是这样一个“谋于国”却“拙于身”的人,他丝毫没有觉察到皇帝对自己的不满,自己身为四镇节度使,却参了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一本,指称“安禄山必反”。

安禄山在朝内有一个好朋友——臭名昭著的“口蜜腹剑”人物、宰相李林甫!
李林甫与安禄山臭味相投,互有所求。
李林甫看王忠嗣参劾自己哥们,就反咬王忠嗣一口,说王忠嗣是四镇节度使,造反的可能性比安禄山大。
李林甫诋毁王忠嗣,除了替哥们抱不平外,还有一个原因。即依唐制,地方节度使如果功勋卓著,很可能会入朝为宰相。李林甫可不想看到王忠嗣入长安为宰相。
王忠嗣为证自清,请求辞去二镇的节度使职位。
唐玄宗含笑批准,并给王忠嗣下了一道命令:攻击吐蕃的石堡城。
石堡城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城池,其以悬崖为城,有金汤之固,不付上上万人生命的代价休想攻得下来。
王忠嗣一口否定,告诫朝廷说,吐蕃倾全国之力守卫石堡城,而石堡城形势又是如此险固,非死亡数万士卒不能拔取,不如等待有利时机,再行攻取。
唐玄宗没对王忠嗣说什么,而把任务交给了另一位将军董延光,让董延光去攻石堡城。
唐玄宗此举是在对王忠嗣进行变相的警告。
河西兵马使李光弼希望王忠嗣能作些变通,但王忠嗣却坦然说道:“我之所以不用几万人的生命去换取一座石堡城,是因为取得了也不能控制对方,而这城在吐蕃手里对我们也不会产生什么威胁,所以我才不肯出兵。我岂能忍心以几万人的性命换取一个官职!”
王忠嗣的话让人感动。但他也很快因为自己的话遭受到了惩罚。
董延光在进攻中遭遇了惨败,为了推卸责任,他说是王忠嗣“阻挠”他的军事计划。
李林甫在这个时候又跳了出来,诬蔑王忠嗣要谋反。
唐玄宗二话不说,将王忠嗣革职,令人将其带回长安,交由三司(刑部、御使台、大理寺)审问。
审问的结果是,王忠嗣被判死刑。
时继任垄右节度使的哥舒翰感念王忠嗣知遇之恩,入朝死保王忠嗣不反。
最终,王忠嗣死罪免去,被贬为太守。
两年后,王忠嗣在任上暴病而死,年仅43岁。
同年,歌舒翰领命攻打石堡城,战死数万人才攻克,仅俘获吐蕃兵400人,与王忠嗣的预料完全一致。
王忠嗣死后六年,安史之乱爆发,盛唐终结,唐朝从此走下坡路,直至灭亡。

有史家认为,安史之乱与一代名将王忠嗣的被贬和早亡有着深刻的联系。
天宝初年,唐帝国军镇兵力布局大致是这样:
安西、北庭两镇共有兵力44000人,相当于唐朝的左臂,舒展到中亚,宣示着盛唐的地位和强大。
范阳、平卢两镇共有兵力128900人,相当于唐朝的右臂,拒挡着来自东北方向契丹、溪的侵扰。
河西、朔方、河东、陇右四镇共有兵力269700人,相当于唐朝的腹心,一方面要消除来自吐蕃、突厥、回鹘等的威胁,另一方面拱卫长安、关中地区的安全。
王忠嗣原担任四镇节度使,手下有歌舒翰、李光弼等劲将锐兵,大唐可谓固若金汤。
王忠嗣被贬,平衡被打破,安禄山就有了北边坐大之势。
而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郭子仪、李光弼等人年龄接近,地位相仿,出身相似,互不服对方,即朝廷缺少了王忠嗣这样能统帅各镇兵将的帅才,极容易陷入各自为战的局面,仗就打成了烂仗。
设想一下,如果王忠嗣不早死,由其全面主持战事,安史之乱很可能只是大海上跳跃的几朵小浪花,瞬间既逝。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盛唐的局面就此一去不返,西域也因此丢失一千多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