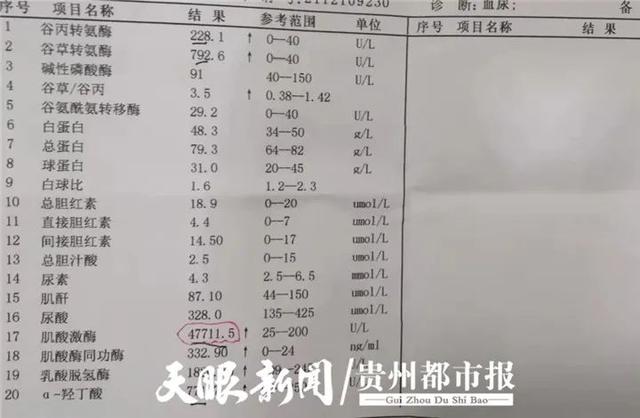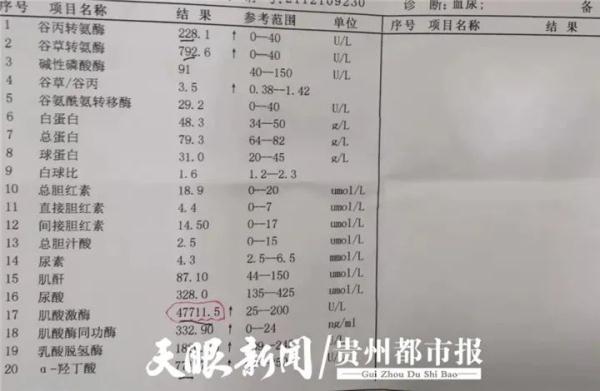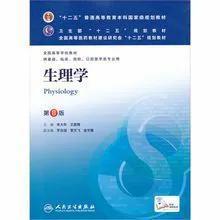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科技哲学专业《大学》《中庸》读书会侧记
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流传至今的经典文献不计其数。其中,《大学》和《中庸》作为《礼记》中的两篇文章,自从宋朝大儒朱熹将其提取出来并与《论语》《孟子》共同列为《四书》之后,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其微言大义也被众多儒家学者们反复解读。近日,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科技哲学专业马来平教授和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科技哲学专业常春兰副教授带领本专业的的研究生们举办了《大学》《中庸》读书会。原山东教育报刊社总编及编审、《中国教育报》等报刊著名专栏作家、《心悟》作者陶继新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参与了读书会并发言;山东师范大学数学院杨泽忠教授带领他的数位研究生在线上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特点也十分鲜明,其对人类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在众多思想文化中独树一帜。因此,陶继新先生认为,我们对儒家经典的解读要联系自身的生命感悟。这种感悟即是要在对文本含义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之相互印证并深入思考。“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要想真正理解儒家思想的意义,还必须将之付诸实践,在行动中去切身领会先贤们的深思熟虑。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文章想要表达的深刻内涵,否则就只能在文本浅层徘徊不前。
硕士研究生许遇好认为,《大学》《中庸》的写作背景大致是春秋战国时期,此时传统的礼乐制度面临崩溃,人们的信仰体系也因社会的巨变而逐渐崩塌。因此,信仰根基动摇的人们面临着如何与天地万物、与他人共存的窘境。曾子、子思等一批儒者为了重新树立起一套儒家价值和信仰系统,深入思考了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及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儒家先哲的这些对世界的思考始终围绕着一些固有的宗旨,首当其冲就是对人的认知状态的观察与反省:首先是要“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样才能够获得充分的认识。其次,儒家所认识的世间万物最终都必然要指向其道德意义和实用价值,“格物致知”也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开篇即写出了认识的目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由天命到人类教化是儒家的一以贯之的路线,其终极目标即是人于天地之间如何自处,为人类的道德伦理树立一个坚实的根基。
硕士研究生董宇指出,朱熹在《大学章句》的序中认为,人们应该首先学习“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学有所成之后再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这即是说明儒家将道德性知识置于其他类型的知识之上。并且,朱熹也已经尝试将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加以区别,“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在认识的方法上,朱熹认为应该“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最终应该要达到“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这种细致的划分是朱子的一大重要贡献。
儒学高等研究院常春兰副教授指出,大学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位于最始端,是其他条目的基础。但对其中“物”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却存在误解,郑玄、朱熹都说“物,犹事也。”根据这一注释就有了当代一种流行观点:《大学》所谓“物”,不是泛指草木鸟兽之类,而是专指人伦政治实践活动。这实际上是由于误解了古代汉语中“物”“事”的含义进而误读了郑玄、朱熹的解释。《说文解字》中说“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事:职也。从史。”根据许慎的解释,“事”“物”可以明确区分。在先秦两汉文献中,“事”字、“物”字单独出现的次数都非常多,而“物事”、“事物”的说法也偶有出现。两汉之后的文献中,“物事”、“事物”的说法大大增多。那么“物,犹事也”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从中国古代的整体性思维来看,“事”“物”关系密切,事是关于物的事,物是事中之物,因此有“物事”、“事物”的说法,而且单独使用“事”“物”时,其意思可能也涵盖了现代意义上的“事”和“物”,所以,“物,犹事也”,意思应该是说“物”既指物又指事。朱熹并非不关注自然界,而是对天体运行这一重要自然现象尤其感兴趣,其著作中有不少天文学方面的讨论。
最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马来平教授给出了自己关于《大学》《中庸》的看法。马教授首先从《大学》的文本之争与“格物致知”论的分歧开始讲起。自朱熹始,发生《大学》今本和古本之争。《今本大学》是朱熹根据二程和自己的理解,将传统《大学》中的部分内容重新整理并加以补充而得到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将“格物致知”部分进行了补足。王阳明则认为不应对《大学》的文本内容加以改动,其原始文本即《古本大学》并没有“错简”或者“阙文”。文本之争的背后,反映的是对《大学》主旨尤其是“格物致知”概念的不同阐释。朱熹认为,“格物致知”即对外物进行主动接触、仔细观察和深入思考,从而最终穷尽物理。而王阳明则认为,《大学》所教的根本在于重视自己内心的反省,而非对于外物的观察,“格物”的实质就是纠正人心的不正,以恢复本体的正,“致知”即是扩充自己的良知。这种基于经典文本不同理解的激烈争论,突出了经典文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乾嘉考据学的崛起。马教授认为,朱子的“格物致知”论突破了儒学惯常的单纯伦理视域,而触及到了主体认识客体的认识论、触及到了科学,从而实现了儒学认识外物维度的确立。这种变化既是朱熹从“格物致知”出发构建儒学理论体系的需要,也是儒学和科学内在亲和性的自然发展。
马教授还提出,《中庸》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科学家的培养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庸》中所提出的以“诚”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能够引导科学家在从事科研活动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实事求是,从价值观层面上防止造假抄袭行为的产生,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有效的伦理基础,也有助于营造一种讲信修睦、同心协力的科研环境。另外,《中庸》中所提出的“中和”思想和“执用两中”“执中权变”的方法论,对于科学思维的培养至关重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应当遵循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等一系列行为规范,这些都是科学家和整个科学界共同发展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品质。这些行为规范与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行为准则存在大量的共通内容,两者息息相关。
陶继新先生联系自己对于儒家学说的理解以及众人的发言,指出自己研究儒学更多是从做人做事的感悟方面去理解,而今天听闻大家从义理层面对《大学》《中庸》的部分内容重新解读后收获颇丰。《大学》《中庸》所反映的儒家思想毫无疑问是注重道德修养,但其道德基础却是来自于涵盖世间万物的天地。儒家讲求“天人合一”,这种境界下的天地万物都与人的道德产生联系。《论语》中,孔子也让弟子们“多识虫鱼鸟兽草木之名”,这是不无道理的。儒家先贤所说的事理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切实从万事万物中体悟出来的。
除了以上发言的师生外,我院科哲专业硕士研究生彭繁和孙佳丽同学也在此次读书会上做了讨论发言。与会者们认为,虽然先前已有部分学者认识到朱熹之“格物”是外物,但对这种观点的论述并不充分,也始终未能成为学界主流。通过此次对《大学》文本的重新阐释和深入剖析,不仅让“格物”中认知外物的部分得以突显,也使儒学中与科学契合的部分被重新发现,这是对当下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和补充。这次对《大学》和《中庸》的深入阅读与交流探讨,让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科技哲学专业的师生们加深了自己对于儒家经典的认识和传统思想的领会,为其以后的科研学术活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常春兰 许遇好)
壹点号文史研究院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