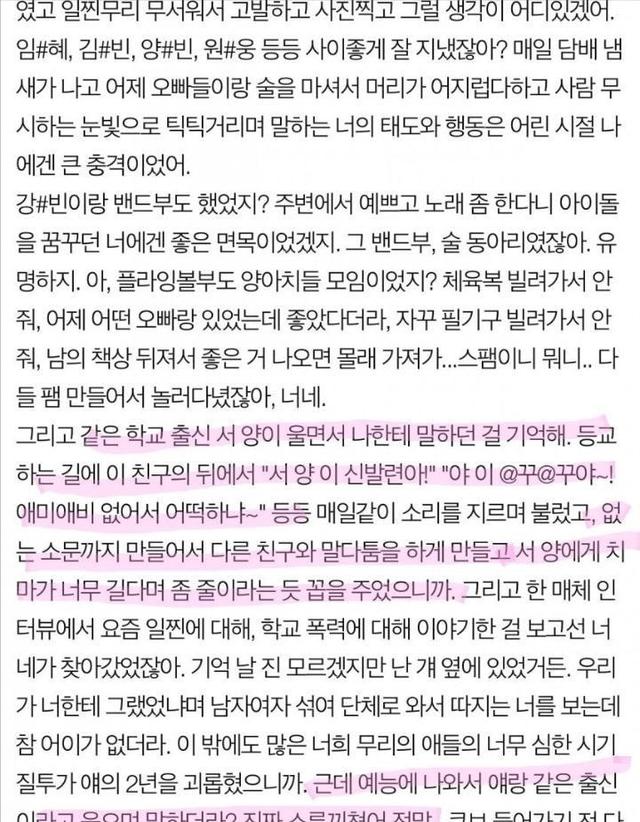戏剧舞台上,演员对每一人物的面部化装,照例是要依据人物的性格,感情,年龄、环境的不同有所区别。由于太感复杂,逐渐进入类型。面部化装有了类型,也使老观众易于识别,从此就有了脸谱的名称。
有人提出:“净角脸谱,原来都是面具,这种面具上,大都涂有彩色,后来因为面具是死的,无法表现神色和感情,进一步把彩色就涂在面部上,这是净角面部化装一个大改革”。我的看法,并不可靠,面具与脸谱是两回事。这种面具、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行头箱里,还有好多,如加官面具、财神面具,魁星面具、土地面具、鬼面具等等。脸谱在金元杂剧上,已经出现,如现存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元泰定元年画的,戏剧壁画,上题“尧都见爱,太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末角下巴上有京剧口面同样的胡须(也挂在两耳上)、净角用墨画眉,也用墨画在嘴两边。又在一九五九年一月,山西候马市郊,发掘大金邦卫绍王大安二年建的董姓墓域,出土五个戏剧陶俑,其中有一陶俑,用白粉画一个三角形于鼻梁上,用浓墨画眉,两颊两边也涂上墨,说明金元时代,已经采用粉墨脸谱,不过还很简陋而已。

李少春孙悟空脸谱
净角用彩色勾在脸上,我的看法,是开始在元末明初。在明太祖朱洪武的第十六个太子朱权所著的《太和正音谱》一书上,他把戏剧故事分作十二类,就是一、神仙道化,二、林泉邱壑,三、披袍秉笏,四、忠臣烈士,五、孝义廉节,六、叱奸骂谗,七、逐臣孤子,八、拔刀赶棒,九、风花雪月,十、悲欢离合,十一、烟花粉黛,十二、神头鬼面,可见元朝末年已经有神灵鬼怪杂剧的演出。用金色、银色、红色、绿色、蓝色、黄色等等勾在脸上,可能是从这些神怪戏上开始的。
也有人提出:“净角所扮人物脸上,有彩色画出图案意味的各种脸谱,无非是为了构成与服装色彩相互协调的艺术体系。”我的看法,值得商榷,我晓得服装色泽,以黄为尊,帝与后才能穿黄服。红为权势,诸侯首相才能穿红袍。绿袍是文官武职的大员朝服,如《二进宫》兵部侍郎杨伯约,《白虎堂》八贤王赵德芳。白袍深明大义人物所穿,如《探皇陵》徐延昭,《白虎堂》杨延昭,《连营寨》刘玄德。黑袍是正直武将穿,如项羽、张飞。蓝袍勇猛战士穿,如窦尔墩、单雄信。脸谱颜色,黄代表邪异。红代表忠义,绿代表凶猛的绿林好汉。白代表奸佞,作为面无血色,善动心计人物。黑代表鲁莽勇敢。蓝代表凶恶,常勾在鬼怪脸上。金色代表神灵。紫色代表老诚忠义。二者内容并未统一,其中黄与白两色,与服装色泽的代表性,成了对立。再说有不少戏上,并无净角,如《黄鹤楼》上,刘备、赵云、周瑜、鲁肃,都是俊扮,无一用彩色脸,但是广大观众,从未发觉有不协调之处。

刘竹友(饰刘备)之《黄鹤楼》
净角脸谱,原来以揉为主,在眉头、眼圈、鼻窝上、用墨笔勾勒,后台近看,十分粗糙,可是站在台下远看,倍觉神气活现。线条细致考究,色泽显明,始于京剧。京剧演出在大都市,舞台的构造与观众们欣赏程度,大不相同,净角为了讨好观众,脸谱勾勒越来越复杂,不但外国人看了要称奇怪,我们身为中国人,连中国戏上的净角脸谱,也无从理解。“为啥要把某些人物脸上,画上各色各样的脸谱呢?”这一问题,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有人向我提出,要求我明确解答(当时我担任上海国剧保存社出版的《戏剧旬刊》主编),我曾经求教于刘奎官、刘砚亭,金少山、程少余、马连良、侯喜瑞、钱宝森、李永利,他们都说只知依据师承,虽然也依据自己脸部轮廓,稍加变化,但不敢脱离传统,对勾脸的原理,一窍不通。后来我与寓于创造性的裘盛戎(盛戎面部象螳螂,别人的脸谱勾不上)和长期以来爱好把南北名净脸谱,从镜子上反映出来画到纸上的倪慰明、吕次维,时常来往交谈。原来他们也是从艺术观点出发,说不上脸谱的正确作用,从此我就开始研究脸谱。我收集川剧、潮剧、京剧、豫剧(大梆)、汉剧、秦腔、滇剧、昆曲、曹剧(山东曹州梆子)、河北梆子、晋剧、绍剧等等剧种的净角脸谱、二百余帧之多,其中还有个人创作的,如翁偶虹所画的,是足够出版一本脸谱集成,可是在我反复检阅之后,就搁了起来,因为在这许许多多脸谱上,并没有找出“为啥要把某些人物脸上、画上各色各样的脸谱”的答案。
也曾有人说脸谱是象征人物的,我对这一见解,表示同意。但是这一说法,对丑角是正确的,净角脸上添了五颜六色,要通过这些复杂的色彩,表现出生动的人物面貌和思想感情,是有困难的。例如赵玄坛脸上,脑门画一大钱,作为财神标志。姜维、公孙胜、庞统脑门画上一太极图,表示他们懂得阴阳八卦。杨七郎脑门画一草体的虎字,代表他是虎将。焦赞鼻梁上(潮剧)画瓣一绿色芭蕉叶,让观众知道我姓焦。闻仲脑门画一直立的眼睛,能看到三十三天。赵匡胤眉子上画一条龙形,作为有帝王之相。窦尔墩眉子上画了虎头双钩,因为他善使虎头双钩。典韦善使双戟,脸谱上画上双戟。包公脑门画一白色新月形、来说明包公阴间的事也要管三分。郝寿臣杨七郎脸谱,左右颊上各画一瓣芭蕉叶,以示他是命里注定要死在芭蕉树上的。如此等等作为象征人物武艺特点和命运,多数不可取法,尤其是郝派杨七郎脸谱上的两瓣芭蕉叶万万要不得,杨七郎是被绑在华标上乱箭射,并不是绑在芭蕉上,芭蕉是草本奇脆,不要说绑杨七郎,就是羊妈妈(母羊)也禁不起一碰。华标是巨大的石柱,现在北京天安门外亦有树立。把华标作为芭蕉,在脸上画上芭蕉叶,太过幼稚。不过利用脸谱来教化观众,而收潜移默化之功,也许是有些效果的。因戏班规定,失节人物,脸上就得添上色彩,那是作为变相论的。

钱金福之焦赞
但是这里面也有问题,从元末的朱元璋与陈友谅二人所言,当时都属于民族革命英雄,由于结果,朱成大业,陈遭失败;写剧本的就以朱为正统,陈非正统,朱元璋在《百凉楼》中遭火烧、吴祯救驾(俊扮),陈友谅在《九江口》遭火烧,张定边救驾,正因陈非正统人物,张定边是非正统的部下,只好委曲他脸上勾上紫三块瓦。再以三国戏来说,作家是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为根据,罗是包庇蜀刘,把吴魏作为非正统,正统归于刘玄德。黄忠、马超、赵云都是身事二主,照例都要在他们脸上添上色彩,因为刘备是正统,就作为弃暗投明、良禽择木而栖,免于脸上添色彩。严颜是非正统的刘璋部下,只好勾上三块瓦紫脸,可是张飞取巴郡,严颜投降刘备,严颜脸上彩色,就此抹去(见《定军山》)。太史慈在《神亭岭》上,是俊扮的青年英雄,降于东吴,太史慈脸上变成为青面虎同样的绿色碎样,因为东吴也非正统。
不过脸谱对社会效果,比较显著,因为戏班里还有一条“做坏事也要变相”的规定,果真有人自动对号,就能起些教育作用,如《四杰村》中余千,由武生俊扮,作为舍命救主的义仆。到了《酸枣岭》中这一位余千脚色,变成武净扮,面部涂得墨黑,作为鲁莽直的粗胚,而且是一个闯祸胚,骆宏勋用宝剑刺死巴术,就是由这一家伙怂恿的。《张松献地图》又名《西川图》,京剧上是用老生扮张松,因为刘璋非正统,刘备是正统,张松虽是西川刘璋之臣,因为他面向正统的刘备,希望刘备入蜀,作为弃暗投明的有识之士。可是川剧上张松,用丑扮作十不全丑相,因为川剧上把张松当作出卖疆土、出卖人民的叛逆,非如此何以服众,故作丑相以平民愤。京剧《九江口》中张定边,原是净扮,勾紫三块瓦脸谱,是一位忠心耿耿,舍命救主于大火之中的忠义老臣。可是在《战太平》中,张定边变了相,因为做了一件坏事,献诈之计逼降被擒的朱洪武部下名将花云,因此把他作为诡计多端的谋臣,用丑扮,勾白粉三角块于鼻梁上,用墨画斜眉子,鹰爪鼻,作为阴险小人的。从这些方面看来,勾脸谱是具有贬的意识。
但在另一角度来观察,恰恰与贬的意识有矛盾,所有历史剧上伟大的美臣名将,大都是勾上脸谱的,如《大回朝》闻太师(仲)、《将相和》廉颇,《上天台》姚期,《打金枝》郭子仪(见山西梆子)那是与戏剧组织上,即角色分配上有关。《将相和》蔺相如是老生扮,《上天台》汉光武也是老生扮,《打金枝》唐太宗又是老生扮,同场的廉颇,姚期,郭子仪,既不能再用老生扮,也不适宜用丑角扮,用净角扮最适当。象《大回朝》闻仲这一人物,是精忠、神勇、威严、刚强的重臣,他的性格和感情,也只有净角演来出色当行。

刘鸿声、裘桂仙之《上天台》
何况戏班里原来有这样的一条行规:“每一行当,都得抱演正反两派角色”。当年老前辈订立这一条行规,是有充分理由,他们说:“人们一张嘴,能说好话,也能说坏话,文人手中一支笔,既能歌颂功绩,又能揭发罪恶,唱戏为业的,有必要将反派正派一门抱”。所以旦角节妇烈女要演,荡妇淫娃也要演,老生虽然正常扮正派人物,但是《法门寺》上草菅命案的糊涂知县赵廉,就是老生扮,《铡美案》中绝灭人性、杀害妻子儿女的陈世美,也是老生扮。丑角扮的人物,好象大都是反派,其实丑角所扮青少年,无一不是热情仗义的小伙子,如《挑帘裁衣》中帮武大去捉奸的郓哥(后来向武松揭发王婆、潘金莲,谋害武大的也是他),《御碑亭》指责王有道无故休妻的德禄,《玉堂春》中,为苏三送信,去关王庙探望落难的王公子的卖花金哥等等。丑角所扮的老头儿,又都是善良的老年人,而且都是老有趣,常常用幽默的语气、滑稽的动态,为观众逗笑取乐,如《乌盆记》张别古,《鸿鸾禧》金松,《翠屏山》潘老丈,《女起解》崇公道等等。
丑角还得抱演丑旦(又名彩旦)。丑旦也有正反两派,反派专扮三姑,六婆和丑妇丑女。正派是扮正直、豪爽,勇武、泼辣的粗线条老妈妈,如《铁弓缘》、《新安驿》妈妈,《四进士》宗妻,《恶虎村》二嫂子,《霸王庄》贾氏等等。至于净角既要扮权臣赵高、曹操、潘洪、严嵩,又要扮忠义老臣尉迟恭、呼延赞、徐延昭、姚期、闻仲;既要扮鲁勇敢的如张飞、牛皋、焦赞、李逵,又要扮性格倔强的郑子明,地痞流氓的刘彪(《法门寺》屠夫)。总的来讲,行当中已有抱演正反两派的规定,勾上脸谱具有贬的含义、应当放弃,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有待于行家来参加讨论。
可惜,不但戏剧从业,连专业的净角,对脸谱作用和运用,也不想深入研究一下,只晓得继承上代,能够保存形式,已经算是称职,观众当然更无从理解,莫怪要提出:“为啥要把某些人物脸上,画上各色各样的脸谱呢?”我想,任何艺术,都是劳动创造,创造伊始,是有一定的原理存在,净角脸谱不可能例外,由于经年历代,有些夸大了,有些变样了,也有些出于个别演员异玄,搞出来的新花样,如名净郝寿臣的杨七郎脸谱就是当前一个例子。

郝寿臣
在抗日战争以前,北京曾出卖过纸型与泥型两种净角脸谱模型。由于京剧发祥于北京,当时北京人几乎全是京剧迷,故此这些净角脸谱模型,大都还合乎规格。现在杭州王星记扇店出售的京剧脸谱扇面和无锡惠山泥塑的京剧脸谱,这不过是投群众所好的消遣品,并不是供行家研究的有价值产品,因为造型与用笔过程中,并没有真正的行家参加其间,不过如姜维、张飞、牛皋、焦赞、孟良、关羽、刘瑾(代表太监脸),鲁智深(代表武陀脸),大体上还不成问题,可是单以张飞一个脸谱来说,头陀脸墨勾的蝴蝶,刘奎官与金少山不同,刘砚亭又与以上二人不同。由于各人的面部生相不一致,勾出来脸谱不可能同样,再说张飞脸谱,《白门楼》,《长板坡》、《古城会》、《取巴郡》、《造白袍》,都有改动。尤其是《造白袍》,还得改勾粉脸(原来都是油彩》墨里加一点白粉,白粉里加点墨,白粉变灰色,墨色变深灰色,勾在面上无光彩,是作为出现了死相的。单指出张飞脸谱,这是那出戏上的张飞脸谱呢?像曹操脸谱,从《中牟县》(即《捉放曹》)开始,到《阳平关》为止、在他粉脸上要添上多次奸纹:同一曹操脸谱《宛城》与《逼宫》、就大不相同,《阳平关》曹操成了魏王、气势就和其他戏中不同,脸谱上也要表现出不同于《长板坡》的感情,说明开勾脸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脸谱模型绘画
末了,我只好抄鲁迅旧作《脸谱臆测》结尾,作为我对“为啥要把某些人物脸上,画上各色各样的脸谱呢”?问题的回答。鲁迅说:“我想,这脸谱便是优伶和看客公同逐渐议定的分类图……况且我们古时候戏台的搭法,又和罗马不同,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现倘不加重,他们就觉不到、看不清。这么一来,各类人物的脸谱,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画化,甚而至于到了后来,弄得希奇古怪,和实际离得很远,好象象征手法了。脸谱当然自有它本身的意义的,但我总觉得并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台构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时候,它更不过是一种赘疣,无需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别的一种有意义的玩艺上,在现在,我却以为还是很有兴趣的”。鲁迅已经指出:“脸谱当然自有它本身的意义的”我看不应因噎废食,应当允许它存在,不过要开始进行改革,重新恢复揉脸,用人的皮肤色的红,黑、白为基本,以人的生理或性格特点为依据,以不影响表演效果为原则,通过舞台实践,逐步进行戏剧脸谱的改革,对新时代的新戏剧作出贡献,不应当考虑到极少数的老年观众的欣赏习惯。事实上这样改革,十年动乱以前已经开始,当时北京摄制的中国评剧院李再雯(即小白玉霜)主演的《秦香莲》戏曲片中,饰包公的演员,就放弃传统的包公脸谱,大胆地改为揉脸,把包公脸上的皮肤色揉得和终日在阳光下参加劳动的农民的皮肤色同样,突出运用眼神,和两颊颤动,来表达包公的性格和感情,非常成功,观众中,特别是爱好京剧的人们,他们不但并无反感,相反的,都说“改得有价值”,却不曾听到有人提出“不象包公”。证明当时已有很多观众同意改革旧脸谱了。时至今日,抱残守缺的老观众留存无几,新的观众,对传统净角脸谱,不感兴趣,此时不改革,等待何时?问题在于要大胆地在艺术实践中摸索试验,不断积累经验,逐渐闯出新的路子来。
(《艺术研究资料》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