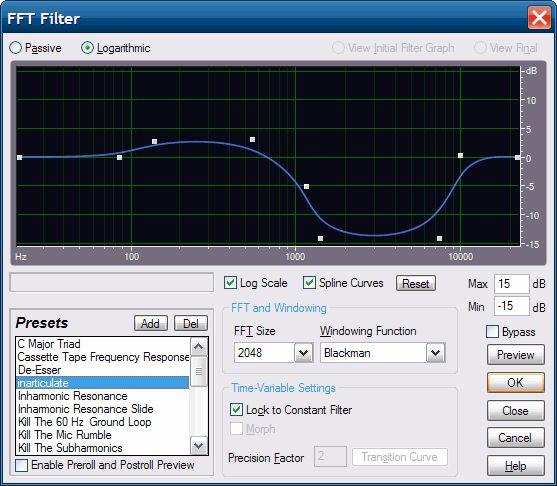《论语》中孔子说“仁”一般都是就事而论,始终没有给“仁”下过一个准确的定义。当樊迟问他什么是“仁”时,他也只是简略地回答说“爱人”。而《孟子》也说“仁者爱人”,这才使我们明白“仁”字具有“爱”的意思在里面。然而爱其实有很多种,爱的对象也不一而足,那么“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人又为什么要去仁爱他人呢?

“仁者爱人”
墨家的“兼爱”建立在利益之上墨子也主张爱人,他讲的是无差别的“兼爱”。墨子认为人性自私自利,大家都只知道“自爱”而忽略了“兼相爱”,这才导致君臣父子之间互相伤害,国家与国家之间也相互征伐,最终使得天下大乱。因此,为了防止混乱,需要每个人都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做到“爱人若爱其身”。如果说“仁者”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那么他首先得有“兼相爱”的思想,然后才能去行仁术,在墨子看来“兼相爱”成了“仁”的核心内涵。
要树立“兼相爱”思想,首先得克服“别”的观念,也就是说要不分彼此,将“自我”推广到所有人身上。墨子说: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人的本性是“自爱”的,我把对自我的爱推广到全人类,就上升到了“兼相爱”,而每个人都这么做,便可实现“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了。
墨子用“兼爱”来解释“仁”,而“兼爱”的来源其实是“自爱”。在讲到“自爱”时,墨子其实跟杨朱一样,都承认人性自私自利、只知道“为我”。所不同的是杨朱肯定“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肯为;墨子则否定“为我”,认为要克服它以便达到“兼爱”,即使为天下人奔走得大腿不长毛、小腿不长肉,他也在所不惜。天下人大多也都承认“为我”是人之本性,只是对“为我”的态度不同才分成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所以《孟子》说: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杨朱与墨子的原则其实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态度而已。墨子在“为我”、“自爱”的基础上扬弃出了“兼爱”,并用它来解释仁,因此比杨朱走得更远——也就是说,在墨子看来仁、爱人并不是人的本性,反倒是对本性的克服。
“兼相爱,交相利”
儒者与杨墨相反,他们不承认“为我”、“自爱”是人的本性。《孟子》主张人性向善,说“仁,人心也”,人的本心总是倾向于热爱他人,而不是固守着只爱自己。这是显而易见的,父母不总是爱护着自己的子女么?情人不总是爱恋着自己的对象吗?信徒不总是爱戴着自己的偶像吗?真正的爱是情不禁的,是理性所无法控制的,是超出利益权衡之外的。
除非一个人不生活在家庭社会之中,否则他做不到完全的自私自利、不爱任何人。当我们说人的本性是“为我”时,实际上是将人视为孤立的存在物,把他人一概当作陌生人,而且假定了人总是能够正确的实现“为我”。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在我们的周围有父母、子女、情人和朋友,我们愿意为他们牺牲自己,不计回报的付出一切,这显然违反了“为我”的“本性”。而且,我们并不聪明,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因此,“自爱”并不比“爱人”更接近于人性。
墨子在“自爱”的基础上建立起“兼爱”,然而“兼爱”并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为了所爱之人,我们可以将利益抛诸脑后,甚至能牺牲自己——爱排除掉了利。而墨子的“兼爱”不过是为了防乱、为了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而已,他不是超出自我之外去爱人,而是在自我之内,把“自爱”推己及人。因此“兼爱”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大爱无私,墨子就说:
“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不可胜计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
归根到底,墨子不是为爱而爱,而是为利而爱,他的爱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墨子把“仁”解释为“兼爱”,把爱人的理由说成是为了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是常人的想法,但它只是停留于经验和表象。
儒者的“博爱”思想孟子生活在杨朱和墨子之后,他对二人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知道墨子的“兼爱”只是对杨朱“为我”的扬弃。如果对“为我”进行批判,便可得出儒家的仁爱思想了。因此,《孟子》说: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
儒者认为流水有向下的趋势,人心也有向善的趋势,“泛爱众”是心的本能,也就是说心不仅会热爱人类,还会热爱万物。因此孟子提出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用来区分“仁”、“爱”与“亲”三个范畴。
- “爱”的对象是万物;
- “仁”的对象是人类、万民;
- “亲”的对象则是最亲近的亲人。
万物包括人类,人类包括亲人,所以“爱”包着“仁”,“仁”包着“亲”。孔子说到“爱”的时候,对象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人。例如他说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是指物;说“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对象是人;
当他说到“仁”时,对象必定是人类。樊迟问他什么是仁,他回答“爱人”;子贡问他博施于民算不算是仁,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当马厮着火时,他急忙问有没有人受伤,不问马的损失;他又教导弟子们“敬鬼神而远之”。可见儒者所主要爱的对象不是自然界也不是鬼神,更不是昆虫鸟兽猪狗,而是人类、万民。无差别的泛爱万物不属于仁的范围,仁的对象只有人类。当梁惠王因热爱国土而驱使自己的百姓去参加战争,导致他们大量伤亡时,孟子就说“不仁哉,梁惠王也!”相比于百姓的生命来说,国家的土地、国君的功业都是次要的,爱国不能以牺牲百姓为前提。
在人类之中,亲人得到我们更多的爱,所以叫做“亲亲”。“亲亲”是仁人乃至爱万物的起点,因为我们出生后最先接触到的就是亲人,对亲人之爱便是孝悌。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有若也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以孝悌为起点,仁爱人类、推及万物,这是儒者之爱的层层次序。墨子则以“自爱”为本,无差别地推及所有人,此为儒墨之分。
孔孟之后,佛老兴起,世人好神仙浮屠,忽略了爱万物、仁万民以及亲亲的职责。韩愈写作《原道篇》,提出“博爱之谓仁”的思想,劝阻唐宪宗不要迷恋佛骨,不要只空谈博爱众生。而忽略了人类、百姓,身为人就应当尽人的责任,不能为了追求自己的不死或涅槃而抛弃君臣父子、背离社会家庭,执迷而不悟。
孔、孟、韩愈都说明了“仁”就是“博爱人类”的意思,并且这种爱存在亲疏区别。到了北宋时期,张载写作《西铭》,解答另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博爱?
韩愈:“博爱之谓仁”
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认为三代之时,人们还懂得博爱人类,而到了现在,大家都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只懂得“亲亲”,不懂得“仁”了。
圣人则胸怀博大,不拘于狭隘之见,“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用礼法来治理天下。那么圣人博爱人类的依据在哪呢?张载在《西铭》进行了证明,根据他的气本论和气化论,人类与天地都是由气构成的,所以从源头上说,人类与万物皆为天地所生。故曰: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人类与万物同根同源,怎么能够自爱自己而不泛爱万物呢?但是万物毕竟不是我们的同类,在爱的程度上应存有差别。所以,我们将万物视为党羽,友爱它们;将人类视为同胞,仁爱之。所有人都生存在天地之间,年纪比我大的就是我的父兄,我敬爱他们就是敬爱造物的次序;年纪比我小的则是我的子弟,我慈爱他们就是爱护造物的生机。人不能把自己视为孤立的存在物,而是要看到自己生存于自然、社会和家庭之中,自然界为我们提供食物、淡水,社会为我们提供工作、教育和公共服务,家庭则监护我们的成长、保障我们的生存,人又怎能仅仅“自爱”而无视于这些恩惠呢?
张载认为让自己的德性符合于天地的人才是圣人,要明白自己在天地之间的位置与职责,爱万物,仁万民。天地是我们的存在之根,父母则是我们的生身之源,博爱万民而不亲父母,是为不孝。大禹为了父母而禁酒,颍考叔为了父母而请羹,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保持孝顺之心。
因此,人生天地之间,以亲亲为始,以仁爱为本,以泛爱为终,三者不可偏废,故统一为“博爱”。陷于“亲亲”,就是《礼运》说的“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有私无公;陷于“仁爱”,就是孟子说的“无父”,因公废私;陷于“泛爱”就是宗教的狂热,由公复私。信徒在鬼神、方术中迷失了自己,在上帝、佛陀的幻想里找到了升天与寂灭的幻想,他把一切送给了神灵,目的就是换来自己的永生、涅槃——终究是自私。
张载著《西铭》
张载的“理一分殊”思想《西铭》从天地大父母推及生身小父母,从“仁”推及了“义”。杨时读后觉得张载说仁跟墨子的兼爱相似,于是写信请教程颐。程颐在复信中回答说:
“《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无分。”
所谓的“理一”就是以亲亲为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对父母的亲亲之爱出发,推及鳏寡孤独、推及百姓万民,最终推到天地万物,越推分殊越多,但根本还是同一个“理”。墨子的“兼爱”则是无差别的推及,视自己的君臣父母与他人、他国相等,这种“爱无差等”做法容易导致爱心泛滥,甚至会陷入“无父”的境地。
因此,儒者强调要明“理一分殊”,不能偏私也不能兼爱,偏私失仁,兼爱伤义。要把它们统一起来——“泛爱众,而亲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