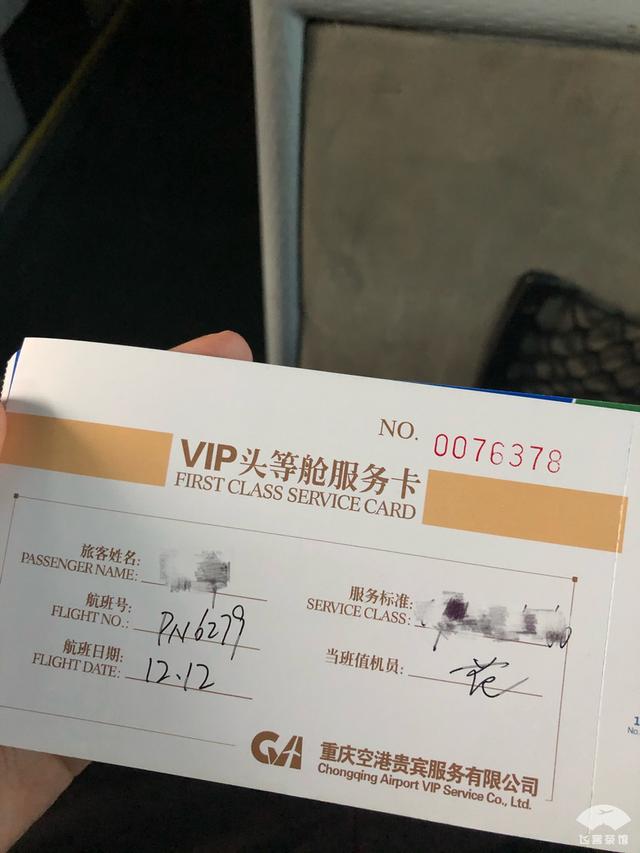城市头条/武汉
没有不被水流过的土地没有不被商业塑造的城

【图说:《武昌汉口鸟瞰图》(清1739-1862年间)】
在很长一段时间,外界认识武汉,主要是通过这“一个半人”。
一个是方方和池莉。她们都是武汉最能拿得出手的作家。不过两人都不是在此出生。前者江苏南京,后者湖北仙桃,还是仙桃一中的著名校友,但在她们成长的过程中,都和武汉息息相关,至今她们也生活在武汉,而她们的作品,也大多围绕着武汉人的鸡毛蒜皮而展开,在勾勒出武汉历史图景的同时,描述出了武汉的日常人生。
《万箭穿心》里的李宝莉刀子嘴,菩萨心,含辛茹苦却把儿子养成白眼狼;《生活秀》中的美丽女人来双扬则是婚姻不幸、亲人相争,但孤身一人活出了侠女范儿,帮弟弟打点餐馆,帮妹妹还钱,供侄子读书……
它们在改编电影之后,前者成全了颜丙燕演技炸裂,后者则让陶红成了第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
这些作品无一例外让人加深了对武汉“烟火气”的理解。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平凡而庸俗的日常中,忙忙碌碌地讨着生活。辛劳,坚韧,而又脾气暴躁,嘴巴从来不饶人,一开口,不是脏话,就是让人觉得像在骂人。天不怕地不怕,“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
就像易中天写武汉,“到武汉的机关单位去办事,门房会问:‘搞么事的?’而不会问:‘您是哪个单位,有什么事吗?’甚至做生意,他们也不会说:‘你看我们怎么合作?’而会说:‘你说么样搞唦!’”
即使如此,易中天也对武汉充满着感情。在他看来,外地人害怕武汉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武汉人。事实上,也正是通过他,让外界对武汉产生了另外一种观感。不过,因为出生在湖南长沙,成名在福建厦门,他算不上正宗的武汉人。但是自1978年到1992年,他有着长达十数年在武大求学和任教的经历。饮过长江水、吃过武昌鱼,让他也算得上是半个“武汉通”。
正是在自己那篇写武汉的文章里,易中天提到的武汉是“大”武汉,而不是小家子气的武汉——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城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属罕见。除了特快列车在武汉一个市就有可能停两次,它还架起了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它是上海以外又一个被冠以"大"字的城市。"保卫大武汉",就是抗战时期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
甚至,根据《吕氏春秋》中所言,"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易中天甚至认为,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地理加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个"天下之中",就该是武汉。因为中国最主要的省份和城市,全都在它周围。这也让武汉占尽了“九省通衢”的地利。
而且,有着"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武汉,有着气吞山河的气势,相比而言,开封太开阔,成都太封闭,杭州太秀气,而南昌、长沙、合肥则气象平平。
这样的武汉,不免让人向往。这样的气度,也曾滋养过易中天,让他日后有机会走上了《百家讲坛》,并写出了《易中天中华史》等煌煌巨著。
但让方方至今犹感慨的是,有着无数优势的武汉,过于认同自己的“俗文化”,几乎放弃了“雅文化”。
而易中天也在这里没有守候太久,等他登上央视的讲坛时,已经离开武汉十数年了。
“矛盾”的大武汉今天,在解释自己为什么离武汉投厦门,易中天的说法是,武汉暑热难耐。这其实是个借口,但听上去倒挺合情合理。
武汉,是中国有名的火炉之一。不管是四大火炉,还是十大火炉,都有它的位置。这跟它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长江从西南向东北穿城而过,然后又拐向东南。可以说,整个武昌的头上都压着一条长江。
古时讲,山南水北为阳,而武昌的位置只能属阴。一到冬天,西北风便带着长江以及汉江的水汽,扑面而至。所以,阴冷。而到夏天,需要有风的时候,武汉市内诸多的高山——汉阳的龟山(原名大别山,后又称鲁山),武昌的蛇山,还有武汉大学内的珞珈山,又是天然的屏障。
结果,南风吹不进来,武汉真的就热成了烤炉。热起来就天昏地暗,经久不息。武汉,武汉,感觉就像说“捂汗”。
在这样一冷一热,比较极端,很难温和的气候下,武汉人没办法让自己温声细语。所以他们的人生不喜欢假装,也不太讲究。外人不容易下口的热干面,被他们当成美食。一到夏夜,满街的凉床上,便是白花花的大腿。

【图说:武汉人把游泳称作玩水】
但得承认,这不是他们故意想这样。相反,往好处想,这样的环境和气候,容易培养出战斗和不服输的精神。
在湖北大地上,一直流传着“不服周”这样的俗语。外人在挑战之前,常问“你怕了吗”,湖北人喜欢给你扔上一句,“你服不服周?”对方如果更牛,“老子就是不服周!”把球就这样给硬踢了回去。
不了解这块土地的历史,你自然意会不了这句口头禅的精妙之处。其实,它来自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湖北包括武汉,是楚人的地盘。熊绎则是周朝诸侯国——楚国的始封君。在易中天看来,“楚人的精神是‘霸蛮’,楚人的传统是‘我蛮夷也’,”所以,尽管为周朝的开创做出了不朽的功绩,但在论功行赏时,熊绎只得到了“子”爵,排在其前的还有“公”、“侯”、“伯”这三个爵位。此外,他不仅被嘲笑是“楚子”,还被安排去看守火炬,堂堂诸侯,犹如奴仆。
这种赤裸裸的歧视,成功地激起了楚人的同仇敌忾。自楚君熊渠开始,就高喊着“我就是蛮夷怎么着”而东征西讨,在占领各个要地之后,分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要知道,王在当时只有周天子可称。
更牛的还有楚君熊通,他自称武王,公然建立楚王国。到了“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更是让楚国强盛一时,甚至因追击战败的陆浑之戎,一度陈兵周都洛阳。周天子派人去犒劳,“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而鼎在当时意喻天子的权威,庄王此举,有取而代之之意。

【图说: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歌剧《楚庄王》,看出湖北对那段历史的自豪】
也正是伴随着楚国的崛起和日益发展,当时的周王朝日薄西山、由盛转衰。尽管历史已经远去,但楚人“不服周”的传统自此流传下来。它绝对不是“它强任它强,轻风拂山冈;它横任它横,月光照大江”,而是你越强我越不服气不服输,你越强硬我越要比一比,就不信你比我强。即使一时失败,也摧残不了他们的信心,尽管秦灭六国,但楚国人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只有了解武汉人的脾性,了解此地的“不服周”,才会理解,为什么这个具有烟火气的城市,会出现张之洞这样的政治强人,会响起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会发生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到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成为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发端之地,还会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中立于潮头,创办了武汉光谷。
即使每个女人都活成李宝莉、来双扬,但在庸常中也一定会有一些刚硬的反抗。
进而理解,武汉为什么会成其为大武汉。
商业文明造就辉煌对武汉来说,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是自己近代“城生”形成的最关键一段时期。因为汉江改道了。
早先汉水自秦岭南麓逶迤而来,流经陕西、河南,然后在龟山之旁入江,时称鲁口。期间,其入江之口多有变迁。直到成化改道,它才有了一个稳定的入江口。
它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地理改变,那就是汉阳被一分为二,此前,汉口还只是与汉阳连在一起并隶属汉阳的荒州,也因此析出,并因沟通长江、汉水,以及洞庭湖三大水系,一下子变成了拥有巨大运输潜力的港口。

【图说:1969年《武汉市街道图》】
此时的中国,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汉口刚新生,便赶上了好时候。
很多陕西商人顺汉水而下,然后到汉口中转。周边的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和全国各地的商人,也逐渐在此聚集。
到清嘉庆年间,汉口已经发展成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的四大名镇之一。从此便是“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以至于“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埠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以前只有武昌、汉阳双城的武汉,渐成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立之势。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汉口又被辟为通商口岸,并于1861年三月开埠。不说不知道,当年的汉口有英、俄、徳、法、日等国在此开辟租界,多个国家在此设有领事馆。
这也让靠近汉水,又是汉口巡检司所在地,并由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联成的长街——汉正街(又称官街),成为这个国家最有名的一条街。
今天谈起武汉,除了烟火气之外,能想到的,一定是码头文化。当楚人的传统精神融入进近代商业文明,或者说,近代商业文明遇上了楚人的传统精神,两者不禁碰撞出了火花。码头上的船来客往,让武汉的人群构成更多元,也进一步打开了武汉的视野,和胸襟。而风里来浪里去,也让武汉变得更冒险、更拼搏,今天,武汉喊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也并非没有根由。不过,它也让武汉人多了一些小市民式的精刮,以及打码头的江湖习气。
让武汉更为之一振的,还在于老乡张之洞的督鄂。他从52岁的壮年,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干到了71岁的暮年,正可谓把自己最宝贵的最有经验的“青春”,奉献给了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
他创办的自强学堂,成了武汉大学的前身。他创建的汉阳铁厂,更是推动了武汉地区的工业聚集,以及早期的城镇化,与此同时,为了“练成一气,通盘筹划,随时斟酌,互相协助”,湖北枪炮厂和织布厂也一并创建。正是在他的大兴洋务之下,受地理和环境影响,自古以来便是传统的农耕经济,以及以手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没有一家官办或民营近代工厂的武汉,开启了近代化转型之路。
至于汉口,更是成了京汉铁路(卢汉铁路)的一端。这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准备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张之洞之所从粤调鄂,也和自己“要想富修铁路”有关。他曾陈述其有七利而无一害,其中有“广开商旅之利促进煤铁开采;方便漕饷之运;有利军队调动”,当然还因为“不近海口,敌不可资”。
随着1905年11月15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竣工通车。
它帮助武汉打破了仅依赖于水道与驿道的传统交通网络格局,自此迈入了火车时代。
方方在《汉口的沧桑往事》中写道:“当踌躇满志的张之洞抬腿由司门口踏上岸时,武汉便注定了它命运的改变。”

【图说:被江水和政治强人一起改变命运的汉口】
一时荣光焕发的武汉,也逐渐迎来了自己的“政治巅峰”——北伐时曾成首善之区,地主逃难时有“一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之说,后来在抗战期间,又当过几天战时首都。看上去,武汉似乎真的有了当这个国家首都的气象。
似乎终究没有变成现实。新中国的首都选择在北京。不过武汉也一度成为直辖市。湖北省的省会也没有搬迁。最后,直辖市机关在汉口,省会机关在武昌。两个机构在一个城市,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但到1954年,这个直辖市的名头被撤销,武汉重回湖北省省会。再后来,武汉变成计划单列市,很快这待遇又取消了。
易中天曾将武汉的命运归结为“得天独厚,运气不佳”,首先是国运不佳,打断了武汉的近代化进程,其次是四通八达、九省通衢,在和平时是左右逢源的优势,到战时便变成了易攻难守、腹背受敌的劣势。
所以,让易中天感叹的是,尽管和南京、重庆同饮一江水,“结果人家一个当了首都,一个当了陪都,只有武汉夹在当中,两头不沾边。”即使新中国成立让武汉有了新生,但改革开放之后,产业由沿江向沿海的转移,依旧让武汉脱离了主流的视野。
但在这一时期,不服输的武汉还是干出了一些亮色。当年货如流水的汉正街,冒着“计划”的大不韪,在“一百单三将”的坐地吆喝中,于1979年创办出了人流鼎盛的小商品市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个体民营经济之路。据说,那个时候全国人民脚上穿的袜子,80%都出自汉正街。
此后,全国小商品市场才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像知名的沈阳五爱,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都是步汉正街的后尘。这让当地的《湖北日报》在报道汉正街时,颇为自豪地引用经济学者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曾经说过的话:在中国,要看对外开放,得去深圳;要看对内搞活,则要来汉正街。
但更多的时候,武汉就像进入了那特色的夏天,让人昏昏欲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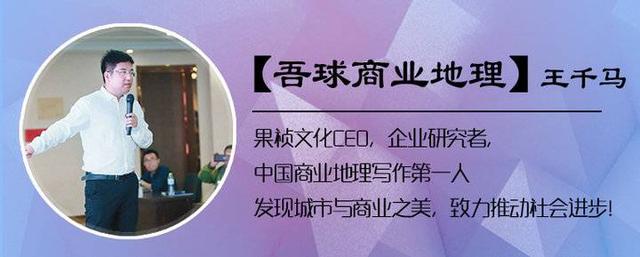
采写|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小说《媒体这个圈》、《无所适从的荷尔蒙》,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近年来相继推出《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海派再起》、《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紫菜爸爸》以及《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等作品。)
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编辑|大腰精
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不代表齐鲁壹点立场。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我要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