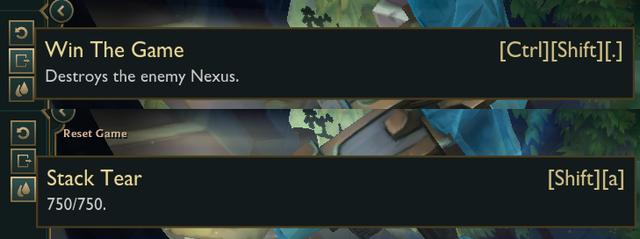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是唐朝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佳作,这篇《出塞》还引起了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龙城飞将到底是谁?”
这个争论甚至还波及到了司马迁,很多人都说世家子弟司马迁跟李广关系好,所以在《史记》中掺杂了私货,故意贬低卫青霍去病而抬高李广,以至于后人才会误解李广就是王昌龄笔下的龙城飞将。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那就是王昌龄本人也认为龙城飞将就是李广,因为在唐朝,是李家做天子,而李广和李渊都是陇西人,夸一夸李广是可以换取高官厚禄的。
但是我们细看《史记》和王昌龄诗作,就会发现这二位都很客观,《史记》没有贬低卫青霍去病,也没有刻意抬高李广,是有人断章取义,这才让我们误解了司马迁,甚至也误解了王昌龄:这二位都没说龙城飞将就是李广。
首先要解答的问题,是司马迁是否贬低了卫青霍去病

作为厌战阶层的代表,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屡次北征,或许有些不同意见。这也难怪,因为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大夫都是如此,从汉武帝时期的博士狄山,到宋朝的朱熹二程,直到明朝的东林党人,似乎都不太喜欢战争。
虽然对卫青霍去病北征颇有微词(当时还看不到长久利益,只能看到战争消耗,这是历史局限性,怪不得司马迁),但是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的战功,却一点都没有抹杀:“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置酒泉郡,后分置武威、张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

司马迁在对汉军损失表示惋惜的同时,也肯定了卫青霍去病缴获大量战略物资:“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于是引兵而还……取食于敌,逴行殊远而粮不绝。”
对卫霍缴获大书特书,甚至可能还有点夸张成分,这些文字跟寥寥数语的“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且司马迁之所以记载汉马损失,是为了解释汉朝为什么要设立大司马一职:“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
不管怎么说,在司马迁的笔下,卫青霍去病都是用较小的损失换取了巨大的战果和收益,这就是一个良心史家的董狐直笔。
接下来再看司马迁有没有刻意美化李广

司马迁对李广的记载,是功过分明。李广私受梁孝王刘武将军印、以欺诈手段杀降、泄私愤枉杀无错之霸陵尉,都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有明确记载。
如果不看司马迁的《史记》,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李广原来还做了这么多错事。
李广打仗确实勇敢,能够手格猛兽,但是司马迁对李广的勇敢,也并不是完全赞同:“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
从这两段记载中,我们能看出司马迁是不赞成作为将军的李广以身犯险的,因为这样也是对麾下汉军的不负责任,同时也明确指出了李广多次兵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李广太冒失。
如果我们细看《史记·李将军列传》,就会发现司马迁对李广兵败当斩是认可的:“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就连李广之死,司马迁也认为卫青没有一点责任,而且卫青当时是很客气地慰问李广并询问情况,看起来司马迁还有点替卫青辩解的意思:“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送给李广干粮醇酒),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

对李广之死有客观评价,司马迁也对李陵之降李家被灭有一个公正评述:“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能看出三点:其一,李陵是能逃跑而没逃跑,麾下步兵能跑掉四百多人,有马的李陵之所以不跑,是不想回到汉朝承担责任;其二,李陵到了匈奴,是在战场上立功并娶了匈奴单于女儿的,这一切都发生在李家被按律族诛之前;其三,陇西李家是以李陵为耻的。
我们也正是通过《史记》,才了解卫青霍去病的千秋功业,也知道了李广李陵的一些负面资料。
当然,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有批评,对李广李陵也有赞扬,但这正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功过分明,如果一味赞扬或诋毁,那么《史记》也就不会被后世史学家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了。
细看王昌龄诗作,就会知道他的赞扬的是谁

王昌龄是唐朝著名的边塞诗人,他在诗文中盛赞飞将军,还真没有奉承李唐皇室的意思,因为他根本就没说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飞将军就是李广,甚至也没说那位将军姓李。
笔者查阅了王昌龄所做二百一十首诗作,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出塞》,还有《从军行》《变行路难》等篇章都描绘了汉匈之战,并先后提到了参战人员和战斗地点:大将军、单于、龙城。
“大将军出战,白日暗榆关。三面黄金甲,单于破胆还。”
“秋草马蹄轻,角弓持弦急。去为龙城战,正值胡兵袭。军气横大荒,战酣日将入。长风金鼓动,白露铁衣湿。”
“单于下阴山,砂砾空飒飒。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

通过这三首诗,我们基本可以断定:王昌龄诗中能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龙城飞将”是卫青而不是李广,因为李广从未与单于主力作战,没当过当将军,更没一战封侯,而是在龙城之战中当了俘虏。
对于龙城之战,《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跟《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记载基本一致,只不过“龙城”分别被写为“茏城”“笼城”:“(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军各万骑,青至茏(笼)城,斩首虏数百。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李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贺亦无功,唯青赐爵关内侯。”
卫青率领一万汉军铁骑直捣龙城首战建功封侯,以后他和外甥霍去病就成了匈奴的噩梦,能让匈奴单于闻风丧胆落荒而逃的,还真是汉大将军卫青,这一点司马迁记载得很清楚:“大将军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彊,战而匈奴不利,薄暮,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

击溃甚至可以说是大部歼灭匈奴主力后,卫青又在一夜之间追杀二百里:“会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
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都含蓄地认为卫青没有一战擒斩匈奴单于,李广和赵食其是有责任的:“大将军之与单于会也,而前将军广、右将军食其军别从东道,或失道。”
《史记》比《汉书》多了四个字:“后击单于。”
所谓“后击单于”是后来参加了围歼战,还是因落后而没有参战,这一点读者诸君都心明眼亮,是不需要笔者赘述的。班固认为李广和赵食其都没参战:“大将军引还,过幕(漠)南,乃相逢。 ”
综合史书与唐诗中的记载和描述,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

探寻历史真相,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断章取义。如果我们把《史记》中关于卫青霍去病李广三人的记载多读几遍,就会发现司马迁是很客观公正地还原了绝大部分史实真相:既没有一味贬低卫青霍去病,更没有一味虚夸李广。
我们把史书与唐诗中的记载和描述综合起来,就会发现王昌龄不是李白,他也没有必要把盛赞李广而博取李唐皇室的欢心。细看王昌龄的边塞诗,我们甚至可以描画出《大将军卫青北征路线图》。
综合史书与唐诗中的记载和描述,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飞将军,是卫青而不是李广,但李广仍然不失为一代名将。李广的忠勇,只适合为将而不可为帅,他适合当先锋破敌阵,但是还不足以震慑匈奴不敢南下牧马。
真正把匈奴驱赶出漠南的,是卫青霍去病:“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
不管怎么说,卫青霍去病李广都是大汉名将:卫青霍去病扫平边患开疆拓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是任何人所能诋毁得了的;李广一生为国戍边,百战沙场而未能建功封侯,也有很复杂的原因,不全是因为他运气不好,但李广同样值得尊重——所有为国征战的将士都值得尊重,我们不能仅以成败论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