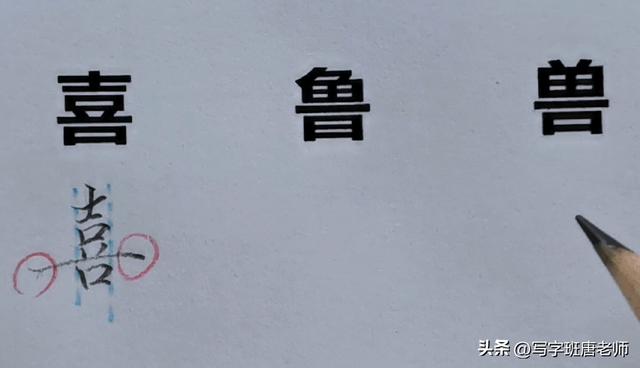爱情是《聊斋志异》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在其近五百篇的小说中就有一百多篇描写爱情婚恋,爱情题材不仅在数量上占了很大比例,而且从艺术成就上来讲,也是《聊斋志异》中最精彩纷呈的部分。其爱情表现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想象奇特,书中很多的爱情描写都具有很强的超时空性,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书中一些痴情、忠贞的男子形象,即使我们今天读来也仍会感动不己、自叹不如。
提到“情痴”,人们最先想到的便应该是《阿宝》中的孙子楚,文章开篇便用廖廖数笔描述了其“痴”的个性,“性迂呐,人诳之辄信为真。或值座有歌妓,则必遥望却走。或知其然,诱之来,使妓狎逼之,则颜彻颈,汗珠珠下滴”,“貌其呆状”,人戏称之为“孙痴”。可以说“痴”就是他的本性,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被人们嗤笑的呆子,凭借其对爱情执着和大胆追求的“痴”,最终获得了美好的结局。

“大贾某翁”为其女阿宝“择良匹”,孙子楚在别人的戏弄下“竟不自揣,果从其教”。知道此事的阿宝只是抱着戏弄的态度随口说了一句:“渠去其枝指,余从归之”,没想到孙竟信以为真,真“以斧自断其指”,以至“大痛于心,血溢倾注,滨死”。
过了数日,刚能动时他便“往见媒而示之”,以为阿宝会履行诺言,可此时的阿宝虽惊奇于他的举动,却并未有托付终生之意,于是再戏请去其痴,孙生认真“哗辨,自谓不痴”,面对对自己的不理解甚至有些戏弄的言语,他有些意冷了,只能告诉自己“阿宝未必美如天人”。
此时的孙子楚并未见过阿宝,这些痴的举动只能说是其天性使然,并未有情的力量,可见了阿宝之后,“情痴”的形象就马上突显出来了。清明郊游时,他终于看见了“娟丽无双”的阿宝,在众人议论纷纷时,他却“独默然”,看起来是“痴立故所”,其实魂魄早己追随阿宝而去了。

回到家的躯体只能卧床“终日不起,冥如醉”,家人无奈,只得去阿宝家招魂,此时的阿宝才真正惊骇于孙的痴情,被其深深打动了。在水月寺相遇是两人的第一次情感交流,此时的阿宝己动情,但碍于家世的差异,孙仍是求爱无门,再次病倒了,时时不忘阿宝的他竟化作了鹦鹉,飞到了阿宝的寓所,女“解其缚,亦不去”。“他人饲之,不食,女自饲之,则食”。“女坐,则集其膝;卧,则依其床。”且云:“得近芳泽,于愿己足。”
至此,孙子楚的“痴”己达到了最高境界,从求婚到断指,再到离魂化鸟,他甚至可以超越生死的界限,只为对爱情的坚韧执着,对心上人的一往情深。
《连城》中的乔生少有才名、仗义无私,是一个有肝胆、善良的书生。在连城的父亲史孝廉为女择婿时,他以两首题诗相和,得到了连城的喜爱,在连城“赠金以助灯火”时发出了“连城我知己也”的感叹,并从此“倾怀结想,如渴思啖”。

可是连城的父亲厌弃乔生的贫困,在二人相知不久后,便将连城许给了王化成。乔生虽绝望,但仍梦魂中不忘知己,连城也因此病不起,此病“须男子膺肉一钱”才能治愈,而此时的王化成却置身事外,于是乔生毅然“自出白刃,刲膺授僧,血濡袍裤,僧敷药始止”,为了爱情,他可以不顾疼痛甚至是生命。
当史孝廉食言无法将连城嫁与乔生时便设筵款待他,想以千金作为酬谢,乔生听后怫然大怒:“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己耳,岂货肉哉!”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报答知己之爱,虽然家境贫寒,但他不会为了金钱去站污崇高纯洁的爱情。
被乔生真情所打动的连城,出于无奈,自知将重病不起,便托温妇婉言劝慰乔生忘了她,去过美好的新生活,可乔生却慷慨坚决地说:“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诚恐连城未必真知我,一一但得真知我,不谐和害。”

他认为真正的爱情在于心灵契合,相知相重,而不在于色、貌,为了这样的爱情,他可以奉献自己的生命,而且如果是真知,即使不结婚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的“知己之爱”己经超越了婚姻的范式,达到了更高的精神境界,真爱在于它的价值而不是结果,所以他的愿望很简单,相逢时为之一笑,便死也无憾了。
于是在二人偶遇时,连城秋波转顾,启齿嫣然,向乔生发出了爱的讯息,乔生见之则大喜过望,发自内心地感叹“连城真知我也”,两个有情人的真心己牢牢地拴在了一起。为爱深感忧虑的连城在王氏议婚之后的数月便去世了,乔生前往临吊,竟“一痛而绝”,追随连城而去了。
这是痛苦的最高程度,是真情让他为爱献出了生命。死后的乔生在朋友顾生的帮助之下终于找到了连城,并不悔地表示“卿死,仆何敢生!”“仆乐死不愿生矣”,二人的真情感动了顾生,在他的帮助下二人得以“归生”。此时,乔生与连城的爱己超越了婚姻和生死,为我们宣扬了伟大的爱情真谛。

《瑞云》也是一篇与此类似的相知相爱的故事。瑞云为杭州名妓,色艺无双,虽流落风尘,却高洁自爱,向往美好纯洁的爱情。贺生“素仰瑞云,固未敢拟同鸳梦,亦竭微赞,冀得一睹芳泽。窃恐其阅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却未想到“相见一谈,而款语殊殷”。
贺生归后情不自己,于是修赞复往,忠情于他的瑞云想与他“图一宵之聚”,贺生虽内心欣喜向往,却无奈以实情告之:“穷之士,准有痴情可献知己。一丝之,己竭绵薄。得近芳容,私愿己足;若肌肤之亲,何敢作此梦想。”贺生不顾瑞云的身份而将其视为知己,可无奈家境贫寒,他只能以痴情来报答对知己的这份爱意。
后有和生者怜惜瑞云流落风尘,便略施小术使其相貌丑陋而无法接客。贺生见到她时她“蓬首厨下,丑状类鬼”,瑞云见他后竟“面壁自隐”,可贺生却并未因其丑而生憎,他怜惜瑞云,赎其作妇。此时的瑞云自知其丑,“牵衣揽涕”,不敢以伉俪自居。而贺生却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遂不复娶”。
贺生以此作为对知己的酬答,这份知己之爱己经超越了盛衰之变,让作者发出了“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易念”的感叹来表达对爱情忠贞的赞美,最终二人获得了圆满的结局。

作者在肯定歌颂这些男子在爱情方面高尚纯洁品性的同时,也对一些薄情负心、轻浮的男子进行了惩罚和批判。首先,对那些轻薄、单纯迷惑于色的男子进行了戏谑和惩戒,揭示了男子的劣根性。
如《翩翩》中的罗子浮,因秽行而“广疮溃臭”,行乞于市,后被翩翩医好,然而“甫能安身,便生妄想”,见到“绰有余妍”的花城便忍不住“阴捻翘凤”、“以指搔纤掌”,使得“所服悉成秋叶”,这样的尴尬场面无疑是对薄幸男子的戏谑和批评。
再如《瞳人语》中的方栋,“佻脱不持仪节”,“每陌上见游女,辄轻薄尾缀之”,这样轻薄的行径终致双眼失明,后因检省悔觉,才又见光明,但也落得重瞳的惩罚。《画皮》中的王生因贪恋美色又不听劝阻而招致杀身之祸,且让妻子受尽欺凌才得以重生,不得不说是对重色男子的惩戒。《画壁》中的朱孝廉经过壁画一游,“灰心木立,目瞪足耍”,让老僧道出了“幻由人生”的深刻警省。

以上诸篇中,作者只是对那些被色迷心的轻薄男子略施小戒,希望他们能吸取教训,有所悔改,而对于作品中那些忘义负心、行为恶劣的男子则进行了严惩、恶报。如《窦氏》中的南三复,与窦氏女交好,并发誓与其相守终生,而后却念其农家不堪配,假词循之,又因议婚大家女貌美财丰,遂决志于窦氏,窦氏“挞于室,听之;;窦氏与子坐僵死于门外,“抑何其忍”!“而所以报之者,亦比李十郎惨矣”大家新妇自经而死,南家自此稍替,数年无敢字者。新聘曹家女更是神秘诡谲,而南三复也终因屡屡恶行被论死,这是对负心汉的强调谴责。
再如《云翠仙》中的梁有才,遇见貌美的云翠仙便殷勤示好,取得云母中意后与翠仙结为夫妇,且又受云母相助得以坐温饱,却品行无端,整日与无赖朋友竞赌,更甚者竟听人戏言,想卖妻求荣,这样的德行真是令人发指,而这给自己带来的自然是行乞于市,虐死于狱中的悲惨结局。

再如《丑狐》中的穆生,他惧狐为异物,又厌其丑,然而竟因钱财而悦从之,并由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可是当丑狐“赂贻渐少”时他便开始心厌之,并聘术士“画符于门”,“背德负心,至君己极”。于是狐女发出了她绝情的报复,大闹设坛,割术士一耳,使物嚼生二指,受于其者,皆须要偿,使生家贫困如初。异史氏曰:“邪物之来,杀之亦壮;而既受其德,即鬼物不可负也。既贵而杀赵孟,则贤豪非之矣。夫人非其心之所好,即万钟何动焉。观其见金色喜,其亦利之所在,丧身辱行而不惜者?伤哉贪人,卒取残败!”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所赞扬的对待爱情的态度:追求忠贞、心灵契合的知己之爱,而对负心背义、轻薄重色的男子则大加批判。
撰稿/张聪【读史品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