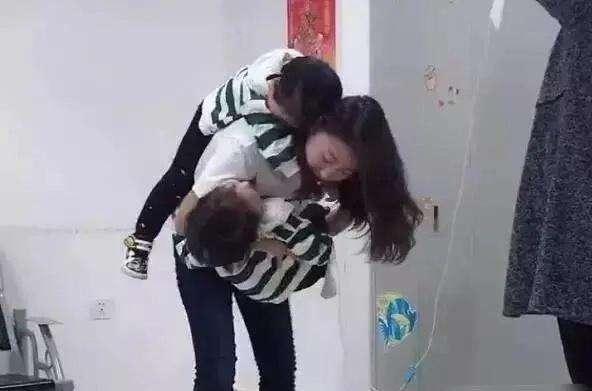我们经常说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并且会拿出“唐诗”、“宋词”、“元曲”作为例子。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元曲却不能与唐诗宋词的地位等同。
大多数的人都能随口举出几首经典的唐诗,宋词的情况也还好。但一提到元曲,好像除了《天净沙·秋思》外,就很难再找出其它的篇目。有的人还知道《窦娥冤》和《西厢记》,但真正看过的人寥寥无几。学生们通常知道“元曲四大家”,因为那是考试的内容,而把他们的代表作都看过的估计就屈指可数了。
元曲的确是元代最为繁盛的一种文学形式。一般认为元曲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元朝开始的几十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文人学子们出仕做官的道路被封死,迫不得已转向了戏剧的创作。而这些文人型作者的加入,为元曲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分别以前述《天净沙·秋思》和《窦娥冤》为代表。其中杂剧的题材非常丰富,有风花雪月,悲欢离合;有忠臣义士,孝义廉节;有冤狱公案,民生疾苦......这中间有一类题材比较特别,主要是表现帝王的爱恨情仇,其代表作为马致远的《汉宫秋》和白朴的《梧桐雨》。

《汉宫秋》全名为《破幽梦孤雁汉宫秋》,讲述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但剧情做了改动。王昭君因为不肯贿赂毛延寿而被故意画丑,结果被打入冷宫。其后因弹奏一曲琵琶得以和汉元帝相见。毛延寿逃至匈奴处挑拨单于南侵索要昭君。由于文武百官的无能,昭君主动提出愿意和亲。元帝无奈答应并送至灞桥,昭君行至汉与匈奴交界处投水而死,匈奴害怕与汉结仇便将毛延寿捆绑送回。之后元帝梦中与昭君相会,却被孤雁的哀鸣声惊醒。
马致远写《汉宫秋》用了颇多的文人笔法。元剧中一般人物登场要先念几句上场诗,用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或是展现内心活动。《汉宫秋》开篇就是呼韩耶单于的上场诗,起头两句“毡帐秋风迷宿草,穹庐夜月听悲笳。”语句意境皆美,只是和呼韩耶单于的身份形象并不相符。我们很难相信蛮荒之地的匈奴王会如此文绉绉,这可能是马致远对自己文学才能的一种炫耀。
再看汉元帝于灞桥送别王昭君后的一段经典唱词。
【梅花酒】呀 !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这段唱词先描写了元帝眼中的秋景,将自身置于一片迥野悲凉的背景中,然后展开抒情。想象自己独自返回咸阳后的凄凉场景,由此表现出元帝内心的悲苦孤独之情。这里无论抒情的方法还是技巧,均是文人手法,可以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
孤雁是我国古代文学中常用的意象,杜甫、柳永、苏轼等都曾在作品中使用过。大雁具有群居、迁徙的特点,而离群的孤雁就有其特殊的象征。失伴和失群往往和孤苦凄凉联系在一起,而孤雁的哀鸣声代表着渴望回归到同伴或是群体之中。《汉宫秋》第四折中借助秋夜里孤雁哀鸣表现了汉元帝对王昭君的忧苦思念之情,也表达了对美满爱情的渴望。
3
戏剧不仅只是作者情怀的展现,更是面向民间的艺术,因此《汉宫秋》里面也有迎合观众的一面。比较典型的就是其中夹杂的喜剧成分。比如在王昭君初见汉元帝后的这一段:
【金盏儿】你便晨挑菜,夜看瓜,春种谷,夏浇麻。情取棘针门粉壁上除了差法,你向正阳门改嫁的倒荣华。俺官职颇高如村社长,这宅院刚大似县官衙。谢天地可怜穷女婿,再谁敢欺负俺丈人家!
这一段是王昭君请求汉元帝对她的父母施些恩典宽免,汉元帝一口答应并且幽默了一把。这里的皇帝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而是以一副完全平民资态在调侃,整段充满了轻松愉快的气氛。而随后元帝和昭君告别的这一段词也很有意思:
明夜里西宫阁下,你是必悄声儿接驾,我则怕六宫人攀例拨琵琶。
王昭君因弹琵琶得以遇见汉元帝,元帝临走时还拿这个事情来调侃,在这里也起到了放松气氛的效果。戏剧不仅只是文本,它同时也是舞台上的艺术。在悲剧的背景下夹杂喜剧的元素,既可以调整剧情的节奏,又能够放大悲剧的效果。
4
戏剧还有一个作用是教化民众,将忠奸、美丑、善恶都在舞台上展现,并且抨击丑恶、褒赞善行,从而起到感化民心,激发良知的作用。文人士大夫自然通过诗书礼义来进行道德教化,但多数的底层人士并没有这种机会,因此很多历史知识,人文伦理是从戏剧中学习而来的。
例如《汉宫秋》第一折开始时,反派人物毛延寿的上场诗“大块黄金任意挝,血海王条全不怕。生前只要有钱财,死后那管人唾骂”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上道德败坏、见钱眼开的行为进行辛辣地讽刺。
5
白朴也是文人型元曲作者,一般把他和马致远和王实甫归为一类,区别于以关汉卿为代表的民间派。他的代表作品《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描写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和诗歌《长恨歌》及唐传奇《长恨歌传》所叙述不同,《梧桐雨》中的唐玄宗没有从道士处得到杨贵妃死去后的消息,而是梦中被雨打梧桐之声惊醒,“雨湿寒梢,泪染龙袍”在孤寂中追忆往昔。
《汉宫秋》和《梧桐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末本戏,以末角为主唱。末角的身份都是皇帝,又都是以旦角的死亡来展现其悲剧性。并且为了剧情的需要,都对原故事作了相应的改动。
《汉宫秋》把汉朝强大匈奴弱小的背景作了调换,将汉元帝赐王昭君下嫁改为呼韩耶单于大兵压境来抢人;《梧桐雨》中将安禄山造反的原因归结为意图强抢杨贵妃。这些艺术上的虚构除了使剧情冲突更具有张力外,还有其政治上的隐喻。
这里的皇权不仅是皇帝本人的象征,同也是也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当皇权并不能保护深爱的女子,甚至要牺牲所爱人的生命来保护国家的完整和皇帝的安全时,这个爱情悲剧的背后,实际上也是民族的悲剧。
马致远和白朴生活于宋、金和元改代之际,并且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当他们目睹蒙古铁蹄对文明肆意践踏,吏制败坏、贪官横行,而他们所学的“修齐治平”之道在时代的背景下显得苍白无力,毫无用武之地。他们内心必定也充满了矛盾和困惑,他们对统治者和上层阶级的无能表示不满,因此在《汉宫秋》中马致远批评文臣武将不能保家卫国,《梧桐雨》中白朴对唐玄宗纵情享乐、废驰朝纲的行为也有讽刺。但是同时也应看到,作者对两部悲剧中的主人公汉元帝和唐玄宗,所表现出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责难。在面对异族入侵时,连天子都和普通人民一样,成为一个受害者,这样描写体现了作者对中原陷落王朝的同理心。
6
元杂剧中以王昭君为题材的剧目不止《汉宫秋》一篇,而表现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的剧目据考证也有七八种之多。有需求才有市场,这说明帝王的爱恨情仇是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
在上述两部剧中,皇帝的形象并不高高在上,而是和普通平民一样会为爱欣喜、为情所困,面对生离死别也会痛苦无奈、伤心流泪。这对观众而言从心理上拉近了和统治者之间的距离,仿佛原本横在他们之间的巨大鸿沟变得不那么明显。这其中还包含着一种窥探、猎奇的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在目前的荧屏上,古装剧和历史剧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往往其中会突出表现封建帝王的感情生活。只是在现代编剧的笔下,又增添了许多的宫斗、争宠等狗血剧情。甚至会把现今社会的职场、家庭、励志等元素打碎杂糅,融合到宫廷情爱剧中。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也是满足了普通民众对前朝统治阶层的猎奇心理。
其实再放大一点看,社会上的追星现象也是一种窥视和猎奇。特别是在当今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整日沉迷于搜集偶像的八卦新闻、在社交媒体上和偶像互动,会给人一种可以接近偶像生活的错觉。而这其中,往往会产生一些误解,我们的前人也已经有很好的例子。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描写唐玄宗回到长安后对杨贵妃的思念,用了下面两句“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后来就有人指出白居易写得不合常理,因为普通人家才点油灯,皇宫里面是点蜡烛的,并且彻夜不熄。唐玄宗再怎么思念杨贵妃,也不会和平常人一样,夜里守着一盏油灯独自伤心。
这说明文人在描写上层阶级的情感时,往往还是把自身的体验代入其中。而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以自身的悲苦体验去想像皇帝的悲若,却无法体验到做皇帝的快乐,更让人悲哀的是这种快乐却常常无法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