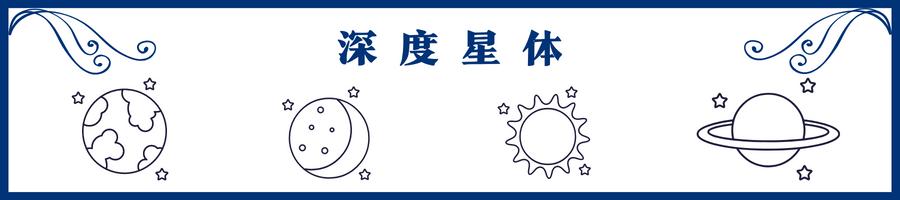石涛一生的风格多变,这是随着他的经历和年岁的发展而相变化的,那么考证他的年岁则显得尤为必要。而了解他的艺术特征,从他的现实行为入手,相反的可以和年岁的考订去相互的联系、推敲。认识一个画派,首先是要详熟它的传承。清初是董其昌南北宗之论,四王风格盛行时期,如四王恽吴为主流的重“南”贬“北”,而金陵的石溪,江西的八大山人,安徽的梅清以及扬州的石涛则是完全处于主流之外的。


虽然这些画派与主流画派格格格不入,但他们的渊源师承,并无二致。四王恽吴沿袭了董其昌所推崇的从北宋和元一直到明代的吴派,反观石涛,同样也是此路数而来。只是他与南宋到明代的院派,确实是丁点不沾的,在当时而言,喜好元人的,大都推崇北宋,而石涛却与众人有着不同之处。“未见有斩关手眼”这是他对郭熙的评价。依石涛的路数,宏观去看,早期多是走陈洪绶,中期有着沈周、元四家的影子,当然对于沈石田,石涛不愿意提及,就像他从不谈陈洪绶一样,但是这也避免不了他在画中有着沈石田体貌的东西,而他的笔意与画风,也跟倪瓒与梅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古人常不愿提及自己师承所属,想必石涛亦是如此。

石涛对绘画中感受的成分尤为强调,主张创作既是用心的感受通过实际操作的结果,包含了大量的自觉性。并且豪言一画之法是自己所创,前无古人。所谓一画之法,并不是死守一种画法。石涛曾说过,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吴冠中先生也对此作出自己的解释:“只求效果,不择手段,即择一切手段”。7我的理解既是: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表达自我,便是一切技法的源泉。

其实在中国的绘画史中,这种自觉性早在石涛之前就已经开始。石涛身份立场中的种种相关因素的构建,对发觉他语言上的策略性定位与不明显的自觉,显得尤为重要。石涛的艺术实践与他复杂的社会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的行为与他所表现出的绘画观念时常有着实际的冲突。他认为自己的绘画中有着独特的、持续的、绝对的、自成世界声音或是观点,但这却不是支配他生存与创作下去的唯一成因,这些能动性、支配力与自我中心的隐喻,使我们更接受他的作品就是某个主体的显现。

由于在康熙六十多年这一时期中,异军突起的这些与六家画派截然不同的闲士们,虽有着同源的师承,但他们能在传统基础上抒发自己的创造性,不在传统的笔墨与形式上兜圈子,因此,都具有独特的面貌。如龚贤就曾自诩笔意“前无古人”,虽有夸大,但足以说明他是不为传统所左右的。而这几家之中,尤为石涛的创造性,更为丰富和大胆,也更加的杰出。人能以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

石涛的“野逸画”中,最主要的便是石涛对其生平事迹的公开展示已到了当时其他画家无可比拟的程度。八大山人毫不保留地公开其所栖息的内在生命,石涛却实际上把过去看待成现实的另一面,并为此创作不懈。其他野逸画家或许会再三重返生命历程的几个高潮,例如梅清回溯两度黄山之旅,或戴本孝对登临华山的缅怀;石涛对其过往的沉湎却绝对无迹可寻。除了略去北京时期的雄心壮志之外,石涛的追忆绘画并无足以识别的模式,似乎总是某个片刻的种种思考之回应。

一整套册页可能为描绘生命中的一段时期,或过往不同时空的总和,抑或是融合了过去与现在。某些特殊的经历是一再重复的主题,例如横渡洞庭、登临黄山、三访长江边上的采石矶,或是南京近郊胜迹如东山之行。隐藏在这许多画中的共通主题,是撤逐漂泊的自我,一个当朝代更迭的大动乱尚记忆犹新时会激起尊敬与同情的主题。当然,以一名四海飘零的王孙遗孤来说,就更具说服力。到了石涛绘画生涯的后期,石涛已经可以确定,这种绘画的直接对象对大架构的历史至少抱有一个朦胧观念,在这个背景之下,任何作品的零星片段都具有其最具意义的脉络。那段记录于毕生诗作并不时在回忆中浮现的丰富经历,正是石涛最珍贵的资本。

石涛的兰花可上溯到少年时在武昌学画的早期阶段,指导者是一位卸任官员,他对这个美德图像的主张其进士功名所保证。然而,兰花也是石涛作为中国西南部出身画家秉赋的一部分,当然,石涛在晚年时可能另有不同的主张。他回归遗民思想使其得以在宋朝遗民画家郑思肖(1241-1318)的传统之下,以兰花图像的道德精神作为遗民的象征而自居。而且,石涛就像当时王孙画家诸如八大山人、过峰和兰江,也利用兰花作为自己高贵血统的标志。
对任何一位文人画家来说,绘画的表现特性,即绘画作为行为痕迹就是其品德的证明。而这也揭示了代表石涛野逸绘画的一个主要面向:即兴创作。石涛说:“人能以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8在这里,抹去了笼罩在“一画”概念上的玄虚的色彩,把它真正归还到作为绘画造形手段的一笔一画的本位。对于文人,这些即兴作品主要不为展示技巧,虽然它们经常如此,而是理论上非预先计划的自然性情这位不羁的道教画家,借美酒或某些超凡灵感的诱发而将画作点石成金,这种一度被公认为属于浙派绘画的形象,被石涛转变成自己的特色,以此满足从来视绘画为娱乐的扬州市场。

回顾石涛半生的经历,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个摆荡在两种矛盾欲望之间的人;他一方面被社交、旅游与艺术等乐趣所吸引;另一方面又渴望成为一名成功的禅宗大师,即所谓的成功包括世俗面与精神面的层次。我们见到他在一连串的时点上掌握自己:先是他在武昌短暂的停留的尾声,接着是投入旅庵的门下,以及第二次从歙县返回宣城时认真参与修复自己寺院的工作等。#文化#
我认为他给人的摆荡印象是正确无误的,甚至与石涛性格的基本面向相合不悖、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石涛未来生活中持续存在的特征。然当我们从公众目的与政治企图这方面来看,他的早年岁月则呈现了不同模式。因此,就现有的片段证据来看,1663-1664年正是一个清楚的时代区隔。在这之前,石涛看似随着偶发的际遇来反应,知足并安于僧侣角色、一方面认同明遗民的情感,一方面又愿意与曾在清朝为官之人习画。作者/李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