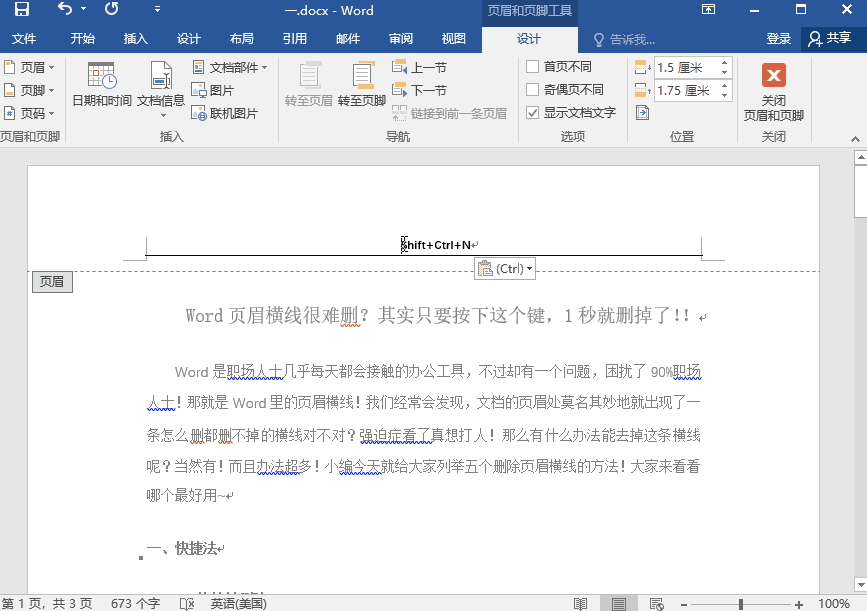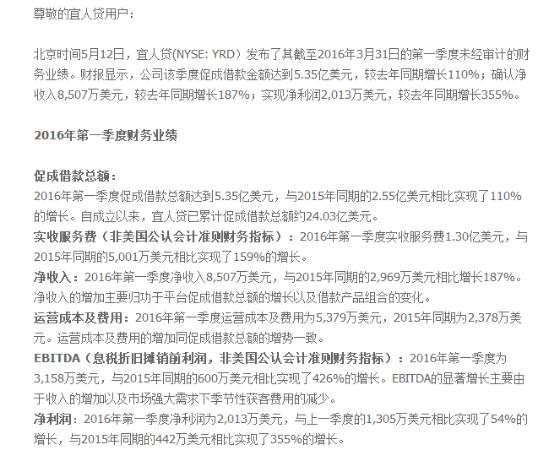当光阴慢慢划过,时间抚平伤口,这些背负了“慰安妇”沉重标签大半个世纪的老人们,如今又身在何处,过着怎样的生活,经历着怎样的悲喜忧乐?
她们,曾经是风华正茂的少女,本应有着跟大多数人一样的人生轨迹。
然而,日本侵华战争终结了她们的青春。“慰安妇”,这个沉重的标签伴随了她们大半个世纪,也折磨了她们大半个世纪。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先后沦为“慰安妇”。
有学者指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使用国家力量、采取强制手段、针对外国女性的性奴隶制度,这样的国家犯罪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令人发指。
72年过去了,健在的“慰安妇”越来越少。3年前,还有24人,如今只剩下14人,其中,海南有4人。
黄有良:至死也未等到道歉

黄有良
8月12日晚9时左右,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瓦房内,90岁的黄有良痛苦不堪,不断呻吟。
住在隔壁的小儿子胡仁富干了一天农活睡着了。起初,他以为母亲像往常一样,身上的风湿加剧,又喊疼了。听见母亲的呻吟声,他起床端了碗水走进隔壁房间,发现母亲已经不行了。随后的几分钟,母亲面容渐变惨白,眼睛望着漏雨的屋顶便没有了呼吸。
胡仁富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老人离世前异常痛苦。
随着黄有良老人离世,中国大陆所有“慰安妇”原告均已逝世。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先后有24位“慰安妇”幸存者作为原告、在4个起诉案中控告日本政府,全部败诉。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的研究表明,1941年,日军入侵了黄有良的家乡。当年10月,15岁的黄有良在收割水稻时被日军撵至家中并遭到性侵。此后被抓进了慰安所两年。后来一位村民壮着胆子向日军谎称黄父去世,央求放黄有良回家奔丧,黄有良才脱离了慰安所。
之后,家人在村里起了两个坟堆,假装是自杀的黄有良和其父的坟墓。随后,一家人连夜逃往100多公里外的保亭县。直到日军战败,她才敢回到家乡。
可世俗的眼光,如同战争留下的伤痕,伴随了黄有良余生。无奈之下,她后来嫁给了一个麻风病患者。“他知道我的过去,一有气,就打我,骂我。”
在将5个子女养大的过程中,黄有良从未主动提及这段往事。1993年,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符和积来调查慰安妇的境况,她一直缄默不语,在征得丈夫同意后,才鼓起勇气,道出往事。
黄有良的离世并未在当地掀起波澜。葬礼上,除了亲属,还有同村三四十位乡亲、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和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五名志愿者和几名记者、一名当地干部。
这一天,正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我国首部获得公映的“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在全国上映,黄有良的影像永远定格在了电影中。
至死,她未等到那一声道歉。
卓天妹:被关押四年后父母离世

卓天妹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宿风村92岁的黎族老人卓天妹已经不能下床。
半个月前,傍晚时分,看到《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镜头时,卓天妹试图坐起来说些什么,但喃喃自语了几句黎族方言后,便没有了力气。
老人床前的小木凳上放着一碗煮好的稀饭和一小碟菜。儿媳妇陈玉琼说,最近老人气喘加重,饮食也不规律,“饿了就扶起来吃两口。”
几个亲属专程从附近村庄前来探望老人的病情。陈玉琼炒了一盘苦瓜叶、炖了半只鸡、一小碟酱料,就着干饭,四五个人在外屋的院子里围着一桌聊起家长里短,不远处几只小鸡跟着母鸡身后钻进鸡笼。
“婆婆命苦啊。”陈玉琼介绍,卓天妹是以招工的名义被强行掳走,一同被掳走的还有同村的二十多个姐妹。她们白天给日军挑水、洗衣服、煮饭,晚上还要遭受蹂躏。有时还要跳黎族舞蹈,唱黎族歌曲。日本人稍不满意,便会遭到毒打。在受强暴、殴打、劳累饥饿的多重打击之下,卓天妹的身体终于被击垮。直到日本战败,她才回到家。彼时,她已经进去了四年,而父母都已离世。
苏智良的研究显示,海南本土的“慰安妇”受害者基本上是在村子里被日军强掳,或者被以招工的名义诱骗至军营,绝大多数受害者除被性侵外,还被迫从事体力劳作。沦为“慰安妇”的受害者包括汉、黎、苗、回等多个民族的女性,绝大多数人被性侵时仍是未成年少女。
卓天妹先后有过两段婚姻。第一次嫁给一个比自己大7岁的中年男子,但只维持了两年,男子因病离世。按照当地习俗,卓天妹两年后才又改嫁到现在的村庄。
如今,卓天妹的记忆已经模糊,眼珠也渐渐失去了光芒。看着卧病在床的阿婆,回忆往事时,陈玉琼数次哽咽,泪珠在眼里打转。
数年前,当志愿者前来采访调查时,老人含糊几句后再也不说话。等到夜里,卓天妹挣扎良久走进儿媳的房间,将屈辱和盘托出,两个女人抱在一起哇哇大哭。“我的婆婆很伟大,她没做错什么。”陈玉琼说。这既是对婆婆的尊重,也是女人对女人的同情。
陈连村:没说几句,便落下泪来

陈连村
8月下旬,正午的阳光直直照在海南万宁市大茂镇进坑村。气温已飙升至38℃,湿热而沉闷。
村里一个错落有致的庭院内,91岁的陈连村正在吃午饭,老人意识清醒,平时还能独立煮饭、喂鸡。在客厅坐下来后,她一直拉着《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手,没说几句,就落下泪来。
儿子张先雄坐在母亲身旁,向记者勾勒出母亲落入魔窟的大致经历。
十三四岁时,家住保亭县加茂镇毛立村的陈连村在放牛路上,不幸被日本人撞见,此后遭到性侵。路过的好心村民将昏厥的陈连村抬回家中,陈连村父母以泪洗面,靠着黎族草药调理了半年才恢复了身体。
然而,噩梦并没有结束。此后全村人被日军强征修路,长相清秀的陈连村白天在工地做苦力之外,夜里还要被强迫给日军提供性服务。陈连村不知道,彼时,海南岛已经沦陷,和她同样遭遇的还有上千名姐妹。
史料记载,1939年2月,日军入侵海南,作为进攻东南亚的重要基地。日军在此大量驻军,并于第二年陆续占领海南的大部分县城和乡镇,并在交通要道、重要村庄建立起军事营地和军事据点。到1941年共有据点360余处,日军围绕这些据点实施蚕食、扫荡。
据日本作家水野明撰写的《日本军队对海南岛的侵占与暴政》一书记载,仅在崖县、昌江县、八所镇、那大镇的日军慰安所,就有慰安妇1300人以上。以此推算,彼时海南16县76间慰安所的本地慰安妇人数,先后应达5000余人。
受不了侮辱的陈连村试图逃离,又被抓了回来。鬼子让她们跪成一排,从背后用棍子抽打腰椎。此后,陈连村放弃了逃离,直到日本战败才回到家中。
放牛路上遭遇鬼子的经历,让陈连村对“出门”始终心存恐惧。张先雄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在生产队干集体活,只要天稍擦黑,她就要等别人同路才敢回家。即便后来给自家菜地干活,她也必定赶在天黑前回家。甚至连赶集,她也绝不会外出超过两个小时。
72年过去,陈连村内心深处的伤口仍未痊愈。惊恐、伤痛,似乎从她的少女时代一直延续至今。
李美金、王志凤:守住秘密远嫁他乡

李美金

王志凤
91岁的李美金和92岁的王志凤都住在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由于媒体采访和外界关于慰安妇的调查,她们的“慰安妇”身份近些年才被村民知晓。
1940年,王志凤在澄迈县山口村家中被日军强掳,关押在附近的大云墟据点。一年后,李美金在澄迈县茅圆村被掳,关押在日军设在隔壁临高县加来机场的据点。
日军投降后,在相当长时间内,两位女孩再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这段经历,选择了偷偷嫁人,又恰巧都远嫁到了土龙村。
为了守住秘密,王志凤前后四次搬家,丈夫去世时也不知道她“过去的故事”。“他死后我才敢说。”王志凤苦笑。
王志凤夜里会还做噩梦。这几年睡眠也越来越差了。老人偶尔会喃喃自语,她说,假若还能见到曾经伤害她的日本人,她一定会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现在上哪找他们去?”《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问她,是否会接受这些日本人后代的道歉。“我会接受,但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你的爸爸、爷爷曾经做过什么。”她说。
记者来到李美金家时正值晌午。在村口一棵百年榕树下,她正靠在一张塑料椅上乘凉。虽皱纹满面,却依旧泛着光泽。老人双手戴着一对镯子,手握拐杖,一身紫色花纹的短衫,整个人显得慈祥、安宁。
“日本人坏透了。”这是李美金重复最多的话。在人生晚年,老人反倒愿意敞开心怀。严守一生的秘密,就此打开。
时至今日,耳背了、眼花了,她还在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给儿孙们上“政治课”,叫他们不要忘记了日军当初的暴行,并珍惜眼下的生活。
百年榕树下,阳光明媚,微风轻拂,树影斑驳摇曳。李美金时不时唱起儿时的歌谣,伴着低沉旋律的还有鸡鸣犬吠和母猪带着小猪散步的哼哼声、小孩的嬉戏声、村口小卖部里的麻将声。时光中的秘密默然守候,被老人的歌声和盘托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金红 卜多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