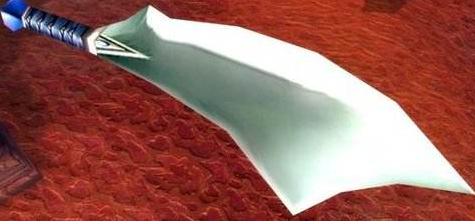文/杜遂东
母亲不在了,可她亲手做的腌菜酱豆子却一直是我最难忘怀的美味。
那些年,家家户户境况都不太好,尽管已经可以填饱肚子,但天天吃的地瓜干馍(在今天反而是好吃的东西了)和喝的玉米糊粥,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实在难以下咽。平时能够用来就馍饭来吃的菜并不多,不外乎就是一些腌胡萝卜、白萝卜、芥菜疙瘩。而天气一冷,大家就有口福了。
秋收过后,初冬来临。母亲便会早早地准备我们全家七口人一冬的下饭菜,腌一大缸酱豆子。
母亲每年腌酱豆子的场景,至今还清楚记得。
每回母亲都是从布袋中取出一些黄豆,放在簸箕里,两手抓住箕帮,一上一下地颠簸,很快便将里面的杂质簸了出去,坐在那里再把已有霉斑变质的坏豆挑出。就这样颠簸几次,六七斤干干净净的黄豆就被置入一个准备好的大瓦盆里。
黄豆非常坚硬,比较难煮,一定要在下锅煮前把它泡软。母亲簸好豆子,父亲便会从后街的井里打水,挑来倒进装有黄豆的盆里。说也奇怪,在里面仅有小半盆的黄豆,原本小小的粒儿,经过一晌的浸泡,居然粒粒圆滚滚的,胀得整个盆子都要放不下呢。
也许是因为害怕耽误时间抑或是怕我们多吃熟豆而不舍得吧,煮豆子一般都是选在晚饭后进行的。把泡好的豆子倒入大锅里,添上半桶水,便大火烧起来。烧火大部分都是父亲的事,因为这一烧也要好长时间的,而父亲是个很有耐心的人。
夜深了我们姐弟几个也不去睡,就是为了等着吃些熟黄豆。打开锅盖,一股热气便腾空而起,熟豆的鲜香直窜进鼻间,沁入肺腑。灶房里立刻蒸汽弥漫,烟雾缭绕,全身都暖暖的。母亲总是先给我们盛一碗,让我们端到屋里去吃。这时的豆子是极好吃,咬在嘴里香香的,甜甜的,面面的。
煮熟的豆子晾了一夜,水分已然少了许多,白天还要在太阳下晒一会儿,用手摸着有干了的感觉时便装进一个布袋里,用绳子紧紧地扎了口,将布袋深深地埋进麦秸堆里,也有埋在我们睡觉的地铺里的时候。五六天之后便会拿出来察看,如果布袋里的黄豆长了白毛,用手一扒有黏黏的细丝的时候就算焐成功了。如果没有白毛,表明温度太低,还需找一暖和点儿的地方再埋上几天。
焐好的豆子经过晾晒后,母亲就利用一个晚饭后的时间,把洗好的白萝卜用镲板镲起来。你会看到,一个胳膊样大的萝卜,瞬间一片一片跌落在镲板下的篮子里,白亮亮的,非常喜人。还要把镲好的萝卜片放在案板上,用刀把它们切成细条状,宽窄要适度,太窄腌时容易烂,太宽厚又难以入味。只有萝卜条是不行的,还要切上些白菜配合着才好吃。这样一忙活,常常要到夜里很晚的时候。为了家人能吃得可口些,从未听母亲说累过。
各项齐备,是混在一起腌制的时候了。取来一个大盆,铺一层萝卜、白菜条,撒上两把焐好的黄豆,再均匀地放入碾碎成面的盐和自制的五香粉。就这样一层一层直至大半盆时,用两手抄拌起来,豆、萝卜白菜条、盐和香料就均匀地混在一起,然后放进洗净晾干的大缸里。放满了缸,用力下摁后盖上盖子,只等发酵几天就好了。
常常在腌上的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吃起来。这时候的酱豆子还不好吃,盐与香料的滋味不能渗入菜和豆子里,萝卜尚保留着一股辣气,豆子也没泛开,有点儿霉的味道。等到十几天过后,缸里的萝卜条没有了辣气,变得软些了,而豆子也开始有了酱香的味道。早晨做饭的时候,盛上满满一碗,和馍一块儿放在箅子上熘熟,点上几滴香油,配上稠乎乎的玉米糁熬制的地瓜粥,那滋味真是一绝。有时一大碗都不够我们吃呢!如果放进油锅炒一炒,掺上鲜红的干辣椒就更好吃了。记得有一次,有位表叔有事路过我家,正赶饭点,家里没有别的菜,母亲便给他和父亲炒了一碗酱豆子,拿了一瓶老白干。那位表叔吃喝得极为开心,一直过了多年再提起时,他还直夸母亲腌的酱豆子好吃呢!
等到我们姐弟一个个都成家后,母亲依然保留着腌酱豆子的习惯,每次都要给我们几个分一些。后来,我们都劝她不要再腌,告诉她霉变的豆子对身体不好,她总振振有词地说:“我吃一辈子腌酱豆子了,也没见落下什么毛病!倒是你们,娇贵得很,不是这个疼,就是那个痒的。”
现在想想,那真是最天然的食材了,老祖宗传下的古法又哪里会有什么害处呢。反观今天这些五花八门的食品,却最让人放心不下。
可惜,再也吃不上母亲亲手腌的酱豆子了,可母亲对我们五姐弟的疼爱和关怀,会永远的留在我们心中。
酱豆子,永难忘!
【作者简介】:杜遂东,菏泽正高级中学语文教师,热爱文学,喜欢写作,作品散见于“学习强国”、《牡丹教育》、齐鲁壹点等网络平台和刊物。

葵邱书院投稿邮箱:kuiqiushuyuan@163.com
壹点号葵邱文学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