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羡林先生工作照
季羡林教授漫长而辉煌的学术生涯中,采用了多种理论方法,但是就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除了比较语言学等方法之外,恐怕主题学方法是其中最为值得重视的方法之一。这里,谨就目下所及,粗略地加以总结。
一、叙事母题的认知、研究可行性与操作
季羡林教授的研究实践,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研究的出发点,即,叙事文学母题跨国界的影响研究,在学理上要求实际上更加严格,不尚空谈,其若言之有理、自圆其说就离不开实证,实证性的操作步骤往往就要从细小的母题、意象着手,从而实践了他“小题大做”的一贯主张。
首先,是对于主题学研究方法之可行性的确信,早在1948年《“猫名”寓言的演变》中,季羡林教授就充满信心地说:
“我们研究比较文学,往往可以看出一个现象:故事传布愈广,时间愈长,演变也就愈大;但无论演变到什么程度,里面总留下点痕迹,让人们可以追踪它们的来源来。”
这一点,还表现在以具体的故事母题研究为例证,一次次地演示这一跨文化传播的文学史事实。
其次,是力图追寻特定故事的同源性、跨文体性,兼具本土性和世界文学的视野。根据确凿的材料,1946年在《一个故事的演变》中他肯定地指出“一个鸡蛋的家当”的故事:
“无论怎样,我们总可以看出来,印度就是这个故事的老家,正像别的类似故事的老家也多半在印度一样。……在印度本国这故事已经有了无数的演化。后来它又从印度出发几乎走遍了世界,譬如在《天方夜谭》里,在法国拉封丹的寓言里,在德国格林的童话里都可以找到,它一直深入民间,不仅只在文人学士的著作里留下痕迹。到了中国,他变成我们民间传说的一部分,文人学士也有记叙。”
较多地受到德国主题学研究的“同源性”理论的影响,季羡林教授较为偏爱同源性的实证研究,而这一实证的指向,即追索故事母题跨文化流传的最早源头,即是古代印度及周边地区。
因而,1947年,在《东方语言学的研究与现代中国》中,他从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中,分析了母题类型流传的四种可能:
一是各不相谋,二是由中至欧,三是由欧至中;四是从第三个地方来的,即印度,这最后的可能性最大,尽管还没有在印度发现。
这一观点后来还一再重申,如《〈列子〉与佛典》叙述机关木人的故事,他在1949年《“列子”与佛典》一文中,就找出了《列子》与《生经》故事的相似:
“我想无论谁也不会相信这两个故事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不但是从佛典里抄来的,而且来源正是竺法护译的《生经》。”
进而推究成书时间:既然《列子》抄袭了太康六年译出的《生经》,那么该书纂成不会早于太康六年(285年)。

季羡林 著
在跨文化进行母题时,也不是没有某些禁区所带来的困难、顾虑与困惑的。
如一些西方比较文学家的观点,就把“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这一点,往往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不承认在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间的文学比较也属于比较文学研究。
对此,季羡林教授曾敏锐地注意到可能带来的危害,并及时强调了比较文学中打破禁忌的问题。1986年北京大学举行“全国首届东方文学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时,他明确指出:
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学者,提出了一个说法:在一个国家中,不能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一种洋“塔布”。这洋塔布利害得很,它禁锢了我们同志们的心灵,不敢越雷池一步。
去年在深圳会议上就有人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明确答复说:这是一种洋塔布(taboo,禁忌),必须推翻。有这种主张的是欧美人。他们知道的“世界”只有欧美。在那里很少有多民族的国家,往往一国之中只有一种主要语言,
因此,要进行比较研究必须跨越国家。但是像中国,还有印度这样的国家,国内民族林立。
在历史上本来也有可能像欧洲那样分裂成众多的民族国家,可是由于某一些机缘,没有分裂,而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国。
在这样的国家中,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别不下于欧洲国与国之间的文学。因此,在中国和印度,民族文学之间是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比较研究的。
可见,对于形象学探讨中的一些历史上属于不同国家、而如今属在国内不同民族的那些“异国形象”,似也应作如是观。
这样,就给不少类似研究拓开了旧有的禁区,具有开一代风气的巨大作用。而且,在中印这样的国家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还有着在实践后进行进一步理论探讨的可能。
其三,始终不渝地关注具体文学母题、意象与套语的印度渊源研究。例如大耳的意象母题,1949年,季羡林教授没有局限在文学作品中,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里的印度传说》中,较早注意到三国到南北朝的史书中的人物描写“帝王贵相”母题,认为陈寿写刘备“大耳”,“长臂”,来自于公元初年译经故事。
佛经中有“臂长过膝”sthitãnavana tajãnupralam babãhuh,是奇人的标志,还有“大耳”(pinãyatakarnah),是圣人的标志。遍布中国各地的释伽牟尼塑像上都能看到这两个特征。这一观点也被国外汉学家如李福清等所认同吸收。
再像猫名寓言的演变,画师与木女故事,《西游记》中龙王形象、变形斗法等,以及《罗摩衍那》中诸故事母题的枯燥多种语言中的传播,皆是。
对相关古代中国的兔崇拜与兔预言,也并非没有古代印度文化蛛丝马迹的,1958年,《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中,季羡林教授曾敏锐地注意到兔的神话并不是国产:
“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梨俱吠陀》起,印度人就相信,月亮里面有兔子。梵文的词汇就可以透露其中的消息。……此外,印度神话寓言里面还有许多把兔子同月亮联系起来的故事,譬如巴利文《佛本生经》第316个故事。
在中译佛经里面,也有不少这样的故事,譬如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二一《兔王本生》;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六,《兔品》;竺法护译《生经》三一《兔王经》;宋绍德慧询等译《菩萨本生鬘论》六《兔王舍身供养梵志缘起》等等。
唐朝的和尚玄奘还在印度婆罗痆斯国(今贝拿勒斯)看到一个三兽窣(从穴中突然钻出来)堵波,是纪念兔王焚身供养天帝释的。”
一般认为,兔的智慧之文本表现,无疑也是民间故事及佛经中兔崇拜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对于六朝至唐代成书的史传、志怪和明清小说有关兔为祥瑞、逐兔带来主人公命运转折等相关表现,的确可以看成是有很大催奋力的。
时贤论述生命线与克星时,曾注意到:
“民俗学上所谓‘生命线’(the 1ine of 1ife)或‘生命点’(the point of 1ife),指特定个人某个秘密的、幻想的,生命、灵魂或mana所寄托的致命部位——它通常粘附着某种巫术,某种仪典以及这种巫术或仪典在语言层次上的再组织,表现为神话、传说或故事。”
而季羡林教授则更追溯了生命线母题源头之后的较早中介,《〈罗摩衍那〉在中国》中,他指出在古和阗文本有关《罗摩衍那》的故事里,十首魔王(Rovana)的“致命点”在右脚大拇趾上:
“十头王抱着悉多(sita),飞行空中。人们给他占相,知道他那致命的地方是在右脚大拇指上。
他们说:‘如果你是好汉的话,你就把右脚脚趾伸出来!’他伸了出来,罗摩用箭射中脚趾,十头王倒在地上,人们把他的脖子捆住,套上两条链子。他想往天上飞,又被打倒。”
季羡林教授指出,在梵文本《罗摩衍那》里十首魔王是只能被凡人杀死,“毗湿织因此化身为四,下凡降生,成为凡人,最后除魔”。而古和阗文本却创造性发展了它。
这样,就难能可贵地完善了这项研究,并且提示了中国叙事文学中类似描写的源头所在。


《罗摩衍那》
其四,对于主题学与形象学理论结合研究路径的探求。1987年,《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一文,揭示出在中古汉译佛经故事中,复仇主题相对集中于表现佛陀与提婆达多的宿怨今报故事。
提婆达多,汉语又译作地婆达兜、调达等,是阿难之兄,释迦牟尼堂弟。他追随佛陀出家,勤修十二载,得到佛陀赞扬,后在阿闍世王支持下,提出五法修行,与释迦牟尼分庭抗礼,成为印度佛教史上最早分裂教团的出家人。
缘此提婆达多为佛教僧侣们所深恶痛绝,同时,这也说明提婆达多的信徒还一直存在,并时有活动,甚至其信徒还有美化提婆达多的《法华经·提婆达多品》为其树碑立传,除晚出的少数大藏经典对提婆达多反佛事件有新解之外,大多佛经对提婆达多都痛加攻击,极言其毁佛害佛后,身陷地狱。于是在这一兴奋点的作用下,佛经故事套用因果律时很自然地将佛陀与提婆达多归为一对宿世怨家。
本生故事多言佛陀前世如何无意得罪提婆达多,还是结了怨,此为俗套,这其实就是关注到了该形象并非反映了该人物的真实历史面貌,而不过其对立力量有特定目的动机而造出来的扭曲了的形象,是一种“意识形态形象”。
在这一角度上,西方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认为:
“形象就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种描述,制造了(或赞同,宣传)这个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显示或表达他们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
……毫无疑义,异国形象事实上同样能够说出对本土文化(审视者文化)有时难于感受、表述、想像到的某些东西。因而异国形象(被审视者文化)就能将未被明确说出、定义的,因而也就隶属于‘意识形态’的各个‘国别’的现实,置换为一种隐喻的形式。”
此外这项研究大体说来,也接近主题学理论中的“人物母题”,即以某一定型化、类型化的人物作为一种叙事母题;而析言之,则是一种类型,其包孕的内容实大于母题。
早年,胡适先生受他所称呼的“母题研究法”的启发,曾概括出古代小说中如包公等形象为“箭垛人物”,就指的是这一类母题。
因而,季先生在这一学术背景上,又以具有固定模式及内蕴的“提婆达多母题”做为前提,试图开掘出生成这一母题(箭垛人物)的历史――宗教史成因,不能不说其具有超出论题本身的巨大启发意义。

王 立 著
二、对于叙事母题跨文化传播多种中介的关注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季羡林教授总是不局限在就事论事上。1947年他在介绍亚洲多种文化包括伊兰(伊斯兰)系文化对于中国影响时,就指出:
“到了汉魏六朝,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开始传播到中国来。居间介绍的也多半是伊兰民族;因为据我们现在研究的结果,在初期有许多佛经不是直接从梵文译出来的,而是经过中亚诸小国的媒介,这些小国多半是伊兰系的民族。
这我们只要一看最初到中国来的和尚的名字就可以知道。凡是姓安的都是安息人,凡是姓康的都是康居人。真正直接从印度来的很少。……”
不仅如此,对于阿拉伯文学传入中国的中原地区,他也是取这种观点:“阿拉伯国家的民间文学通过伊斯兰教和旅行家在南方首先传入泉州等地,在西方传入新疆地区,然后再向内地扩散。”
由此,先生特别关注在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故事中进行影响研究:
“印度著名的大史诗《罗摩衍那》,全文没有传到汉族地区,只在佛典的译文中有所反映,然而它的影响是非常清楚的。
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中,相当完整的罗摩的故事可以找到很多个,在新疆古代语言中有罗摩的故事,在蒙古、在南方的泉州,还有其他一些地方,都有与罗摩故事有关的故事。”
此外,有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在中印文化交流的中介地带――新疆地区文学遗存上展开的,如《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一文,该文还从历史地理学上对于陆上的路线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承载异质文化的传播媒介是三种人:
“古时候,走丝绸之路的人不外三种:一是朝廷使节,二是宗教僧侣,三是负贩商人。我们可能会认为商人只不过是为了赚钱,原来也有风雅商人。”
中介本身可以分为时间、空间、媒介等不同的、多维多重的层次。其实,中古汉译佛经就是联结中外文学母题、中外文化的中介之一。
研究文学、文化交流不可能绕开佛经文献。然而,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陆的佛教与小说关系研究基本上停顿了。
因此,就严格意义上的佛经文献运用来说,季羡林教授在1984年发表的《商人与佛教》一文中,就强调指出:“还没有见到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的文章”,为此他“提倡一种利用佛典律藏的风气。”
然而,在提倡的同时,他没有忘记佛经传译历史过程的特殊性和时代背景,以期在运用佛经文献时更加符合科学性,并且以旁证的材料来进行必要的论证和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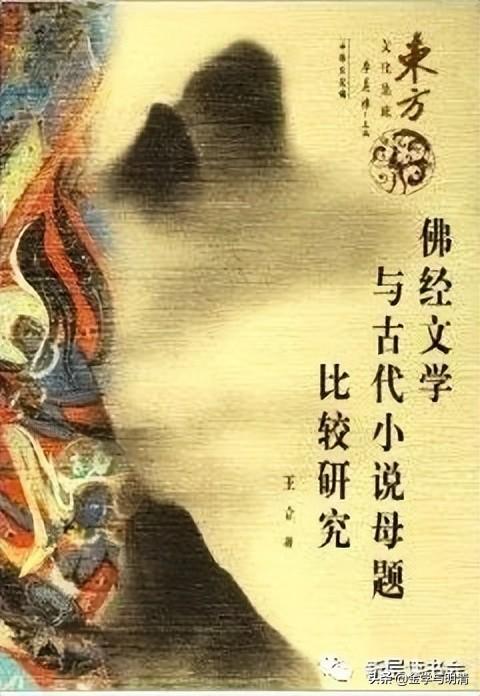
王 立 著
季羡林教授还注意到佛教初入中土时,为了站住脚根也运用了不少中介手段。
例如1980年,在《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文中,他指出幻术就是佛教初入中土时的一种生存手段:
“为了求得生存,初期的译经大师,如安世高、康僧会之流,都乞灵于咒法神通之力,以求得震动人主和人民的视听。一直到晋代的佛图澄(公元310年至洛阳)还借此为弘教手段。
不管这些和尚自己是否相信这一套神通咒法,反正他们不能不这样做。《梁高僧传》卷9《佛图澄传》中多次提到佛图澄的神异,说得活龙活现,神乎其神。‘(石勒)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证。
因而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大50,383c)从这一个小例子中可见一斑。”
对于这些幻术的描述,实际上就生成与丰富了诸如“种植速长”、“一以化多”、“遥测远事”等母题,而诸多幻术的造幻方式为中土人们所借鉴,其效验和功能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也不能不通过佛教本身的传播以及道教等民间秘密宗教,使下层民众广受濡染、仿效,于是就不能仅仅注意佛经本身,还要留心传译中的“有意误读”、汉译佛经生成和早期接受过程中,有关史实与文学母题的联系。
广袤的西域地区,或具体到新疆,是南亚故事、习俗文化等由梵入华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季羡林教授1981年就特意撰写了《新疆与比较文学研究》一文,他以吐火罗文译本的机关木女故事以小见大,认为其“正代表从梵文佛经到中国小说间的一个过桥”,“说明新疆这个地区实在很富于比较文学的材料”。
他还根据英国学者H.W.贝利对古和田文残卷研究,介绍了《罗摩衍那》以古和田语流传的故事,那护沙的儿子为国王,能通解禽兽语。
一次他在花园听到两个蚂蚁说话而发笑,王后追问他笑的原因,但他想到透露秘密就死的诅咒,不敢说。他还听到母驴怂恿公驴抢骡子的饲料,母山羊怂恿公山羊到驴背上抢草吃,公羊不愿去,说:“我不是那护沙的儿子,他为了女人的缘故想丢掉自己的性命。”
季羡林教授指出,巴利文本生经第386个故事也有懂禽兽语事,《高僧传》卷一《安清传》:“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述。”
可见人懂禽兽语,就属于那种中国本土早有,佛教传入之后类似的观念和叙事又强化了旧有母题的那一种母题,而这一“中转站”的材料描述在研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论》
三、寻究母题发生、建构及传播的深层原因
文学母题的生成,离不开某一历史时期流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在其或显或隐的制约下,人们遂对于某一母题产生了趋同心理及创作现象。
季羡林教授在探讨某一母题的成因时,往往不是“一元化”的,而是注意多元化地思考,并且突出重点,力图揭示其背后的佛教文化成因。
他关注佛经传译的特定历史阶段中,中土人们的“有意误读”现象,从而在接受改造的环节上寻究原因。
如1949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里的印度传说》中,有关正史描述帝王贵相本于印度的母题,他就正确指出:
“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正是佛教势力很大的时候。中国的统治者为了增加自己的身份,企图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神秘莫测的印象,好使他们驯服地匍匐在自己脚下,于是就把西天老佛爷某一些传说的生理现象拉来加到自己身上。
……南北朝以后的史书里,这种情况就绝了迹。原因并不是统治者不再企图把自己神秘化,而是佛教的势力在民间已经没有那样大。再耍这一套手法,观众就不大感兴趣,只好另想别的办法了。”
又如对金银变化母题中某些内在要素成因,1980年,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他指出:
“总起来,我们可以说,僧尼亲自用手拿金子和银子,算是一种不大不小的罪过。为什么禁止和尚和尼姑拿金银呢?我想,原因并不复杂,无非是想让他们丢掉对尘世的依恋。
在这一方面,佛典律中有许多规定,规定僧尼不许有私有财产,规定他们只能占有最少量的生活和宗教行持的必需品:身上穿的袈裟、手里拿的乞食用的钵、脚上穿的鞋、剃头用的剃刀、为了防止饮水时把虫子(生物)喝到肚子里去而用来漉水的漏子等等,超过这一些是绝对不允许的。
金银自古以来就是财富的象征,僧尼不但不允许占有,连拿一拿、摸一摸也算是罪过。这就是僧尼不许捉金银这一条戒律产生的根源。佛教在督促僧尼抛弃俗物,潜心静修,誓期涅槃,跳出轮回方面,防微杜渐,煞费苦心。
《后汉书》卷六十下记载襄楷于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上书桓帝说:‘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连在一个地方睡上三宿都不行,生怕他们产生了恋恋难舍之心,金子和银子如何敢让他们捉拿触摩呢?”
1983年,在《印度古代砂糖的制造和使用》中,季羡林教授还特意指出巴利文《本生经》实际上是一部民间故事集;并概括出其故事类型模式的佛经文学成因:
“佛教徒,同印度其他教派的信徒一样,为了更有效地宣传教义,把这些民间故事按照固定、死板的模式,加以改造。只需加上一头、一尾,任何民间故事都可以都可以改成一个佛本生故事。”
这实际上揭示出佛本生故事的母题化,事实上就是把民间故事以佛之前生因、今生果的特定模式固定化了,其中的内容(民间故事鲜活材料)可以灵活性地填充,而主题自身则稳态化定型化了。
季羡林教授对于中国传统小说套语的成因,也曾寻究其与印度文学的某种共同性,予以深刻的揭示:
“……在中国旧日的白话小说里,一碰到描写风景和人物,就容易出用四六句子。在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形。在像《五卷书》这样的散文著作里,一碰到描写风景和人物,也就出现这种宫廷诗体。
这种类似的情形并不是偶然的。在中国的赋和印度的宫廷诗里,有大量的描写风景和人物的现成的句子,借用这些已被成了老套的现成的句子是轻而易举的。于是作家们也就乐得去借用了。”
的确,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是展卷即见地常常有这类描写的韵文,几乎成了小说景物、人物之类描写的不可或缺的套语。
其实,有不少韵文套语,根本就与小说故事本身的情节无关。但偏偏小说家就是爱借用,而且读者(听众)也乐此不疲。
季羡林教授却没有局限在国别文学中,匆促地进行审美价值判断,而是把视野放开,说明印度文学实际上也不例外,从而启发人们思考这是否为东方民族的共性现象,乃至共同的成因,类似的利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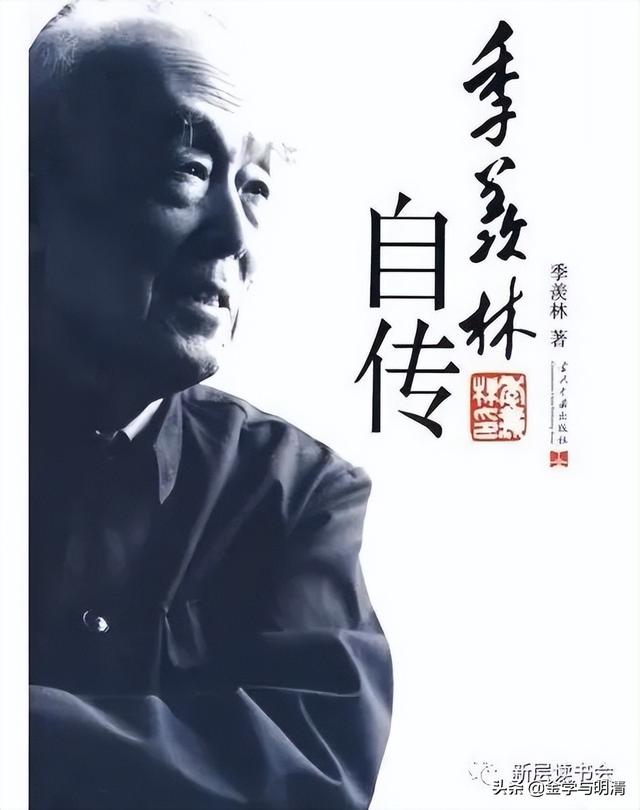
《季羡林自传》
四、主题学方法形成、成功运用的成因
季羡林教授能在研究实践中,形成并成功运用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通晓多种语言的基本条件外,还存在了其他一些主观上的原因。
首先,是学术道路之于学养的积累、视野的拓开。德国,是主题学理论诞生的故乡,季羡林教授在德国攻读多年,受到相关的学术熏陶是很自然的,这从他对于德国学者、学术的熟悉,可见一斑。
其次,是执着的“问题意识”和生活体验的结合。强烈执着的问题意识,是以主题学思路持续思考观察的不懈动力,1988年,先生《季羡林自传》,有这样的夫子自道:
“只要你脑海里有某一个问题,一切资料,书本的、考古发掘的、社会调查的等等,都能对你有用。……最好脑海里思考问题,不要单打一,同时要思考几个,而且要念念不忘,永远不让自己的脑子停摆,永远在思考着什么。这样一来,你搜集面就会大得多,漏网之鱼也就少得多。”
如关于佛经中提婆达多形象问题,也体现了对于某一问题思考的持久与执着,1998年,在《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新增内容说明》中,先生谈到:
“我初读佛传时,并没有什么怀疑。但积之既久,便产生了疑虑:难道提婆达多真能这样坏吗?‘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中国先贤已经说过了,我打一个可能是不伦不类的比喻。
十年浩劫中,常有把一些人,主要是知识分子,‘打’成反革命的例子。提婆达多也是被释迦牟尼的忠实信徒‘打’成十恶不赦的恶人的。我于是就开始精心收集资料,写成了这一篇论文。”
敏锐地发现了佛经中的提婆达多,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上讲的“意识形态形象”,其实在历史上并非真的是像被描述的那样可恶:
“在佛经中他被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威望很高的人。他有自己的戒律,有自己的教义,有群众。他同释迦牟尼的矛盾决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佛教史上是重大事件。”
于是1998年,在《再谈浮屠与佛·新增内容说明》中,他将梵文与巴利文的相关载录排列出来,指出其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唯一区别是,梵文是阿难,巴利文是舍利佛。
而在中古汉译佛经中,有几句重要的话,却被删掉了,即:“大德,从前我曾赞叹过提婆达多的品质,说,提婆达多是善良的、英俊的、有德的,现在人们将会讥笑我前后矛盾。”……
那么,如果我们从主题学的角度看,这实际上就是某一特定的叙事文本多种异文之间的比较。这一爱好和良好习惯,来自于对于学术研究不能指望一次性达到理想目标的理性认识:
“这也许是我的一种好习惯:在学术上,我平生想探讨的新问题,为数颇多。我探讨了一个之后,决不丢开,而是仍然记在脑中,作进一步的探讨。没有哪一个比较重大的学术问题,是一蹴而就,一下子就能解决彻底的,就能毕其功于一役的。”
其三,另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季羡林教授对故事究属原创还是传播复制这一问题追索的执着。
1947年,《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中,他就找出了《黔之驴》故事的来源及其在古希腊、法国的同类型故事,并指出:
“它原来一定是产生在一个地方,由这地方传播开来,终于几乎传遍了全世界。……柳宗元或者是在什么书里看到这故事,或者采自民间传说。无论如何,这故事不是他自己创造的。”
其四,是强烈的学术创新意识和学术规范的讲求。
学术研究的创新之路与方法,事实上与严格的学术规范、严谨的学风是密切联系的。
如许多文章的结尾,都提到该文写成后送给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帮助和指正,得到了材料和观点上的修正,以示“志谢”,这种严谨的学风、实实在在的认真态度,也是令人钦敬和学习的。
这些学者有汤用彤先生、向达先生、周燕孙(周祖谟)先生、王利器先生,等等。
这与季羡林教授专门撰文回忆自己的老师吴宓先生等,出发点是一致的,值得推重,联想起如今有的博硕学位论文撰写者,那些不遵守学术规范的做法,更显得弥足珍贵和令人感慨。

季羡林 著
文章作者单位:大连大学
本文获作者授权刊发,原文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收入王邦维主编:《季羡林先生与北京大学东方学》,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2011年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