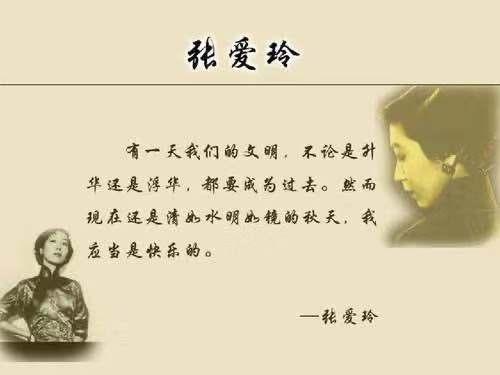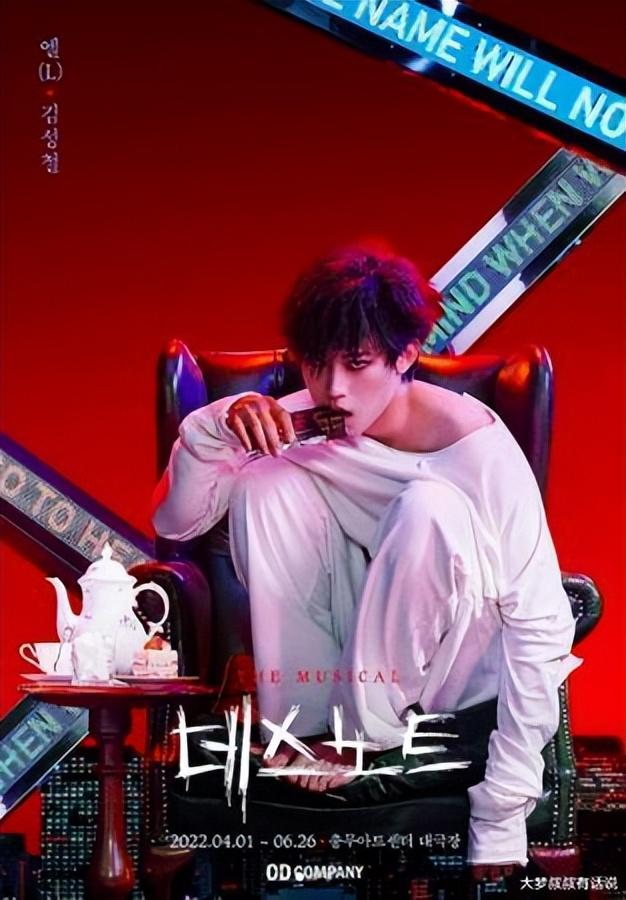门铃响了。一男一女两位客人被请进饭厅。
我闻声来到饭厅。立即楞住了,面前的人是谁?!难道是四哥?我盯着他仔细辨认。是他!两道浓眉,两只大眼晴。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可又不太像他。那神采奕奕的眼神,那焕发青春活力的气息,那爽朗的笑声,那英武的气质。多少年前早就消失了呀?难道又相见在当年的科班里?
我在记忆中搜索。只有在科班里,盛麟オ有这样的朝气,那时我俩都只有十五六岁……
有一天,在佛殿上喊嗓子,盛麟喊:“马来一一出了一股难得的高音亮音。我听见了非常高兴,马上走过去对他说:“您一定要把这个音看住了,您这个大武生就算是立住了。”
盛麟也非常高兴。正是有了这副好嗓子。再配上他的好武功,才终于成为一名与余不同的大武生。当时王连平师兄给我们排了架子花脸与武生并重的戏《高唐州》《北侠传》《独木关》《辞礼征东》《凤凰山》等。这一年,我和四哥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放年假,我到他家去玩,听了许多珍贵的京剧老唱片,跟着学唱,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在科班练毯子功排队遛虎跳、走小翻时二人常聊天,最热门的话题是出科后如何组班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时,盛麟才有这样的精气神儿……
“老三!傻愣着干什么?这么快就把我忘啦!老三!”
这声音明确地告诉我,就是他,就是四哥高盛麟!我立刻嘴里大声喊着:“哎哟,四哥四嫂,哪儿还敢认您!”就像当年一样,高兴地双脚跳起向他扑去紧紧拥抱在一起!
“三十多岁的人啦,还跟当年孩子似的!”
“刚才、看报纸オ知道您和高百岁到北京演出来了,我准备晚上到后台去看您,也看看您的戏。没想到您先我一步,到家来看我啦!”
这次我能到北京来真想看看咱们这些师兄弟们,我还得到叶三哥家看看师娘,到萧(长华)先生家、裘仔(盛戎)家去。就在北京待几天,时间安排挺满。我离开北京七八年了,真没想到我还能杀回来。”
母亲进来了,看着盛麟,没认出来:“你是?”
盛麟亲切地叫:“娘,我是专爱吃您送雪里蕻炒豆腐的那个呀!”
母亲说:“哎哟!是他高四哥!有年头没见着,出息的多英俊呀!你不是一直在上海吗?什么时候到北平……京来啦?”
高盛麟说:“昨晚上刚到。”
“您等着我给您拿烟去!”我说着往外跑,被福媛拦住:“已经买去了。”
四嫂也站起身来拦住:“三兄弟,甭张罗!你们家没烟!我还不知道?”“我这儿有。”又对我说:“你不抽烟,我也不让你了。今天你看你四哥也像个人儿了吧。”
“都解放了,四哥还……四哥还不就变成了我原来的四哥啦!”
“没错!要不是解放,我还能有人样儿?再晚解放几个月,我就是和你在梦里相见的鬼魂啦!哈哈哈!”
盛麟声声爽朗的笑声震撼着我的心!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年在上海遇到盛师兄的情景…
自一九四四年我从上海回北平与盛麟分手,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初随程砚秋先生到上海演出,才与盛麟见上一面。
那天的演出,前面是盛麟的《铁笼山》,后面是我的《清风寨》,大轴子是程先生的《金锁记》。
在后台,盛师兄凡人不理,直走到衣箱,闭眼盘腿坐在上面。我见到久违的盛麟,马上热情地上前去跟他打招呼,没想到他却眼皮没睁,头也没抬地只是哼了一声。
这一下,我倒被木在那儿了,不知所措。
管事李小龙来了:“高老板!”
盛麟哼也没哼一声。
“高老板,您扮戏吧,该着啦!”李管事又催道。
盛麟还是没哼。李管事见他不理,向我摊了摊双手,转身走了。
我非常不解地上前问他:“您是不是病啦?哪儿不好受,我给您买点儿药。”他只摇了头还是没理我。
正在这时,鼓老(打鼓的)来了,冲着盛麟:“咱们对对戏吧!”
他摆了摆手说:“台上见吧。”
另一位管事韩金奎来了,拍了拍盛麟的肩膀说:“高老板,时候不早了,真该扮了。”
盛麟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这一眼看得,让我浑身打了个冷战,这哪里是师兄高盛麟哪!整个人似被抽掉了筋骨,满面枯瘦焦黄,双目冷漠无神。
盛麟转脸对韩管事说:“什么都没有,我扮什么!”
韩管事似乎全明白了,忙说:“噢,噢,我给您……我给您拿去。”
不一会儿,韩管事拿来一条彩裤、两双靴子。
盛麟把彩裤套在棉裤外边,拿起一只靴子,脚一瞪,噗地就进去了,太大。又试另一双,根本穿不进去。
“穿我的靴子吧,咱俩的脚差不多大。”我赶忙去取来一双靴子,送到他的面前。
“袁老板,您也赶快扮戏吧,这儿有我呢。”韩管事看了看表对我说。
“还缺什么从我这儿拿。”知道韩管事是催我扮戏,说完,只得去勾脸。我勾好脸谱,《铁笼山》已经演了一半。站在侧幕一看,只见盛麟勾的姜维脸谱没用红色,用了紫红色。我立刻意识到他肯定没有自己的彩匣子,用的是官中彩匣子,官中彩匣子一般都没有红色。头上戴的是旧扎巾,身穿短了半截的黑蟒,打八将时用的是开门刀(应用八卦刀),这全是官中的。脚上穿着我的靴子,鞋和脚拧着,显然仍是大,不跟脚。看到这,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舞台上,盛麟师兄正一招一式演出,虽然穿着棉裤,蹬着不合脚的靴子,手中使着通常龙套举着的又沉又笨的开门刀,竟然把这出最吃功的武生重头戏稳稳当当地唱下来了。你看他叫锣鼓点儿有多清楚,脚底下拖着大鞋转身、翻身有多溜,对打时脚底下就没有废步,你看他那开门刀舞得有多好!真是衣服虽破戏不破!我站在幕边上被他的精湛表演所吸引,又对他那扎实的基本功佩服得五体投地。
想当年,盛麟师兄出科时(比我早一年),凭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跟随其父高庆奎的班社,到各地演出。常常在高老先生戏的前面给他加演一出武生戏,得到了很多锻炼的机会。他第一次到上海虽未被观众注意,但开阔了他的眼界,学了很多周信芳、盖叫天先生的表演。
盛麟在科时喜欢杨派,回京后如愿地拜了丁永利先生为师,学了多出杨派戏。李万春、李少春、刘宗杨、孙毓堃、王金璐均是丁永利先生教出的学生。
随后他又有幸娶了京剧武生泰斗杨小楼先生唯一的外孙女刘惠芬,成了杨老先生十分钟爱的外孙女婿,深受杨老先生的教益,深得其精髓。
后来,同裘盛戎、毛世来组班到上海,一炮而红。头一出《武松杀嫂》,在武松打时,他运用了很多盖(叫天)五爷的身段,打虎后探兄,唱了一段高昂响亮的【二黄摇板】,冲冲的武生嗓,一下就把观众给吸引住了。后一出《连环套》演黄天霸,又亮嗓子又亮气势,让上海观众为之振。仅几天就唱红了大上海,承认了这位京派大武生。再后来,盛麟师兄染上了鸦片瘾,沦落到这般地步。
第二天,我将绿靠、黪满和唱武戏用的薄厚底靴,都拿给了盛麟用,还时不时地“借”给他二三百元钱。
此后,我也曾到盛麟师兄上海的住家看望过他,其家更是惨不忍睹。一间阴暗潮湿的房子,屋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床,床上就一张床单。他围着烟灯躺着,后续夫人邹畹华陪伴着他。此情此最,令我不寒而栗!令我为为之痛心!盛麟师兄才三十将过,在这苦海里何时才能熬出头……
“老三,你怎么净傻瞧着我不说话呀?”盛麟师兄不解地望着我,拍着我的肩说。
“让您给蒙住了!为您高兴!您居然把烟戒了,整个换了一个人,杀回北京了,春风得意地杀回来了!”
“离开北京八九年了,真是没想到我还能脱胎换骨地杀回来,想当年我们老爷子去世我都没办法回来。我有时也怀疑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我想不出您是怎么从那个…无底洞里逃出来的?”
四嫂接过话茬儿:“三兄弟问得好!还记得在上海你去看你四哥,劝他戒烟……”
“他给我轰出来了!太记得!”
“不能不轰你!”
“为什么轰我?”
盛麟收住笑容,吸了一口烟吐出来:“你劝我戒烟,你不懂!那玩意儿让我走投无路,我恨透它了!可离了它受不了!戒又谈何容易?我们俩戒烟费用大得吓人!我还欠着一屁股的债,靠你?兄弟,你无能为力!当时有一个大富豪爱看我的戏,他想出钱给我戒烟,就不肯出双份让你四嫂也戒!非让我跟你四嫂分手!我能把她扔下?你李家四嫂(盛麟前妻)过世,多亏你这个四嫂照顾我。你去看我的时候,我心全死了!抱定了活一天算一天。哪能让你陪着我们着急!不淡着你,成?不轰你,成?”
“三兄弟,我和你四哥都谢谢你不断地接济……”
“我和四哥是发小,不谈这个,快说说,究竟是什么高招脱离虎口?”
“高招就是解放!遇到的真人就是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咱们分手后,我更是苦不堪言,好容易熬到上海解放。上海戏院全停演,经理们都望风而逃,眼着我无路可走。武汉中南京剧工作团到上海演出《三打祝家庄》,团长亲自上门来看我,约我参加这个团,我就应了三牌武生。过了几天,武汉市派了几个干部来跟我谈,说是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替我还清以前的烂账,赎回行头,出钱给我戒烟!我就到了武汉。没想到武汉特吃我的红生戏,我就这样在武汉待住了。”
“太好啦!解放前旧社会把我这么好的师兄变成烟鬼!解放了,共产党、新中国把大烟鬼变回我的好师兄!”我说。
四嫂接过话茬儿:“还得说靠大伙儿!三兄弟,你想象不出来我们戒烟受了多大罪呢!我没本事,再难熬也得熬。你四哥可好,他挺不住了,就在屋子里咣咣一个接一个摔踝子!大伙儿一见他这样,心痛得跟什么似的,昼夜排班帮着给他捶腰捶腿。等我们好受点儿,送鸡送肉,总算都挺过来了。瞧,这百家饭把他养得多壮实!我也是!辅导员说这是团结友爱,是……阶级友爱!”
现在我们团改为武汉市京剧团,我和百岁是来北京蹚蹚路的。”
盛麟师兄的这番话使我激动不已。新中国、新社会就是好,它使多少烟鬼脱离了苦海!
晚饭后。我陪盛麟师兄到剧场,看他们演出的《英雄义》。盛麟的功架、唱、念等表演。集高、周、盖、杨艺术特色于一身。他的地蹦、踝子高、漂、帅,看着真解气。观众的叫好声此起彼伏。一下就轰动了北京城。
由此引出来一九六二年,盛麟兄与张君秋走马換将,演出后受到周总理亲自接见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梨园佳话。
八月间,新中国实验剧团去大连、哈尔滨、沈阳等地演出。
我们在哈尔滨的演出,格外受观众欢迎。哈尔滨的剧场很破旧,没有座位。就是两头擦砖中间用本板搭上,观众也不对号入座。为了占个好座,很多人家派代表带着两顿饭,早上八点就到场占座位,吃两顿冷饭,直到晚上七点才开始看戏。
观众付出多大的辛苦,又陪上多少时间哪!等到开戏时满剧场人挨人,密密麻麻,热气腾腾。东北观众对《野猪林》《将相和》等戏的欢迎度,更让全团人员深受感动,甚至会有自我膨胀感。
八月十七日,我们新中国实验剧团与淞江省实验京剧团,在哈尔滨市淞江剧场联合举行捐机义演《刘关张生死桃园》,参演者有当地的演员曹艺斌、高亚樵等。除必要开支外,所有收入都当即送交淞江省抗美援朝分会。
这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到沈阳演出,无论是各级首长,还是观众,都犹如久别的老朋友,相见格外亲切。演出期间,东北文化部秘书长罗烽同志不仅热情款待。而且正式提出要组织东北京剧院,欢迎新中国实验剧团全团参加,允许编制不变,经济分配也像現在一样可以单独核算,排戏、管理仍可自定,演出还可半年在关外,半年在关里。
对于这个方案,我认为条件如此宽松,可以考虑,但少春始终没表示同意与否。我感到少春年龄比我小,处世却比我沉得住气,大家多考虑考虑也好。好在新中国实验剧团组建十七个月来,大家团结互助,排了五出新的大戏,而且演出效益好,没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没必要把团改来改去的。只是面对东北各位领导的盛情有点儿不好意思而已。
在沈阳,大家看了东北戏曲学校的演出,看了刘琪演的《扈家庄》。刘琪当时也就十几岁,长得圆乎乎的像个小肉滚,但她小小年纪,手、眼、身、法、步就如此和谐,舞蹈动作如此敏捷,足可以看出这员小将会大有前途。
还看了《将相和》,饰演廉颇的学生叫王平,演得不错。我对饰演秦王的一个小个子花脸也情有独钟,他虽是演次要角色,但他在台上很认真,很有灵气,我看准了他是块架子花脸的材料,他就是李嘉林。
我和他们俩还有徒弟范成玉合照了一张相,一直保留至今,十分难得。
不久,新中国实验剧团接到了北京来的电报:要新中国实验剧团九月底返京,落款是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马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