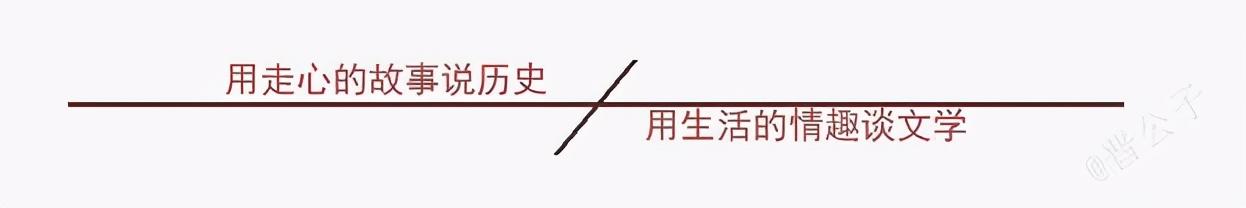

本期话题
《采蘩》和《采蘋》两首诗都出自《诗经·召南》。它们不但有着相似的题目,甚至还有大量雷同的句式和表达。但是说起这两首诗讲述的故事和情景却是截然不同的。究竟这两首美妙的诗歌各自说的是什么呢?
上期文章:
文学创作经验谈:为何古往今来的大作家都视这样东西为文字的生命

《诗经·召南》中有这么两首长得很像的歌诗。其一曰: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
——《诗·召南·采蘩》
其二曰:
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
——《诗·召南·采蘋》
《采蘩》和《采蘋》就像一对孪生兄弟。表面看来,相貌难分甲乙;骨子里却暗含着截然不同的志趣。
我说的这个“难分甲乙”是一目了然的:它们不但有着相似的题目,甚至还大量使用雷同的句式;至于说各有志趣,可就不那么好分辨了。
如果体会不出两首诗在语气、口吻上的微妙差异,这点儿区别是不容易看真的。

说话的语气和口吻,首先取决于主人翁的身份。《采蘩》这首诗的主人翁是什么人呢?潘啸龙先生曾撰文分析说:
《周礼·春官·宗伯》称:“世妇,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贾公彦疏谓“女宫”乃指有罪“从坐”、“没入县官”而供“役使”之女,又称“刑女”。凡宫中祭祀涉及的“濯摡及粢盛之爨”,均由“女宫”担任。
而此诗中的主人公,既称“夙夜在公”,又直指其所忙碌的地方为“公侯之宫”,则其口吻显示的身份,自是供“役使”的“女宫”之类无疑。
——《先秦诗鉴赏辞典》
据潘先生的分析,这首诗描写的是一群卑贱的诸侯宫女,她们辛苦采蘩以供祭祀之用。诗的前两章之所以一问一答紧密地连缀,用意正是模拟她们准备祭祀的紧张情景:
“到哪儿采蘩啊?”
“于沼于沚。”
“做什么用啊?”
“公侯之事”……
没有一句多余的描写,只有极简短的一问一答。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宫女们都在脚不沾地地各自忙碌。有人在一路小跑的时候听到同伴的问话,遂扭过头来匆匆忙忙地应她几个字。这样的问答此起彼伏,宫里宫外的忙碌场面不言自明。
可问题是,一问一答的行文为什么只持续了两章,就戛然而止,第三章换做了陈述的语气呢?潘先生继续解释说:
诗中妙在不作铺陈,只从她们发饰“僮僮”(光洁)向“祁祁”(松散)的变化上着墨,便入木三分地画下了女宫人劳累操作而无暇自顾的情状。
那曳着松散的发辫行走在回家路上的女宫人,此刻究竟带有几分庆幸、几分辛酸,似乎已不必再加细辨——“薄言还归”的结句,不已化作长长的喟叹之声,对此作了无言的回答?
——《先秦诗鉴赏辞典》

坦率地说,上述解释我没法儿接受。
将“被之祁祁”训为发辫松散,依据该是来自《毛传》。《毛传》说:“祁,舒迟也”——多说一句闲话,《毛传》的“舒迟”究竟是指向仪态的从容还是发辫的松散,其实还有讨论的余地呢——但无论如何,《毛传》的这个解释缺乏训诂学上的坚实依据。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说:
祁的本义是地名,用作三个不同的词的假借字——“大”、“多”、“舒缓”——是不大可能的。在“其祁孔有”和“冬祁寒”里,祁作“大”讲没有疑义。“多”和“大”意义相关,可以同是一个词根。
至于“舒缓”,除去《毛传》解释“被之祁祁”、“兴雨祁祁”、“祁祁如云”,就没有什么依据了。可是我们已经说过,“被之祁祁”是讲作“大”好。
至于“兴雨祁祁”和“祁祁如云”,如依照“采蘩祁祁”和“来假祁祁”的《毛传》讲作“多”,就更好一点。如此,“祁”所代表的只有一个词了,他的意义是“多,大”。
——《高本汉诗经注释》
从“被之僮僮”到“被之祁祁”,诗人绝不是在形容与祭女子从妆容严整到发辫松散,而是盛装出席,贯彻始终,“祁祁”正是妆容盛大之意。

“发辫松散”不但在训诂上站不住脚,也不符合先秦时期人们对这首诗的主旨的普遍理解。《左传·隐公三年》写道: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左传·隐公三年》

《左传》的作者说,《采蘩》这首诗昭示了祭祀的基本精神,那就是一定要根植于忠信。换句话说,祭品的贵重与否、祭仪的繁复与否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参与祭祀的人能否始终保持发自内心的敬畏和庄重。
设想,与祭的女士们在祭祀结束的时候已然发辫松散,衣冠不整,那这敬畏与庄重又从何说起呢?
据我个人的拙见,潘先生对这首诗的理解恐怕是受到了高亨《诗经今注》的某些影响——那部撰写于“革命年代”的注本每每想在《诗经》中挖掘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可事实是“被之祁祁”的主语根本就不是卑贱的宫女,却是高贵的公侯夫人。
竹添光鸿《毛诗会笺》说:
副者,后夫人之首饰,编发为之。彼《传》以副为首饰,则被与副同物。被取被覆之义,与副之训覆义近。《葛覃传》云“妇人有副袆盛饰,接见于宗庙”。此诗言公侯夫人助祭宗庙,首饰必用副,则被之为副可证也。
——《毛诗会笺》
竹添光鸿考证说,“被之祁祁”中的“被”绝不是寻常发辫,而是象征着贵族身份的专属装饰,宫女根本没有资格使用。这足以说明《采蘩》第三章描写的主角究竟是谁。
而一旦我们将第三章的主人翁锁定为助祭宗庙的公侯夫人,这一章不再使用问答而必须转入陈述的原因也就清楚了:
准备祭祀的过程是紧张而忙碌的,自不妨以连续不断的问答来加以暗示;可祭祀一旦正式开始,每一个祭仪的环节都需要参与其中的贵族秉持最虔诚、最恭敬的真心来认真完成,它可万万操切不得!
自问答转入陈述,诗人的叙述节奏因祭祀的开启而更趋沉稳。至于其中的主角即公侯夫人,那可是自始至终仪态端方,没有半点虚懈。
《左传》所谓“昭忠信”,仅在她的妆容严整、贯彻始终这一点上便显露无疑。

这么一说的话,新的问题就又出现了:《采蘩》三章,用了两章问答和一章陈述,目的是要刻画从准备祭祀的忙碌到举行祭祀的恭敬的全部过程。那《采蘋》为何不如法炮制?它为什么一问一答,贯通三章呢?
这其实是因为《采蘋》描写的祭祀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礼仪活动。《毛诗会笺》曰:
《(礼记)昏义》言:“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牲用鱼,芼之以苹藻”,其事与《采蘋》之诗正合。
然则采蘋者,大夫妻将嫁,教成而祭于宗子之庙,以鱼为羹,而芼之以苹藻为铏羹,奠于牖下。此祭宗子不主,而季女主之,故曰“谁其尸之,有齐季女。”非大夫妻奉祭祀也。季女者,未嫁之称。言尸之,则非助祭也。
——《毛诗会笺》
根据周代的礼俗,贵族女子在出嫁前必须预先在娘家学习主持祭祀的相关礼仪,以备将来作主妇所用。《采蘋》中的这位女子正在自家的宗庙里完成这堂人生的必修课。因为缺乏经验,手忙脚乱,所以她忙不迭地连声询问:
“到哪儿采蘋啊?”
“到哪儿采藻啊?”
“用什么来装啊?”
“用什么来煮啊?”
“祭台摆哪儿啊”
……
在一旁为她做指导的人看着这位少不经事的姑娘那副笨手笨脚的模样,忍不住就要打趣她:
“这是哪家的女娃子要主祭哦?”
“哎呀,老齐家的幺倌儿得嘛!”
感觉到了吗?是不是比《采蘩》的口吻轻松得多呢?

参考文献:
董同龢译《高本汉诗经注释》;《先秦诗鉴赏辞典》;竹添光鸿《毛诗会笺》。
本文系晋公子原创。已签约维权骑士,对原创版权进行保护,侵权必究!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
欢迎分享转发,您的分享转发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
— THE END —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