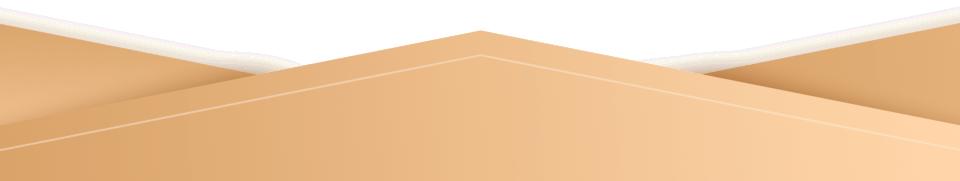人体标本制作师,一个没有人想要去了解的职业,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死尸,将它们按照不同的医疗目的,制作成形态各异的人体标本。
这份工作鲜有人问津,它不仅挑战从业者的生理极限,也在挑战多年来中国人的传统。

众所周知,中国人自古就对遗体的态度,以及处理方式慎之又慎,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周总理等多名开国领袖,以“节约土地”为口号联名倡导火葬,可直到1997年全国全面推行火葬制度前,土葬仍是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实行的唯一丧葬方式。
而到了2021年《民法典》开始实施,禁止土葬才第一次作为法律条文被实施。
对遗体重视的民风民俗根深蒂固如斯,国家尚且要花费几十年,才让人们逐步接受火葬这种加快遗体“消失”的丧葬方式,其他对遗体“有所作为”的事情,中国人更难以接受。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所有人第一次切身体验了生命的重要,无数感人的医疗故事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医疗的温情,种种影响叠加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人数首次破百万,完成了一年登记人数等于前8年人数总和的壮举。

2021年4月,据人民日报发文称,截止当时,器官捐献人数已经突破315万人,提前完成了2019年发布的《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20-2024年)》中提到的“到2024年完成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过300万”的目标。
不得不说,这里面有火葬推行的功劳,从前人们认为逝者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容亵渎,火葬推行后,“骨灰”替代了“遗体”,而“冗余”的器官捐献给别人,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况且捐献还有“生命延续”的美名。
可这些生命礼赞越发盛大的声势,始终没有触及一个“禁忌”领域——遗体捐献。
在描述遗体捐献在中国惨淡的局面前,请所有人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你慢慢接受死后可以是火葬,病危时愿意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捐献给需要继续活下去的人时,你愿意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吗?

大多数人的答案大概是不愿意,2021年,北京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人数11万人,但登记志愿捐献遗体志愿者只有约2.8万人。
在2021年,几乎代表了中国平均教育水平最高的首都北京,遗体捐献志愿者与人体器官捐献者比例约为1:4,其他地区不言而喻。
很多人或许不理解遗体捐献的重要性,但涉猎医学专业的人应该知道,很多医学学科离不开一位不会说话的“大体老师”。
“大体老师”,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现代医学离不开手术,学生也不能缺失对人体构造的了解。
人体构造复杂多变,不是一张死板的照片可以概括,手术又是性命攸关的“神技”,没有实际的人体,医学生认识粗浅,非但不能救人还会害人,因此人体解剖实操课、真实的人体,是医学生离不开的两样。

静默无言,任凭学生稚嫩、粗糙的手法来回研究,虽然没有师名,但大体老师的贡献在许多医学生眼中,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在我国各大院校的医学院,大体老师不仅受人尊敬,解剖前学生还会自发哀悼遗体。
除了这样的大体老师,有时被制作为标本的遗体也被医学生们称作“老师”,没有它们,人类现代医学不可能如此顺遂地发展。
即便如此,在面对全国医师超过400万人依旧面临相当大缺口的现实时,中国遗体捐献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医疗卫生未来发展的前景,究其根本,即是多年民俗影响下的那一句“我不愿意”。
这一点,王耀深有体会。
他一开始也没有想明白,怎么会有人愿意捐献“自己”。

王耀,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人体标本制作师,从业十四年,一年平均经手50具捐献遗体,可他制作的标本,一直难以满足医学研究院需要。
华西临床医学院,虽然隶属四川大学,但对接的是中国医疗界“四大天团”之一的华西医院,作为中国最好的四家医院之一,华西医院有上百年的历史,是中国西部支柱医院。
这里每天面对的疑难杂症是普通医院的几倍,医疗压力、医疗科研压力也不是一般医院能想象的,用于研究、教学的人体标本的需求也是不断上升。
王耀本是华西医院血管科的楼层管理员,人至中年,迫于生计压力,王耀开始主动接受华西医院医学气息的熏陶,学习人体血管相关知识,等待机会在华西医院的工作更进一步。

2008年,王耀得到了来之不易的机会,只不过这个机会看起来并不怎么“好”。
人言道,最好的老师既不是父母,也不是兴趣,而是生计,良师相伴,王耀学得相当不错,再加上耳濡目染,王耀一个门外汉对人体血管构造的了解,比一般本科生还要深刻。
靠着这份刻苦用功,相熟的医生将他推荐给了华西临床医学院,在简单的测试后,他获得了人体标本制作师这个职位。
人都对死尸有抵触,更何况是从事一份“摆弄”死尸的工作,可王耀的孩子上学急等着要钱,他也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咬着牙应承了这份差事。
两个月的培训后,王耀上岗了,怎么制作,面对什么问题该怎么处理,这些王耀理应烂熟于心,他该自信满满,但他去上班的那条路,走的格外忐忑。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嘉德堂,新式仿古建筑,外表看上去典雅大气,不过这份初印象在得知这是解剖、存放标本的教学楼后荡然无存,反而什么“古典带来的文韵十足”全部变成了为恐怖气氛妆点历史感的“大可不必”。
第一次来这里上岗时,王耀是有前辈带着的,走进去倒也没有路上那么忐忑,但他的运气着实不太好,他第一次面对就是一具高度腐化的尸体。
遗体捐赠者信息不明,他们也不该去打探,这是对捐赠者最大的尊重。
但按照人体标本的制作标准来说,人体标本制作的最佳时间在6-8小时左右,即便是冷藏,最多也不超过一天。
这具遗体显然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间,而他们要做得只剩下剔除遗体的皮肉,制作人体骨骼标本。

换作从业者以外的人,看到这具遗体,不免猜测遗体来源,但王耀并不会往坏的方向猜测,因为在我国,只有签订遗体捐赠协议方可将遗体制作为标本,眼下的腐烂,只能说明死者生前遭遇了很不好的事情。
带着多一份的怜悯,王耀和前辈对着遗体做了简单的默哀仪式,默哀结束,两人又鞠了三次躬,方才动手。
一般情况下,工作间是有一个小后门的,为了避免别人看见,通常是关着的,但在王耀的强力要求下,前辈半开了门,让外面的阳光打进来一部分。
高度腐烂的尸体,身上唯一还有生机的地方就是活跃的蛆虫,王耀刚一接触肿胀的皮肤,就有蛆虫摇摇晃晃地向他“打招呼”。

“生动”的画面让原本心情沉重的王耀,恢复了各种知觉,隔着口罩,恶臭的尸臭还在努力突破“防线”,往他的鼻腔里钻,钻进鼻腔后,又一路向下,勾动着胃壁,让它抽搐,将吃过的早饭挤出来。
王耀强忍着恶心,接过前辈递过的解剖刀,轻轻一划,黑乎乎的腐肉、组织液挣开皮肤的束缚向外涌出。
臭味更加明显了。
王耀用更大的毅力控制着大脑放空,控制着手继续操作,控制着胃不再躁动。
清理完腐肉后,失去弹性,坚硬的瓣状肌肉漏了出来,他再次挥刀,切开肌肉组织,漏出下面的骨骼,王耀反复着操作,和前辈忙活了很久,才将人骨从皮肉中清理出来。

期间,王耀没有休息一次,前辈叫停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了中午,前辈建议先吃饭,但王耀拒绝了,即便是带着手套,王耀还是要花些功夫去接受自己的手解剖过一具尸体。
而且,此时他的胃还在翻江倒海,根本没有心情去吃午饭,听到王耀的拒绝,前辈的眼神有些怪异,王耀将其误以为是惊奇式的称赞,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多荒谬。
一心想早点结束的王耀根本忘了在剔除皮肉后,要做的是剔除软组织和对骨骼进行防腐处理,这些只需要一种操作就可以完成,那就是水煮。
水煮法是人体骨骼标准制作过程中较为传统的方法,不仅便于去除附着在骨面的软组织,还能有效地将骨髓腔中的油脂逼出,防止骨骼从内部腐坏。

这个方法优点很多,但缺点更加明显,为了时刻观察骨骼状态,水煮过程中,制作者需要盯着整个过程,这不仅是对制作者视觉的冲击,还是对心理、嗅觉的冲击。
第一次工作以王耀吐得天昏地暗为结局,那一天之后,王耀一度想要辞去这份工作,但还是现实阻拦了他的任性,他咬牙坚持了下来,开始了十四年如一日的人体标本制作生涯。
毋庸置疑,这份工作很辛苦,遗体不仅会是以面目全非的样貌出现在王耀面前,更多的时候是在生命体征消失的第一时间送到王耀的手里。
有很多生前患有奇难杂症而不治身亡的捐献者,其遗体的医学价值十分高,但随着生命体征每多离捐赠者远一分钟,遗体的变化就多一分,距离想象的医学价值就更远一点。

这就导致王耀总是在和时间战斗,常常忙起来就忘记休息。
忙碌的工作,加上经验的丰富,王耀开始忘却对工作的不适,渐渐地自己可以独立一人完成不同的标本制作,尤其是血管类标本的制作。
他对血管格外熟悉,唯一的阻碍就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将错综复杂的血管自血肉中分离。技术操作要求很高,王耀克服起来很难,还经常出错,但王耀唯一的优势就是很少错漏一根血管。
他本来是为了不被扣工资去做分离血管的,但有一天,他刚刚制作完成的血管标本被立刻拿到了解剖课的课堂。
他静静地站在门外,听着台上教授的讲解,看到学生的恍然大悟,他突然咂摸出了一点不一样的意味。

尤其是当听到教授说“这个标本制作得很不错,没有任何错漏,你们可以以此为范例”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了与有荣焉。
“荣”的不是现在的夸奖,而是这些未来的医生们因为自己的一个标本,在医学道路上走得更顺遂。
因为这件事,他的工作情绪也转变了,从前他总是带着悲悯和遗憾去对待那些遗体,现在,只有敬重。
人类手术的早期发展史,无疑是一部反伦理史,无论是私掘尸体,秘密解剖,还是后来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鲜有光明正大的“推手”。
直到遗体捐献出现,人类虽然还是普遍难以理解“亵渎”尸体,但这些捐献者,却背负起了人类医学的发展,帮助现代医学不断进步。

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转变,王耀的心态也转变了,他去登记了遗体捐献,他再也不嫌弃整日一天忙到晚,甚至有时很矛盾地想就这么一直忙,亦或者变得更忙,一年50具自己吃得消,60具也可以。
但这样的想法,在亲眼目睹一次器官捐赠时,改变了,一次,他去医院办事,一个年仅6岁的小姑娘离世,她的家人痛不欲生,但还是将她的肝脏捐献了出去。
他被情绪感染了,迫切地想要知道小姑娘的肝脏后续会在哪里,他熟悉医院的捐献流程,他发现小姑娘的肝脏被移植给一个肝脏先天受损的5岁女孩身上,女孩的家人激动地哭了,是喜悦地哭。
悲痛,喜悦,移植是一个生命逝去的悲痛换另一个或几个生命新生的喜悦,绝望与希望交织,生命起落间完成交替,这样的冲击亚于王耀第一次工作。

遗体捐赠,捐赠整具肉体,看似不做任何的“生命交换”,实际上是一场与“死神”更伟大的交易。
交易有四个参与者,捐赠者、王耀、医生、“死神”。
“死神”带走生命,却把收割生命的伤痕当做代价留在人间,捐献者拿出伤痕向医生交易避免“死神”再以同样方法收割生命的办法,而王耀就是“定格”伤痕的中间人。
用一家之悲痛,换更多人未来绝处逢生时的喜悦,这便是遗体捐献者。
站在中间的王耀变得更加矛盾,这样很伟大,没有人不渴望这样的伟大有很多,遗体捐赠者家人除外。

王耀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不是所有人都有感情,也不是所有人都对逝者不闻不问,可只要世上还有人为了亲人离去而悲痛,王耀就难以祈祷经手的遗体再多一点。
十四年过去,不仅身边的人,甚至有时候连家人都很难与王耀共情,难以理解他在工作上的“乐此不疲”,经常在他半夜接到“紧急任务”慌里慌张时,感到羞怒。
“别人避之不及,你慢一点又能怎样?”这是王耀听到的最多的话。
他的回复也一样单调:“我快一点,医生就快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