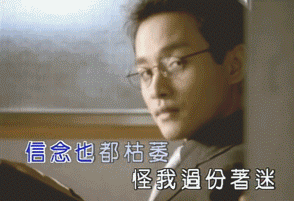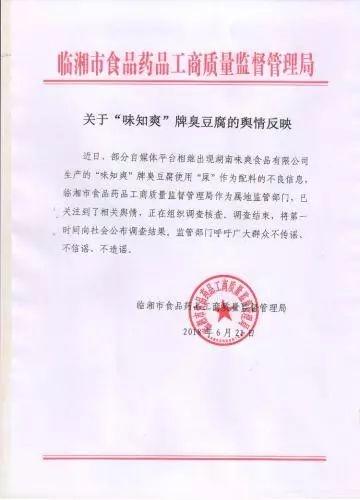今天开学第一天,忙忙碌碌。下午总算抽出时间看了一会书,乌台诗案,苏东坡人生的转折。(再忙每天都要抽出一点自己阅读的时间)

苏轼是个嫉恶如仇的人,看到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总要忍不住说出来,如农家三个月吃不上盐、农人青苗贷款等。把这些现象写进诗中,在他看来不过是直抒胸臆,记录世间百态罢了。可他忘了自己是一个誉满天下的大诗人,每一首诗都会被争相传阅,而且自己还有一个特殊的支持者:宋神宗。
每次收到苏轼的表章,宋神宗都会反复地读通,然后对臣子说:“苏轼大才!”听见皇帝这样说,朝中那些唯利是图、只会争权夺利的小人无比惊慌:要是苏轼得皇帝重用,自己还能有好果子吃吗?他们一直想找机会除掉这个眼中钉。终于,他们找到了这个机会:苏轼的几句牢骚话。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依照惯例,苏轼呈上了一封谢恩表章。在表章中,他说自己没有政绩,却得皇帝信任,不由感叹皇恩浩荡。这本没什么,可直爽自在的苏轼却在奏章末尾加了这句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大概的意思是,我不聪明,自然比不上那些升迁的后辈们。皇帝或许是看到我年纪比较大,至少不会惹出什么大乱子来,才派我来这里当地方官的吧。
古代文人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非常微妙,常把自己的本意隐藏在看似平淡无奇的语句中,读者自然也养成了寻找字里行间深意的习惯。苏轼无心的抱怨在某些臣子眼中成了伤人的刀剑:你说自己不会惹祸,是不是暗示我们会惹祸?你是想告诉皇帝,如今朝局混乱都是我们的错吗?
御史李定和舒亶更是将苏轼恨到骨子里。在关于新政的朋党之争中,“新进”是有特定含义的--王安石引进的无能之辈,“生事”则是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习惯用语。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的追随者看到这封奏章后大怒:这不是指着我们的鼻子骂吗?更让他们担心的是,朝廷定期出版这此公报,而苏轼的表章一定会被传阅,到时自己就会成为笑话。
苏轼自然没有这个意思,即使有,光风弄月的他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告诉皇帝。但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两人却想出了各种手段来对付苏轼。元丰二年(1079)六月,一位御史上书弹劾苏轼,摘抄了谢恩奏章里的那几句话,说苏轼故意制造矛盾,攻击变法派“生事”。当然,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李定和舒亶又我了几首苏轼的诗,将“尔来三月食无盐”说成攻击朝廷的盐禁令,将“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曲解为讽刺青苗法。如此一来,苏轼就成了包藏祸心、心怀不轨的小人。
一共有四份弹劾奏折被送到宋神宗的书案前。俗话说,三人成虎。御史群起而攻之,原本才华横溢的大诗人就渐渐变成了恃才傲物的狂妄之徒。宋神宗大怒,下旨:“一查到底!”李定和舒亶听后有些失落他们原本希望皇帝立刻下旨处死苏轼。不过他们又立马得意了起来:落人我们手中,你就别想翻身!他们特意让心腹皇甫遵去湖州向苏轼宣布这个“好消息”。
苏轼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此时的他远离庙堂、自在道遥,他喜欢独自一人爬山,也喜欢在潮湿、温暖的早晨和大儿子去山林间散步,还喜欢和知己好友去拜访寺中高僧。在李定、舒亶嘱咐皇甫遵速速将苏轼押解人京时,他正抱着自己的名画,准备将把它们拿到院子里去晒。当他无意中看到过世好友送给自己的画时,竟不由得流下泪来。他被贬出京时都没有这样流过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