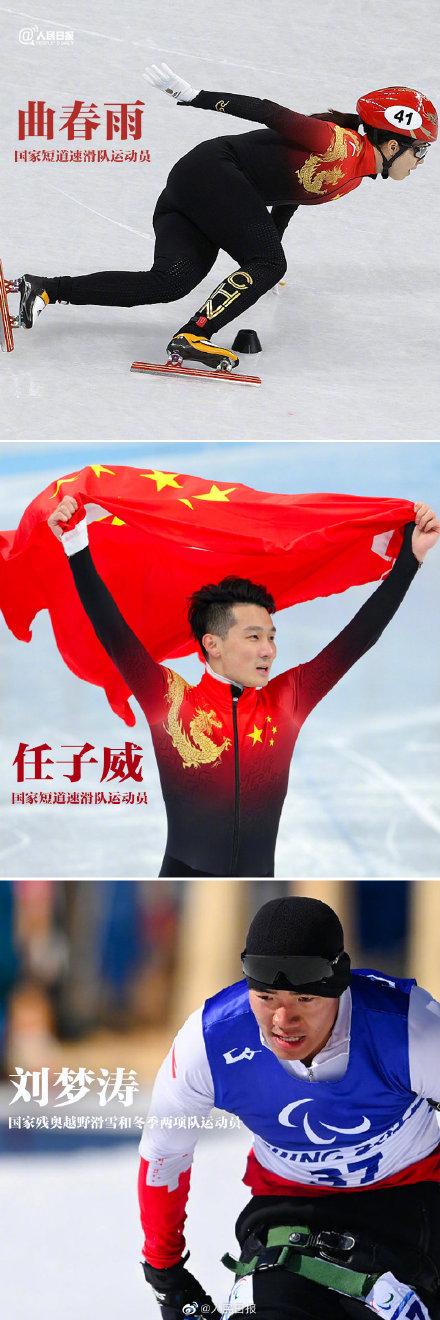在中国科举的历史长河中,有极少数成功者,科场上春风得意,光宗耀祖,登第为举人进士,他们大多成为国家政权的管理者,属凤毛麟角;还有巨量的失意者,科场上屡试屡爽,试辄不售,始终默默无闻,属芸芸众生。在这芸芸众生中,尚有很小一部分获得了初级的秀才功名,严格说这些人不能算作失意者,毕竟他们与最普通的老百姓拉开了阶层意义上的距离,作为封建社会占人口极少数的读书人,已进入国家后备人才序列。至咸丰朝(1851--1861),全国参加童生试的读书人约450万,考中秀才的约15万,占3.33%。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就是这样一位读书人,说他是科场成功者亦可,说是失败者亦可,说他成功,蒲松龄19岁(虚岁)时,在一年的时间内,县、府、道三试第一成秀才,小试牛刀就一鸣惊人;说他失败,终其一生直到76岁去世,都没有考上梦寐以求的举人,进士功名更是只有望洋兴叹的份了,他自己可能都不敢奢想。
蒲松龄72岁那年作诗感慨:“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其蹉跎岁月、科举失意的情怀跃然纸上,他自认为白头到老而一事无成。由此可见,我们后人颇为看重的《聊斋志异》在大作家的心目中是无法与中举相提并论的。
二、并无证据证明蒲松龄的失利是受到了考官的刁难迫害或所谓胸无点墨的误判。清初科场对舞弊事惩处极重,顺治二年的“南北闱案”,不仅受贿考官和行贿考生全部被斩首,父母妻子流放,亲属亦被株连。顺治十四年,山东科案中,六名乡试同考官被革职下狱问罪。蒲松龄赶上的乡试正巧在这些严厉的处置之后,据胡海义、吴阳先生的考证,自康熙二年(1663)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山东乡试的主副考官金煜、吴国龙、张鹏、王掞、张鸿猷、翁书元、高龙光、曹禾、林尧英、曹鉴伦、柯愿、佘志贞、张廷瓒、李象元、王思轼、觉罗满保、魏方泰等人,都是为官清正、品行端谨之人,在主持乡试时并无恶评,取士公平公道,均没有发现营私舞弊问题,而且他们都是朝廷慎重挑选和临时指派的,一般都是翰林出身,包括同考官在内,也都是举人、进士出身,不可能是胸无点墨的糊涂蛋,朝廷对他们的约束亦很严厉。至于科举中请托的风气一直存在,它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考实的不多。事实上,蒲松龄为参加康熙十一年的乡试,请同乡进士、宝应县知县孙蕙为其写了“有力”的推荐信,希望山东官员能够重视这位蒲秀才,结果亦是枉然。
蒲松龄平日遇到的更多的考官是自施闰章开始到黄叔琳为止的21任山东学政,因为他们要主持岁、科两试,包括院试。院试原称道试,清初沿用明代提学道机构,山东提学道在济南、青州均设有机关,雍正时正式改学道为提督学院,后来青州学道机构撤并,统属至济南提督学院署,位置在大明湖南岸。这是很多人搞不清蒲松龄县、府、道三试第一的原因,主要是不明白这个“道”是什么意思。资料显示,蒲松龄是在青州参加山东学政施闰章主持的考试后得的秀才功名。那么,青州的考试是个什么级别的考试,令很多人云山雾罩,晕头转向,有人说是府试,有人甚至说是济东泰临道的考试,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说蒲松龄“在淄川县、济南府、山东学道的考试中,连取三个第一,在山左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主持院试的学台,是山东学道施闰章”。这段话似是在打马虎眼,马教授虽然煞有介事地把“学道”“院试”“学台”搅合在一起,但并没说明白“道”,显然她不清楚“道试”“院试”的关系。事实上,施闰章的正式官称为“提调山东学政”,而不是山东学道。清朝的省学政有很多说法,如学使、学道、学院、学台、学宪、学臣等等,其中学道的说法由各省提学道衍生而来,现在广为使用的“学院”的说法由各省提督学院演变而来。提学道机关主持的考试即为“道试”,它等同于后来的“院试”。路大荒先生《蒲松龄年谱》所说“是年以县、府、道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受知于施闰章”是比较准确的说法,马教授因为不明白而没有采纳。道试由各省学政主持,通常在学政“按临”一地时与岁、科试一起进行,针对生员进行岁、科试,针对童生考秀才进行童子试。如翁同龢1858年担任陕甘学政时曾经“按临”乾州,对乾州和邠州两属生员666人和童生分别进行了岁考和童生考试,各考三场,另外,还考了教官(各州县的学正、教谕、训导等)和武生。当年由山东学政施闰章坐镇青州举办的正是这样一次考试,除了考青州府属的童生外,应该也考了济南府属的淄川的童生,但他肯定没有考武生,因为施闰章只是提调学政而不是提督学政,权限不够,后来的学政黄叔琳则有了此权限。其实,在边远地区,道试的说法沿用很久,如《洪秀全传》中就说洪秀全自幼聪明,十五岁县试得前十名,后来又通过了广州府试,但一直考到31岁,道试也没通过。
清代各省学政三年一任,特殊情况如丁忧、调动、死亡等,随时更换,学政差不多每年都要主持各种考试,忙得很,蒲松龄遇到的山东学政分别是施闰章、刘昌臣、刘芳声、王鑨、周龙甲、杨毓蔺、蒋胤修、梁遂、钱江、劳之辩、桑开运、唐庚尧、宫梦仁、任塾、朱雯、刘谦吉、陆鸣珂、徐炯、顾悦履、赵申季、黄叔琳。这21位学政大人,蒲松龄对施闰章和黄叔琳特别感恩戴德,多有记载,而对于1682年出任山东学政的钱塘人唐庚尧未见言及,1683年,蒲松龄由增生考取廪生,应该是通过了唐学政主持的考试,这是很重要很光彩的一步,不知何故,蒲松龄的现存文献中对他好像只字未提。
所有21任学政中,蒲松龄唯一对朱雯编过指名道姓含沙射影的故事,对其他20位学政未见什么不满。《聊斋志异》中收有一篇《蚰蜒》,就是贬损朱学政的:“学使朱矞三家门限下有蚰蜒,长数尺,每遇风雨即出,盘旋地上如白练。然按蚰蜒形类蜈蚣,昼不能见,夜则出,闻腥辄集。或云:蜈蚣无目而多贪也”。其实,学政朱雯(字矞三,浙江石门县人)官声甚好,有“尽心所事,劳勣百端”之誉,离任江宁之时,为府学“捐俸修整四碑亭及两庑门栏”。康熙二十三年(1684)“分校南闱,首得王方邺卷,极荐主司,因限于额,竟置副榜第一,甚为扼腕。”王方邺的诗词古文在清初名重一时,朱雯实在不能说是有眼无珠,堪称慧眼识才。
蒲松龄对科举的不满主要限于乡试,而且把管理考场事物的杂七杂八的外帘官,如监试官、搜检官、弥封官,和内帘官,如主考官等混同起来,将外帘官对于穷秀才的呵斥粗野等以偏概全地归罪到内帘官身上,“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思考,官呵隶骂是对企图作弊者的震慑,是有价值的。其实,对于士子的考前检查,如脱鞋子、搜衣襟往往是由最低层的官兵执行的,搜检官可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干这活。而对于最核心的起关键作用的内帘官中的同考官(房官),蒲松龄聊斋中鲜有涉及,分析之下,感觉是逸重就轻,张冠李戴了。蒲松龄对自己科场得意的童生试和从未参与的会试向来不说三道四,其文学讽刺呈现出一种盲目而狭隘的发泄情节。在《三生》中,蒲松龄让众考生请阎罗王剖出主考官的心,“沥血鸣嘶,众始大快”。除童生试外,蒲松龄一直不被历任乡试同考官认可,难道说那些考官都是有眼无珠的瞎子,要挖眼剖心吗?
三、蒲松龄的八股文不符合考试衡文的标准,科举考试用的八股文是“制艺文”或称“时文”,它不是天马行空的玩法,注重“理、法、辞、气”,有相当的逻辑性,讲求论据论证,思维求同,有点像现在的领导讲话,不要花里胡哨,要中规中矩,属于政论文一类,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其标准化程度是最高的。现在的托福考试和高考不也是这么玩的吗,有确定的尺度。蒲松龄长年搜集离奇故事的活动,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求异思维习惯,小说笔法多,形象思维多,富于奇幻,擅长文艺描摹,而且无所顾忌,莫言自称是蒲松龄的学生,真是挺像。蒲松龄虽然没有现代人媚俗的初衷,但猎奇搜艳的“积习”难改,比如,他在性的描写方面从不避讳,写性无能、性狂躁、同性恋、性怪僻、猥亵、强奸、诱奸、乱伦、群交、人兽交等等,在他的聊斋故事里屡有展现,甚至还写过一篇儿子为不让父亲与小妾再生儿子分家产而把父亲阉割了的《单父宰》。事实上,蒲松龄在宝应县为孙蕙作幕僚时,所写的公文、告示或书信中,有许多亦是如此笔法。如“送往迎来,则贱如声伎,婢膝奴颜,则状同伏鼠”,虽有看点、有卖点,但终属浮俗。可能正是这个原因,进士出身著述严谨的纪昀对蒲松龄的“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不以为然,认为“《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要知道,搜神志怪与科考文章的写作手法有很大的不同,二者是在两个方向上用力的,在搜神志怪方面,蒲松龄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被人认可,录取他为岁贡生的山东学政黄叔琳就曾经收过蒲松龄孙子蒲立德专门为其抄录的《聊斋志异》,难逃特别关照的嫌疑。而科考能力方面,有学者对《聊斋全集》卷十收录的23篇八股文进行过分析,发现蒲松龄的这些八股文章更像随笔、散文,文学味较重,甚至有篇幅过长的毛病,康熙时八股文的字数要求在550字,你洋洋洒洒没完没了也不行,550字内要写好确有难度。
另一方面,治举子业用心不专也算个原因,或者说《聊斋志异》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科举考试,这主要不是说写聊斋占用了科举备考的时间,而是说写小说的手法与写八股文的手法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套路。前面说过,写聊斋和考科举是蒲松龄人生中的两条线,并行不悖,没有逻辑上的制约关系,但二者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干扰,有相关性。进士出身的知县孙蕙就告诫蒲松龄要“敛才攻苦”,他的朋友张笃庆也劝他放弃聊斋故事的搜寻,专心科考,都是说两者很难兼顾。就普通人的才能如蒲松龄者,想科场成功,需要切实投入大量的时间、努力和日常训练,如果指导正确,准备对路,全力以赴,全身心投入,未必不能侥幸考中举人,当然,也未必能考中。因此,治举子业用心不专绝不一个重要原因。
四、蒲松龄多多少少有点心理障碍,心理素质不是很好,考场上犯过不止一次低级错误,他的喜怒哀乐一定都刻在脸上,写在文字里,他对学政施闰章和黄叔琳的露骨的感恩在小说和文章里均有体现,看上去有点过。反之,他对不录取他的考官的恶狠狠的杀气腾腾也写进小说里,从不讳言,他更多的是小民百姓式的较为直接的发泄,更接近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有点像个怨天尤人被惯坏了的孩子。尽管如此,蒲松龄并不是科举失利极端的例子,广东顺德人黄章四旬入学,六旬补廪膳生,83岁选岁贡生,百岁应顺天乡试,三水人陆云,入学为秀才时已经百岁。人生挫折常在,而应对各有不同,同样是遇到挫折,大文豪司马迁表现出另一种格局,他遭受那么大的耻辱,其《史记》《报任安书》等作品也属移情似的创作,但其有升华、有境界,藏之其山,传之其人,鲜见直接的个人情绪发泄,司马迁基本上不直接贬损人,而是对他喜欢的人物进行升华。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移情模式,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县试府试都不错,唯道试不售,说起来还不如蒲松龄呢,洪秀全一怒之下揭竿而起,干脆自己举办科举考试,其科举考试甚至在起义的第二年(1851)就在广西永安开始了,花样还不少,有乡试(信士、艺士)、县试(秀士、英士)、郡试(贤士、能士)、省试(文曰俊士、武曰毅士,提考官所取为约士),到了天试(进士)这一级,也不叫进士,而叫达士,可见封建社会小文人的科举情结是多么的沉重。
康熙二十六年,蒲松龄再次参加科考,可能是对乡试有了某种恐惧情结,表现为一上场就亢奋,犯下“越幅(中间空了几页)”的低级错误。其实在考场上,也不是绝对不能“犯规”,苏东坡在科考时就有“违规”发挥,他在考卷中杜撰了一个上古的典故,唬住了学富五车的宿儒考官梅圣俞,不敢提出质疑,担心一经提出,即表明自己没有读过年久湮没的古籍,他丢不起这个人。不过,你很难要求蒲松龄有这样的心理素质,他远不具备那样的逻辑幻想能力,蒲松龄的创作基本上是有本有源的,他的故事绝大多数都是先听来再加工,或许没有横空出世的完全个人想象式的创作。比如说,《聊斋志异》中有一篇《人妖》,写的是山东东昌府人马万宝行淫之事,其所本即是明人陆粲所撰《庚巳编》卷九的《人妖公案》,原载《明实录》,只不过原来的主要人物为成化年间山西太原府的李大刚之侄,其人男扮女装,“暗行奸宿,一十八年不曾事发”,这两篇“故事”的题目甚至都相同,结尾处,蒲松龄还以“异史氏”的名义发表了一段评论。
如果蒲松龄的才情足够用,心理素质足够强,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科举努力,即使是有时发挥不好,或遇人(考官)不淑,或病或灾,未必不能像晚清状元张謇那样,最终考上举人,张謇4岁能背诵《千字文》,16岁考中秀才,期间经过18年的六次乡试,方才得中举人,又经过5次的会试失利,最终考中进士成状元,只说明他确实有这样的才能实力和应试素质。

五、需要注意的几个点。
1、蒲松龄的童生试确实很意外,先是被淄川县知县费祎祉(鄞县进士)考为县试第一,费祎祉是他最应该感恩的人,接着被济南知府考为府试第一,最后被山东学政施闰章擢为道试第一。按照惯例,县试第一称补博士弟子员,一般就自动认定为生员,府试、道试(院试)第一不第一的都不是很重要,只是名声好听些。蒲松龄都成了县试的“案首”了,万里挑一了,还能不算个秀才吗。应该说三试第一轰动乡梓,名噪一时,是个小概率事件,似乎暗示着他日后科举考试的不顺利。
2、蒲松龄由附生到廪膳生用时极长,秀才也叫生员或附生,过去说的生童是两个概念,一个是生员,一个是尚未中秀才的童生,生员进一步为增广生,增广生进一步为廪膳生,这是秀才中的最高层次,因为这时可以食廪,就是官府给一定的粮食补助或银钱,廪膳生是有一定名额限制的,淄川县在同治九年(1870)廪膳生、增广生各为20名,康熙朝或不超过15名。在这15人中,生员不能直接食廪,廪膳生按空缺顺序递补,必须退一补一,不出不能进,不能随意扩编。退出廪膳生的最好渠道是考中举人,其次是考中“五贡”,大意是把他们贡献给国家,入京城国子监(国学)读书,或者病退、死亡等,只有这样,下一个成绩优异的增广生才能进入廪膳生行列。要成为廪膳生,需要通过学政组织的岁考或科考,学政并不专门组织升廪膳生的考试,而是在“按临”一地时将附近的生员们集中起来,在进行岁考或科考时合并举行,同时考核各州县的教官。成绩优异者可以晋升为增广生、廪膳生,成绩最差的连秀才功名也保不住,教官考不好也要受到处分,如果你成绩平平,永远进不了廪膳生行列。这几步看似不难,蒲松龄却用了25年,44岁补廪膳生,进步很慢的样子。
3、蒲松龄没有抓住最佳的中举机会。康熙十七年(1678)乡试,蒲松龄39岁,正值年富力强,是最有机会考取的一年,这一年山东录取比例极高,为十五取一,康乾时期的录取比例一般在一百取一至六十取一,皇上发善心的时候或三十取一,十五取一极少见,等于是朝廷优待士子,而这一年考中山东乡试第一名解元的恰恰是一位淄川人毕世持,他超越了当时的名人赵执信(写有著名的《华不注山行》等诗文),可惜这个毕世持中解元后再无进步,三次会试不第,八年后,39岁一命呜呼。当然,参加乡试之前要通过学政组织的科试预考,将较差的生员筛掉,这可能主要是考虑乡试的特点,乡试不像岁考或科考,可以在学政按临的州府举行,它必须集中到济南一地举行,由朝廷临时派员主考,如果考生太多,考场、服务、监督、批卷等方面都是沉重的负担,这有点类似八十年代初期山东高考的预考,是一次选优的过程,落选者将没有机会参加高考。

4、蒲松龄没有中“荐卷”的迹象。一名秀才能不能考中举人,关键不是看那些杂七杂八的内帘官,甚至不是看主考官,而是看同考官,因为考生的卷子首先送到同考官那里批阅,如果入不了同考官的法眼,不会推荐给主考官,也就没有机会被主考官批取。当然,对士子的取舍确有考官的主观性,但同考官在所批阅的众多的考卷中要选出最佳者送到主考那里,他要考虑自己的名声,一般不会随意推荐,因为可供选择的卷子太多了,他弄个资质平平的卷子推荐到主考那里,会被主考笑话自己眼力不济。所谓“荐卷”,即乡会试中,同考官批阅后,选择自己认可的推荐到主考官那里的卷子。主考通常在各同考官推荐上来的荐卷中决定是否批取,未被批取的是“落卷”,这是一种狭义的荐卷,这样的“荐卷”是很被看重的,是可以载入家谱的光彩经历,甚至与批卷的同考官亦属师生关系,可以长久往来。
过去科举考试有刻荐卷的习惯做法,同治元年会试时,同考官孙家鼐(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就将他批阅的荐卷全部刻印出来,并选出三篇最佳者,那年的会试“落卷”共有99套。同时,主考官还有搜落卷的程序和义务,即使开始没有批取,尚有被主考弥补的可能性。蒲松龄历次科考的悲剧在于,其试卷还未到乡试主副考官那里,就被历任同考官枪毙了,也没有被主考官捡漏,无缘成为荐卷。他的同乡孙蕙就出任过江南乡试同考官,康熙二十年做过福建乡试正考官,曾经给蒲松龄寄过福建的考卷,他最了解蒲松龄的“毛病”在哪里。理论上说,蒲松龄近五十年的科考历史,即使不能侥幸中正榜举人或副贡,尚有成为荐卷的可能性,如果不中而成为荐卷,也是很骄傲的事情,它比食廪的层次高得多,会在家族中留下记忆,显然,我们没有看到蒲松龄相关的记载,他也没有尊称哪一位同考官为老师,与科举中式差得较远。
5、蒲松龄并无凭落卷讨要公道的记载。科举制度发展到清代,已经非常完善了,其表现之一是确立了一项安抚落第士子的制度“发领落卷”,乡会试落榜的考卷在十日内发还考生阅看,考官必须在上面批注不中的理由,以示公平。如果考官鱼目混珠,不识好歹,肆意摒落佳卷,考生可以举报告官,直至上访到礼部。嘉庆三年,湖南乡试中,湘阴考生彭珴落榜后,发现自己的考卷竟然不见了,等待乡试录刊印后,却见第一名解元卷竟然是自己的原作,他立即告官投诉,最终作弊者被处斩,彭珴得以赏还举人功名。显然,蒲松龄没有类似的经历,他被发还的落卷时,面对考官批语,或许不得不口服心服。
6、蒲松龄由廪膳生到岁贡用时亦极长。康熙二十二年(1683),蒲松龄44岁,补廪膳生,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食廪29年之后,才在青州考取岁贡生,与他的好朋友张笃庆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为府拨贡相比晚了25年,与淄川人赵金昆(1709)、刘振元(1707)、孙允滋(1706)、刘大儒(1703)、仇嗣广(1701)、王仪世(1699)、陆肇铨(1697)相比,蒲松龄也骄傲不起来,他们均在蒲松龄之前考得了岁贡。晚清探花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指出:“府、州、县廩生食餼十年后挨次升贡者曰岁贡”,基本上是论资排辈依靠年资获得的“援例”行为,有国家照顾性质,可能正是这个缘故,县令也不太重视,出贡半年多,既没有按规定给他立旗匾,也没有给他发贡银,闹的蒲松龄很不高兴。《清史稿》记载,康熙朝定岁贡“府三岁二人,州二岁一人,县三岁一人”,淄川县似乎是享受了州的待遇,二岁一贡。蒲松龄72岁中岁贡后作的诗“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是一次科举失意的大悲叹,“五贡”中的副贡、拔贡、恩贡、优贡好赖都有自己的同年,唯有岁贡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的功名,连个同年都没有,毫无骄傲的资本。
7、蒲松龄的所有学生无一人中举。如果说蒲松龄五十年的科举奋斗未能中举有些偶然因素,那么他在王敷政家坐馆(任私塾先生)3年,在毕际有家坐馆30年,所教的学生及蒲家子侄中无一人中举,则说明他的那一套科举路数概不合宜。而他的朋友张笃庆在焦家坐馆20年,所教学生焦绥祚后来中了进士,比他强很多的感觉。蒲松龄长子蒲箬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中秀才,38年之后,雍正四年(1726)为岁贡生,好像也不太聪明,最多是和老爹打了个平手,至于他的孙子蒲立德在黄叔琳主考时得院试第一,其真正的成色也得打个问号。
8、剑走偏锋,噩梦肇始。有人说山东学政施闰章是蒲松龄科举失意的罪魁祸首,有一定的道理。施闰章激赏蒲松龄的那篇文章,恰恰是一篇小品文的感觉,不是八股文,而施闰章高度评价说:“观书如月,运笔成风,有掉臂游行之乐”,这似乎是在纵容蒲松龄不拘一格,随意挥洒。初出茅庐的蒲松龄信以为真,拿着鸡毛当令箭,从未怀疑过恩师对他卷子的评价会有什么问题,他特别看重施闰章的意见,而且会一直沿着这个思路准备,终生不易。如此南辕北辙,岂不是以爱的名义扼杀蒲松龄的科举事业吗?自从三试第一成生员后,穷秀才的噩运就真正开始了,在接下来的乡试征途上,“三年复三年,所望竟虚悬”,蒲松龄算是没有出头之日了,正所谓“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

蒲松龄总觉得自己很丢人,怨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