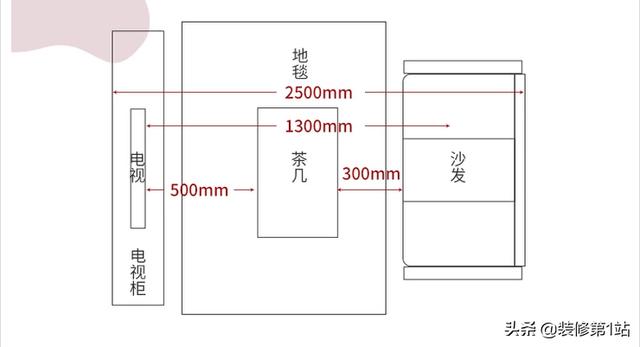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句话出自《诗经·小雅》,体现的是我国从周朝便开始出现的“天下”观,天下便是普天之下,而不管这个天下有多大,都是“周天子”的臣民。
如果说这一观念在先秦之时还是一种理念,或者说一种理想状态,那么秦皇南征和汉武西进便将这一理念变成了现实。从此整个东亚地区,整个文明地区全部纳入了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内。

在这个体系中,以“天子”为核心,向外依次是内臣、外臣和朝贡国,外臣便是藩属国。而朝贡国之外则是化外之地,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1、秦汉秦汉时期的华夏文明是自信的,也具有明显的对外开拓性质。秦始皇的南征百越,将华夏文明传入长江以南;汉武帝的西域凿空,使华夏文明第一次传入西域;两汉的北击匈奴更是将这一时期华夏族的自信和开拓精神体现的淋漓尽致。
汉朝有四句话至今仍被我们广为传诵:
-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霍去病,封狼居胥
- 汉军方至,敌勿动,动,则灭国。——傅介子,斩杀楼兰王
-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陈汤,斩杀匈奴郅支单于
- 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汉朝之于中国,犹如罗马之于欧洲。正如《汉武大帝》中所言:
他给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建立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
汉朝,永远使人心驰神往,即使强大如后世的唐朝,也常常以汉朝自喻。
2、隋唐秦汉的大一统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后遭到了巨大的挑战,随着五胡的入主中原,华夏文明开始衣冠南渡,原本的天下出现了近三百年的动荡。
不过,随着以鲜卑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与北方汉民族的融合,我国出现了第二个大一统时代,这一时代从本质上来说其实与秦汉时期是相同,同样信奉华夏文明的“天下观”,同样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唐太宗李世民甚至认为: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也就是说,李世民甚至将四夷之地同样划入了当时的“天下”范围之内。唐朝之时的“天下”比汉朝时期更大,各国的遣唐使纷纷进入长安朝拜,大唐使华夏文明又一次真正成为了天下之主。
-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
-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
-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
-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
-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
边塞诗,是唐诗中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许多诗人都有边塞和军旅的生活经历,其诗作中大多表现的是阳刚之美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同时体现的正是大唐帝国雄浑的盛唐精神。
3、两宋安史之乱和唐朝的灭亡,是我国整个帝制时代的转折点。关于这一点,明朝陈邦瞻曾在《宋史纪事本末·序》中这样写到:
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
也就是说,战国七雄与汉朝之间为一大变;而唐宋之间又是一大变。
唐宋之变,在史学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唐宋变革论”。唐宋之间的这一变化自古至今的史学家其实都有表述,也没有疑义,只不过将其作为一个理论来提出的却是出自日本的史学家内藤湖南。内藤湖南认为,唐宋之间并非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巨变。后来,许多的史学家都对此表达了相似的看法,比如:

- 其一,隋唐之时的中国是门阀世家政治,而宋代则是在平民政治之上的君主专制。
宋朝之前的皇帝,本身便是世家大族的一员,其能否独裁专制其实受自身的能力影响甚大,一般的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相权是皇权的重要制约。
而从宋朝开始,世家大族消失,皇帝又通过撤掉宰相的椅子,终结了坐而论道的传统,朝臣与皇帝的距离遂越来越远,而这一点为明朝废除宰相奠定了基础。
- 其二,隋唐之时的中国世家大族依然是高官的主要来源,而从宋朝开始真正开始了科举取士
科举虽然兴起于隋唐,但并未真正主导有唐一代的政治,据统计,唐朝每年通过科举录取的官员不过五十多人,朝廷基本上还是被世家大族所掌控。
而随着世家大族在唐末被黄巢屠戮殆尽,宋朝并未重建世家大族,而是真正开始了以科举取士代替了世家大族,文官政治开始形成。
此外,还有很多,比如农民从世家大族的奴仆变成了国家的佃农;党争从世家内部的权力之争变成了士人学子之间的政见之争;宋朝的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出现了纸币;文学从骈文演变为散文,豪迈的唐诗也变成了婉约的宋词。
不过,如果从帝国对外的角度来看,两宋与汉唐最大的区别便是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变成了“画地为牢”。

宋初,赵匡胤虽然也认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但其在统一中原地区的过程中玉斧一挥,便把大渡河之外变成了“化外之地”,也就是放弃了西南夷。
宋朝与汉唐不同,它开始于辽、西夏、大理划定边界,开始产生了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其文化内涵不再是开拓进取,而是转为内在的单纯和收敛。
宋朝与汉唐不同,虽然其对外交通也很发达,但其排斥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本位文化和华夷之辨超过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曾经的“普世”观念。
- 公元1005年,辽宋签订了《澶渊之盟》,盟约规定两国以以白沟河为界;
- 公元1044年,宋夏签订了庆历和议,规定西夏在战争中占领的宋朝领土从中间划界。
这些盟誓也好,和议也罢,其实都与后世清朝的不平等条约类似,对于宋朝来说就是割地赔款,画地为牢。

宋朝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不同,它在名义上还代表着整个华夏文明的正统,也在事实上占据着传统华夏文明的核心区。于是,宋朝的“怂”,使中原王朝从此不再有开拓进取之心,而科举取士的文官政治强化了这一立场。后来的明朝虽然在开国之初一度向外开拓,但不久便又陷入了与宋朝同样的境地。
我常常想,若非后来的元清两朝,我国大概率就会保持在画地为牢的长城以内,福祸相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