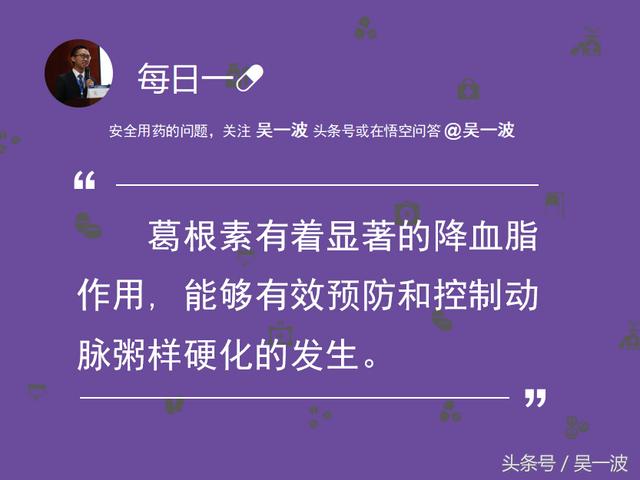很难说如果不是因为金马奖折桂,这么散淡的一部《八月》会不会有机会到院线上跟观众见面。这部电影充满了台湾电影新浪潮的种种气息,也难怪颇受台湾评审们的青睐。

《八月》海报
导演叫张大磊,片中的小男孩叫张晓雷。张大磊用近乎白描的手法讲述了张晓雷上初中前那个暑假无所事事的时光。小孩子的世界单纯又无聊,大人们的世界却因为赶上国企改制的时代大潮而面临着一场巨变。

晓雷
那些扑面而来的怀旧气息,散落在时不时唱起的苏联歌曲里,夏天学游泳的姿势里,夜晚灯光下变化着手势做手影的游戏里,家属大院嘈杂的广播里。
当父母问晓雷为什么想上三中时,晓雷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三中的校服好看帅气。这还真是被遗忘的小插曲。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童年时也曾认真地和小伙伴们讨论过各个学校校服的美丑差异。穿什么样的校服,也曾真真切切地成为小孩子们对于成长的诉求之一。
黑色影调是一种怀旧,也更显单纯。《八月》的摄影很好,明明不见色彩,却有温暖又明媚的感觉。早前曾在俄罗斯学电影的张大磊,显然也受到了塔可夫斯基等苏联电影大师的美学影响,尤其是各种过场戏中对水和倒影意象的运用,为电影平添了不少诗意。

当然,这部电影在美学上更倾向于台湾电影的风格,大量隔着窗户和门拍摄的角度,不稳定的光源闪烁的光线,小孩子背对镜头面向的成人世界,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种种拍摄手法,在这部电影里都屡见不鲜。
不过影片更让人触动的,是片中弥漫的平实的生活气息。日常对话的那份散漫随处可见,起了个话头、似乎值得一说的重要的事,下一个接茬的人却漫无目的地把话题带到了不相干的事情上。没有一本正经的对话,每个人的心事都被淹没在平淡的生活里。

晓雷父亲
作为一部致敬父辈、描摹旧时光的电影,《八月》里没有刻意的美化或批判。片中的父亲虽偶有迷茫,一面说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一面又不停地说“我觉得没什么,凭本事吃饭是好事”。旧时光里的团结和光荣也没有被渲染和煽动起来,兄弟们各奔东西、闷头喝上一杯酒,不说豪言壮语,转眼也确实有人过上了好生活。影片也没有拍人因为失业或者失去理想而萎靡,不过是换了种活法,谁的生活都在继续。
事实上,那样一个暑假,应该是焦灼的。影片中,母亲的角色承担了这份焦灼,她一面要面对娘家老人的重病,一面焦虑着儿子够不上重点初中的分数线,全家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工作,丈夫已经好久不开工了,眼看着铁饭碗又要被打破。

晓雷全家福
在晓雷母亲的娘家这条线索中,提到了她哥哥三十年的工龄都换成了毛线、不知如何是好,父母与儿媳之间似乎也有着长达数年的矛盾累积,年轻漂亮的妹妹帮晓雷开了上初中的后门、又给了晓雷母亲一笔钱,说明晓雷家经济也不宽裕。
然而这些焦灼也并没有被放大成带动观看者焦虑的情绪,镜头保持着冷静的旁观距离,并没有在交代这些负担的部分给出哪怕一个特写的强调。那些不安和矛盾,就像生活里习以为常的存在一样,不会爆发,只是一种让人习惯的膈应。
而其中的种种对照,其实被导演打磨得很是工整。比如小男孩即将面对的新世界,和一个老人卧病在床生命一点点流逝;比如晓雷刚开始发育的身体、象征着蠢蠢欲动的叛逆的双节棍,和一个看似叱咤嚣张的“孩子王”三哥在父亲出意外后将接下父亲的班变成一个社会人;比如一个个体的无忧无虑,和一个时代的分崩离析。

影片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是,晓雷看着一群大人奋力推着抛锚的大卡车,转而一拐弯,走向了分岔小径上的一片山林,好似两代人就此分道扬镳,一个时代的集体符号在远景处虚焦,年轻的个体走上了孤独而未知的旅程。
然而《八月》的表述也仅此而已。你惊喜于它的淡,然而细品之下,也就只能品出这种淡而已,电影没有什么力度,也没有更多层次的回甘。
影片既然像台湾电影,导演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自己深受台湾电影的影响,那么对照同样以孩童视角出发的杨德昌的《一一》或者侯孝贤的《冬冬的假期》,都能明显感受到这部电影的单薄。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右)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另外一个路数。影片中,小四是绝对的主角,杀人事件以及整个环境的境遇是和少年本身对峙的。而《一一》中的洋洋,或者《冬冬的假期》里的冬冬,则和《八月》中的晓雷一样,属于旁观的线索人物,不是情节中矛盾冲突的焦点,不过是导演们展现观察成人世界视角的一个出发点而已,而且这三个小孩都处在亲人饱受病痛折磨的阶段。

《一一》中的洋洋

《冬冬的假期》中的冬冬(左)
在开始初识生命的时候,站在童年和少年交接点的门槛上,洋洋通过相机观察着成人世界,其间种种荒诞与心酸,串联起人世的种种境遇,好像通过一个小孩子的眼睛看尽了一生,最后感慨一句“我觉得,我也老了”。
冬冬和妹妹的暑期见闻,则折射出孩童与成人世界的距离。在那个假期过去后,他们懂得了关爱与理解,学会了承受和分担。一个冷峻,一个温暖,一个批判,一个关怀。
对比之下,晓雷的暑假,过得的确有些像影片最初的名字了。哦,影片最早叫《昙花》,惊鸿一片,不着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