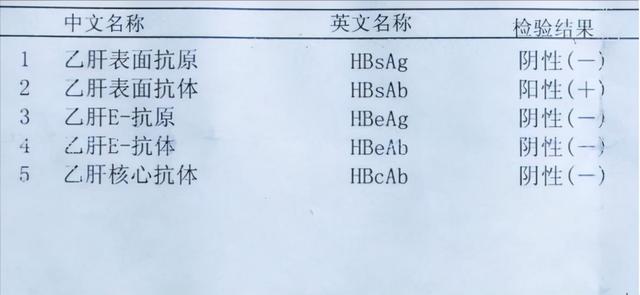前一阵子,看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其中讲到毕飞宇,他从小四处漂泊,从村庄,到县城,到都市,那个地方他都待得不长当他回到曾经生活的土地上时,他突然停住了,看了很久想了很久,镜头推到他的脸上,他的眼睛里涌上一种酸楚,他就背过身去了我也被他的伤怀之情触动,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有一种眷恋叫故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有一种眷恋叫故乡
前一阵子,看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其中讲到毕飞宇,他从小四处漂泊,从村庄,到县城,到都市,那个地方他都待得不长。当他回到曾经生活的土地上时,他突然停住了,看了很久想了很久,镜头推到他的脸上,他的眼睛里涌上一种酸楚,他就背过身去了。我也被他的伤怀之情触动。
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想没有故乡的人,心是没有生根的,那就像被风吹掉的叶子,离开母亲的孩子一样飘零无助。我想我真是幸运,有像莫言一样深深的乡愁,但是我转而细想,我何尝又不是像毕飞宇一样,四处漂泊呢。
我在爸爸的老家莲花出生,一个满池莲花盛开的地方,在我三岁左右搬走了,打我记事起,我并不记得在那里生活过,但是我的感官和肉体似乎记住了它,我总能想起一些熟悉的画面来。我们搬到了妈妈的出生地兴家,与爸爸村子有近一个小时路程。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又搬回了莲花,在舅爷家暂住了一个学期后,又搬到了三叔所在的县城虎林,一直生活到现在。
你说,我的故乡应该是哪里?
我在莲花生活了三年,在兴家八年,在虎林十八年。但是若是问起我的故乡,我的第一反应总是莲花。哪怕在那里不过两三年的光景,甚至没有记忆,但还是最亲切,就像亲生母亲一般,这时我便有些理解了落叶归根这个意象。
我最近一次回去,是在2018年底哥哥结婚的时候,只待了一天就匆匆返回。坐在通往村子里的客车上,窗外的大山一排排壮汉一样高大得逼仄,一条只有对开车辆通行的盘山道,蜿蜒曲折,我望见了对面的山路,中间卧着的是一片土地,有时是湖,我幻想这要是插双翅膀飞过去岂不是一眨眼功夫,但是客车像一只毛毛虫小心翼翼地蠕动,空荡威严的山区里,这只本巨大的毛毛虫也变得越来越小,成了一个移动的小点,十分钟,二十分钟过去,爬到了对面去,顺着山路一圈一圈地爬行,在我也有些看得疲惫的时候,车子驶进了一片平地,低矮的房屋整齐地抱在一起,车子爬得高了,回头望下来,看到那村庄其实很小很小,一个孤单的孩子一样躺在那,还好群山的怀抱让它如同被母亲保护着。我不禁就产生了怜悯的情绪,那路上奔跑的孩子要去很远的县城念初高中,人们常年待在这里,这辆鸣叫的客车是她们通往大山外的使者,路边站着一些接车的人,接货的人,看热闹的人,里面的人望着外边,外边的人瞅着里头,互相稀奇着。我注意到路边的几户人家,宽敞通亮的大砖房,门前砌的高台,台面上干净整洁,拾级而上,高人一等的感觉。这种清新自然的居住环境比城市里高空中的一格空间美妙多了,然而就是这样,农村再美再舒适,年轻人也依旧奔向那繁华却孤独的异乡都市里,农村没有机会,城市没有自然,鱼和熊掌必然不可兼得。
车子离开每个乡村,我总会为它感伤也被它感染。像看到一个留守的孩童,心疼她的孤独,却又迷恋她纯净的心灵。我的故乡莲花比留守儿童好一些,它相对而言算是个大一些的村庄。一条街把村庄分为两半,不过十分钟,客车也从村头驶出了村尾。而村子深处交错纵横,又是另一番密密麻麻的生活景象。远离村子的东边山脚下,也有一些人家,那里被村里人称为东沟。出了村尾,有一小段路,两旁是平整开阔的庄稼地,几分钟就到了一处有三四层矮楼的地方,地方不大,住的也大部分是村子人,街中间还有个大的原形花坛,很多人会坐在花坛边上等车,围着花坛形成了规矩的局面,引出了四条路来,一条向北通向村子里,一条向南通向兴家村,一条向西通向大桥,一条向东进到楼区里。街边的商店是独立商铺,招牌很大,门面也好看,不像村子里的食杂店都是个人家开的,还能看到里面的炕。村子人叫这里小区,它就像城里的小区一样,那个时候在农村见到二层楼都是稀罕事,这里就成了村子人心中的世外桃源。嘴上说着有啥好的,但若见了有人在那里住,又会立马得到消息谁谁搬到小区了。
我本是个不爱关心世事的人,在虎林生活里十八年,我除了认识家附近的几户邻居外,再往下走一点就不熟悉了。然而在莲花,我真正住过也不过半年光景,莲花的地貌就清晰地呈现在我脑海。所谓故乡,应该不是你住得时间有多久,是那里世代住着你的亲人。
他们在,你的树根才有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给,才不会烂掉。
曾经,那里住着爷爷奶奶,他们去世已经十多年了,如今的村里人也记得他们。他们曾住的房子很破,但那里对我来说是个很温暖的地方。我如今已经没有奶奶家这样的去处,人的生命就变得很单薄。小时候放假,总去奶奶家。奶奶的味道,是她带我串门时路边簌簌的杨树叶味道,是白色泡沫箱子里的冰棍味道,是莲花湖里哈喇的味道,是莲花池亭亭玉立的莲花味道。
我能不怀念莲花吗?我能不把它视为我的故乡吗?
但我又由衷地感到惭愧,我记不清莲花湖开满莲花的样子,有生以来我只去过一次,就是小时候奶奶带我去的那一次,我甚至以为那是个梦境。
村子以莲花命名,也是以此盛名。去往莲花湖的那天,因是莲花盛开的季节,人们结伴而往,队伍甚是庞大,我们走得很慢,像是一场朝圣之旅。快到的时候,我感到那雾气扑面,人们也渐渐不语,我不敢出声,心中装着敬畏。湖边有一凉亭,与莲花应景。莲花真是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立在池中像一个纯洁的仙子。有拿着相机的,那是拍照的人,人们不动声色地走进船里,与它近距离拍照,就匆匆而返,一个接一个,好似与明星合影。奶奶让我也去拍一张,我那会儿还怕得很,拍照,和莲花对我都是稀罕事儿。后来,我把这一行写进了作文里,在那时,这真是一次独特的体验。
莲花在村子里是无处不在。我四年级转学过去,念了一学期,那会赶上春游,跟着学校去了一次景区,又见到了莲花。就在刚进村的路上,路边有一个别致的大门,上面的字我记不清了,颇有景区的感觉。走进去,有假山,有莲花池。地方不大,却也很雅致。不过那的莲花很少,应该只是为了应景,和莲花湖的莲花相比,看得不够尽兴。
除了生长莲花的莲花湖,这里还有一条湖,它也被人们称为莲花湖,它不生莲花,却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它沿着村子底下从上而下流淌,贯穿了整个村子,人们在上面建了莲花大坝。平日不放水的时候,大人和孩子就好去湖边洗衣,玩水,捉鱼和哈喇。夏天,湖区里,没有遮阳处,头顶毒日头,放眼望去,都是人。多走走,就像逛集市一般。人们都从自家巷子里下到湖里来,一一对应着分布在各处,精力足的孩子们出溜来出溜去,回来跟大人说自己看见谁谁了。在这里,人们能待一下午,太阳沉下去了,上头大坝就要放水,人们各自端着洗衣盆搓衣板,泡了水的脚走在沙地上,沾了沙子,卷起裤脚,走回家的功夫,脚就干了,沙子也就得瑟掉了。
有一年,闹了水灾,挨着湖边坡地上的菜园子都被淹了,有几户人家也被殃及了。同时,洪水也带来了厚厚的鱼虾,家家户户都能打捞一桶一桶的鱼。从巷子里走过,都能闻到一股鱼腥味。那年夏天,我们有吃不尽的炸鱼。
2003年离开莲花以后,我与它再见就变得艰难,只有在有事情办的时候才有机会回去一趟。它已经在这些年里一点点变了模样。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路两旁从过去四五家小卖店,几乎都变成了商铺,五花八门,旅店,饭店,烧烤店,麻辣烫店,还有服装店,竟也有手机店,城里有的,它也不差什么了。故乡发展得好了,我高兴又失落。从这片土地上奔跑的孩子有了孩子,孩子的孩子也有了孩子,一代又一代,这片土地已经把最风华正茂的美丽给了前人,轮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给的了,倒换成了受它哺育的人们来改造它。它的眼泪和欢乐所剩无几,而对它深情以往的那些人也代代终老,这片土地最后会剩下什么记忆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虽比不上艾青的家国情怀,但是我也一样深爱这土地,这片生我的土地。也许只有离开的人才会有如此深的想念,离开的人是可怜的,因为想念总会掏空一个人。如今我已经成家,又有了孩子,我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带着他们去那里,和我的下一代,重新寻找并种下这片土地的记忆。
写到这儿,我也就知道,虽然半生漂泊,而我始终没有感到过飘零,那是心里一直有一个最令我温暖的,最让我想念的地方,它就是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