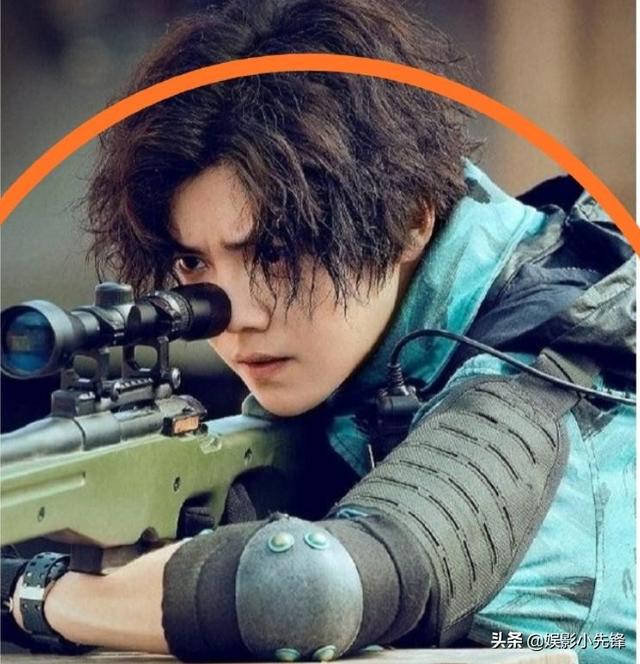多年前,在我研读复杂经济学的时候,有人建议我应该也要研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因为奥地利学派具有与复杂经济学许多相似的地方。然而,我的直觉一直没有让我前去研读。最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斯皮茨纳格尔的《资本的秩序》一书。斯皮茨纳格尔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奥地利迂回投资”理论。但是,我认为在《资本的秩序》中,毋宁说他是全面展示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图景。
斯皮茨纳格尔是一位“末日”投资者。他认为他的方法是运用了中国道家的迂回策略,“输者得之,失者得之”。这就是奥地利学派的投资,一种典型的、反直觉的、经过验证的方法,从有着150年历史的奥地利学派中提炼出来的投资。斯皮茨纳格尔是第一个将路德维希·米塞斯和他的奥地利学派理论浓缩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高效的投资方法的人。他从识别股市崩盘的货币扭曲和非随机性,到蔑视高生产率资产,从而“把奥地利学派从象牙塔带入了投资组合”,形成了“奥地利学派投资法”。
1
对于斯皮茨纳格尔而言,资本是一个过程,或者一个方法、途径,即古代中国所说的“道”。资本具有跨期特征,它的定位和在未来不同时点的优势是核心。时间是资本的生存环境。当用一种新方式思考资本时,必须从新的角度考量时间,当我们这样做时,这就是我们的路径,我们的资本之道。这条路径以非常且有意的迂回绕道而闻名,这就是所谓的“迂回”——“向右走就是为了之后向左走”。
奥地利学派认为人类行为具有不可预测性,个人选择对经济运作具有重要影响。价值具有主观性,企业家的角色以及对资本创造的追求推进了社会发展。很早以前,奥地利学派的先驱者卡尔·门格尔和欧根·庞巴维克就发展了一套关于资本的新思想,即以迂回方式获取更丰厚的结果。他们聪明的传承者路德维希·米塞斯在发扬光大这一学派方面发挥了比别人更大的影响力。到了斯皮茨纳格尔这里,强烈主张不要直接追求利润,而要采用迂回获得利润的方式。
斯皮茨纳格尔十分推崇埃弗里特·克里普。克里普是芝加哥一位资深谷物交易员。斯皮茨纳格尔认为他是一位“大师”,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克里普悖论”。斯皮茨纳格尔从克里普那里形成了自己的投资体系:迂回投资法,即奥地利学派投资法——放弃直接获利的途径,采取较困难和迂回的路径,暂时的亏损是一个中间步骤,是为了将来得到更大的潜在优势。“为了向左,就先朝右走”。
斯皮茨纳格尔自信他的迂回策略吻合军事家和企业家的古老战略。这个策略也是文明的创建者和毁灭者的策略,是我们这个世界发展的逻辑。根据《老子》的说法,做任何事的最佳路径都是相反的,得来自失,有失才有得;胜利并非来自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而是通过一套迂回路径:在当下等待并做好准备,以便能在未来取得更大的优势。在这期间,必须“无为”,即“什么也不做”。也必须“为无为”(“无为而为”),即“通过不作为而达到有作为的目的”。
《老子》论述的是阴阳两极、平衡与失衡的先后和转换的基本过程,每一种情形都蕴含着相对立的情况。“无为”的重点是等待一个客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容忍损失,以换取未来的机会。之所以必须等待,是因为愿意为了后来更大的进步而牺牲这一步。等待的最高形态是为了获得优势。否则,难免“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忍受中间步骤的损失和优势,才能击败那些急于马上获得收益的对手:直接使力会被反作用力击败。
投资者如果要“为无为”,就需要一种坚定的、脱离眼前正在发生的、可见事物的前瞻性,转向即将到来的、现在还无法看见的事物。斯皮茨纳格尔将这样的视角称为“景深”,即能够敏锐感知更久远的未来时间。景深既非长期,也非短期,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所以不必考虑长期或短期。正如克里普悖论,应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时间——跨期,其中包含了一系列“当下”时刻,环环相扣,像一支伟大的乐曲,或者一串珠子。
克里普可以承担许多笔小亏损。他深知,对这类小亏损的不耐烦或不容忍,以及急于快速获利,会造成致命打击。人们总是在这类小亏损面前成为受害者。因此,他先预期到损失,第一次损失是好的,之后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也可以称之为“好的进攻就是拥抱亏损”,付出时间代价,用当下换取未来的优势,这个优势可以让你进行更有效地进攻。这是一种“以败为胜”的策略。根据斯皮茨纳格尔的定义,等待必须先于见机而动。利用他人的急切心理,正是迂回策略的逻辑,这是交易和投资的基本和终极优势。
克里普坚信,学术界的任何东西都在金融市场这个真实而残酷的现实世界里毫无用武之地。克里普认为市场倾向于经历不频繁的大型波动——我们称之为“肥尾”,市场回报的频次分布会出现极端状况——用最简单和最精致的方法复制一篮子期权,是一个不错的操作方法。克里普总是说,“当不需要快速承担损失时,就可以快速盈利了,但是我无法告诉你何时盈利”。对于他而言,小鱼不值一提。
2
斯皮茨纳格尔从针叶树中得到了迂回曲折生长的启示。针叶树早在约3亿年前恐龙诞生之时就已经出现了,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并且被植物界公认为最伟大且长寿的物种。当6500万年前白垩纪晚期,被子植物统治植物界时,针叶类植物很少拥有立锥之地。针叶树的生长速度一般滞后于迅猛生长的被子植物。于是,针叶树聚焦于自身的“资产”,发展出强壮的根和厚实的树皮。这使得它们在资源使用上变得非常有效率,并具有令人吃惊的寿命。对于针叶树来说,生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韧性和毅力,并且最好甚至必须采取迂回式策略:早期缓慢而平稳的发育,为接下来快速而高效的生长打下基础。
针叶树避开肥沃的土壤,撤退到多岩崎岖的地方生长,以此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这就是针叶树为提高生产效率付出的代价。它们为了提高自身的整体生存机会,会在明显的地方将机会直接让给竞争对手,这样它们就能在以后更适时且更有效地繁殖。针叶树显然清楚正面冲突的潜在致命性。这就是大自然采取的一种迂回式跨代发展的路径。这种策略正是针叶树用于对付更具攻击性的被子植物的独特方式:通过直面暂时的失败,牺牲眼前利益,而达到最终的成功。这就是森林的生长逻辑。大自然进步的秘密在于,它的视野之深就像针叶树迂回路线,起初指引自己指向其中一方,以便在未来更轻松地转向另一方。
《孙子兵法》和卡尔·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都认识到,并非所有的战斗都是决定性的,采取迂回策略要好得多,关键在于耐心地获取过程中的优势地位,高效而有目的地实现最终目标。无需战斗就能获得胜利,这就呼应了道家的“无为”和“为无为”,同时也吻合森林生长策略。胜利并非来自对目标的直接追求,而是自己的目标。如果未来有机会实现更大的利益,就愿意在当前付出一定的成本。然而,人性的弱点使得我们倾向于小而即时而非大而久远的回报。华尔街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你现在必须就去做,否则明天就没有同样的机会。这显然是一种偏见。于是,他们更倾向于冒着小概率的巨大风险,迂回式投资反而是不合理的,从不考虑未来反而才是真正的明智。
企业家如果采取了迂回之路,那么可能将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亨利·福特就是一个典范。福特被誉为现代真正的杰出人物之一。福特迂回生产的标志是胭脂河工厂,包括港口、造船厂、炼钢厂、铸造厂、车身制造厂、锯木厂、橡胶加工厂、水泥厂、发电厂和装配厂。迂回生产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用福特的话来说,就是“让资金回到生意中来,满足更多的生产需要,并将部分成本转嫁给购买者”。迂回的悖论是,迂回之路需要大量额外的时间,而在这期间几乎显示不出明显效果,但在后期却能节省大量时间,正如一开始缓慢生长的针叶树,最终会获得加速生长的机会。福特希望赚钱,但不是以消耗生产资本为代价,他懂得如何更加明智地通过跨期投资来获得更大的战略优势。
3
斯皮茨纳格尔将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做为奥地利学派的《老子》。隐藏在这部宏大、扎实、正式研究成果里的是对克里普悖论的简洁归纳,即将《老子》的简洁和优雅通过解决问题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这就是斯皮茨纳格尔的“冯·卡拉扬时刻”。冯·卡拉扬直到50岁以前都没有获得指挥家的声誉,但他最终成为最知名的指挥家。卡拉扬以真正的老子的风格在阿尔卑斯山隐居,进行“安静、专注的学习和冥想”,退出了与他竞争对手的直接冲突,“静静地、自信地等待着”。
在米塞斯的世界里,首先是时间的角色。时间参透了一切:所有的行动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其中总有步骤和“时间片段”,其目标是“消除未来的不安,哪怕只是即将来临的瞬间的未来”。行动是为了缓解我们无法满足的“急躁和等待带来的痛苦”。克服这种自然紧迫感是生产力的关键所在(即迂回生产),“要让生产过程有更多的果实收成,就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负责等待时间的角色”。贯穿米塞斯观察的始终是市场价格的基本不规范,其内在主观性是一种源于人类感知、需要、体验和不耐烦的主观性。这种基本的非决定论导致了“经济学方法”,这就是米塞斯的行为经济学或人类行为科学。米塞斯正确地把迂回的核心说法归功于庞巴维克。“急躁程度”在此即为“时间偏好”,按照米塞斯的看法,是利率的唯一来源——等待和放弃眼前的利润或消费,甚至资本流失,是我们人性中合乎逻辑的一部分。实际上,为了做某些有益的事,我们必须克服人性的一部分。这就是克里普悖论,以最宏大的规模,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语言中进行了正式化和世俗化的描述。
斯皮茨纳格尔自叙曾于1999年加入纳西姆·塔勒布的安皮里卡资本公司。他在2005年离开安皮里卡后,创建了普世资本公司,塔勒布又加入到斯皮茨纳格尔的团队中。斯皮茨纳格尔和塔勒布都喜欢在市场尾部寻找机会,都称自己为“危机猎手”。尾部指的是尾部风险,通常是一些事件的影响尚未完全退去的时候,被忽略的风险。这些风险有时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的形成。
塔勒布在不确定性尤其是“黑天鹅问题”的研究上显著地影响了斯皮茨纳格尔。但是,斯皮茨纳格尔认为,导致市场崩溃的真正黑天鹅问题不是一个不可预见的远距离事件,而是一个可预见的事件,尽管它被认为是遥远的事件。大多数“喜欢波动性”的回报,无论事先还是事后,都是被高估的,即便使用了幂律尾部或其他严格的估值方法。斯皮茨纳格尔并不像塔勒布那样采用杠铃战略,因为它是一种直接的正面攻击。对于他而言,凸性是一种有效(低风险)的工具,用于利用被压抑的迫切交易需求和市场扭曲,这就是迂回策略。凸性指的是,凸性突出的债券在市场利率变动时,要比凸性小的债券涨得更多,而跌得更少。
4
斯皮茨纳格尔认为奥地利学派投资法十分接近价值投资的方法。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思想上,尤其是奥地利学派投资法强调投资过程中进行有意的迂回。斯皮茨纳格尔甚至认为,本杰明·格雷厄姆及其追随者,他们所遵循的理论事实上是奥地利学派的一个远亲:一个在不知不觉中分裂的派系。格雷厄姆的“市场先生”的两极比喻是一种合理的方法,可以回避扭曲陷阱和企业家“想象力缺乏”。格雷厄姆“把有价证券当做一项生意去投资是最聪明的投资”的做法,赋予投资实践一种以前不常见的严谨、逻辑和企业导向,而且表现得具有明显的奥地利学派的风格。也许格雷厄姆最深刻的洞见是避开证券市场阴影,完全专注于企业活动本身:商业和资本。他非常关注作为资本的有形资产,这是一只股票的核心价值所在。他提出了许多量化指标,从债务限制到长期盈利、稳定增长的股息,再到市盈率。
奥地利学派投资和价值投资之间的区别还体现为视野的深度与跨期的长度。后者是耐心地等待很长时间,就像在等待一场遥远的优惠券。前者是耐心地收集更多潜在的优惠券的因素。两者都需要纪律和耐心,但奥地利学派投资关注的是有效的跨期过程而不仅仅是终点。斯皮茨纳格尔发现,格雷厄姆最优秀的学生沃伦·巴菲特曾经通过他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接触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1962年的一封信里,霍华德写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想为非常渴望阅读有关恐慌和类似现象的儿子沃伦要一本《1819年恐慌》。尽管沃伦·巴菲特后来对奥地利学派正统学说的大部分内容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但他的基本投资行为却比他承认的更加紧密地和奥地利学派理论联系在一起。
斯皮茨纳格尔盛赞奥地利学派投资方法的严谨和吸引力在于其原则的直观逻辑:甚至在他测试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他的优势为什么存在。“而对于大多数价值投资者来说,即使他们看到价值投资方法提供的优势,也不理解——通常仅仅依赖于模糊的长期价格会向均值回归这一点。格雷厄姆有句名言,称之为‘我们的业务奥秘之一,对我和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谜’。因此,他们仍然容易被下一个看似有吸引力的投资计划和扭曲的市场环境所淘汰(就连格雷厄姆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末也是如此)。”
奥地利学派投资法,一是依赖米塞斯提出的观点,二是依赖庞巴维克提出的概念。斯皮茨纳格尔本身以尾部对冲和所谓的黑天鹅式投资而闻名。他专注于看跌期权,将看跌期权作为失败投资提供更具流动性的资本,还允许人们在扭曲发生期间对股票进行大量投资。执行米塞斯式的投资策略,是极其雄心勃勃,甚至是大胆的。斯皮茨纳格尔宣称,米塞斯式投资策略每年比股票市场的表现高出两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完全基于市场领域的“小儿科”策略,不仅既打败了一般的专业选股人,也打败了存在极高的生存偏差的对冲基金经理,而且还具有非常低的成本和风险。但是,我认为一般的投资者无法从中直接运用。
至于斯皮茨纳格尔的迂回策略,确实高度吻合价值投资。斯皮茨纳格尔在书中写道,要取得成功,必须看起来十分愚蠢。什么也不用做,坐在那里等待就好了。这正是查理·芒格先生所倡导的。迂回式的奥地利学派的投资目标,不在于现在就找到赚钱的方法,而是为今后更理想的投资机会做好准备。这些同样都可以成为价值投资的准则,是可以直接学习的。事实上,价值投资同样也运用迂回策略。一个显著的案例就是巴菲特投资比亚迪。2008年9月,巴菲特以每股8港元买入2.25亿股比亚迪。一年后,比亚迪股价猛涨至10倍。然而,巴菲特并不为之所动。结果,比亚迪股价又回到原点。此后整整10年,比亚迪的股价从未到达那时的高点。而今,13年时间却超过34倍,回报率仅次于可口可乐。这个经典的案例生动阐释了“为了向左先朝右”的迂回策略,这表明并非仅仅存在于奥地利学派投资法中。
现在,我基本上已经明白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行为经济学。而在行为经济学领域,已经涌现出丹尼尔·卡尼曼及其伟大的思想。除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自主秩序”与自组织具有一些相似性外,整个学派与复杂性科学以及复杂经济学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甚至相去甚远。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风险提示:本文所提到的观点仅代表个人的意见,所涉及标的不作推荐,据此买卖,风险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