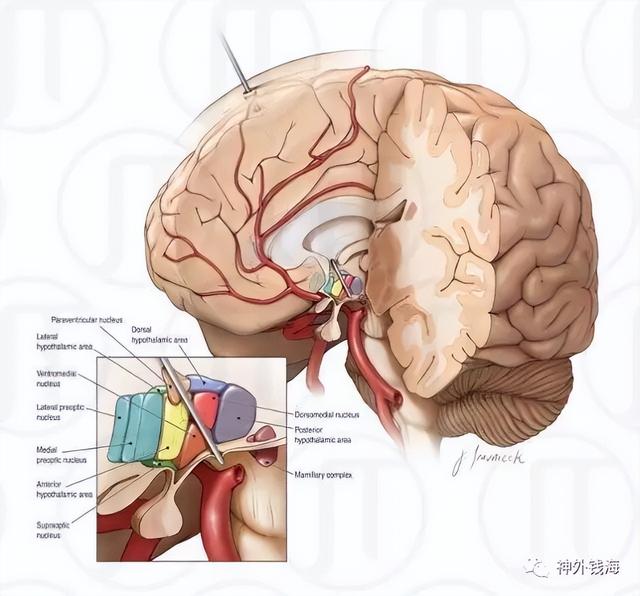岁月静好,珍惜当下

壹 打落袋(台球)
上海混克拉斯(上海小流氓的昵称)的市井运动—康乐球,老咂劲额(很有意思)!是我们上海人发明的!
斯诺克有什么了不起啊!一身马甲,脚高头嘛皮鞋,打扮得跟上海国际饭店咖吧里向的服务生一般,没腔调!再加上斯诺克则球台大是大来,打进一则球,吃力煞脱啦(累坏了)!花式台球呢,我们人称其为落袋,比斯诺克好白相(好玩)。1990年代初的辰光(时候),上海滩上,混克拉斯们顶适意的休闲活动就是看录像、蹦嚓嚓、打落袋。
打落袋之前,我们上海的混克拉斯们白相的是一种叫康乐球的市井运动。棚户区里向、弄堂门口,一帮人围在一起斗赚积(蟋蟀),另一帮人就在打康乐球。
条件不好的辰光,我们上海平民百姓买不起台球设备,创造性地用改良过的象棋棋盘、象棋棋子代替价格高昂的台球桌、台球。旧上海时期小开大户白相得起的高档运动,阿拉上海平民百姓变着法子也能白相。
之所以叫康乐球,是由于老里八早(很早时候)上海闸北康乐路高头的木器店做出的装备顶嗲!

贰 斗赚积
我们上海混克拉斯顶欢喜斗赚积,咂劲!
我们上海的混克拉斯管斗蟋蟀叫“白相赚积”。不管是住棚户,还是居于弄堂,又或是成长于武康路洋房中,欢喜白相赚积的混克拉斯们都会将火光汉大师的蟋蟀经奉若至宝。而自家的一角,就算是鸽子笼、螺蛳壳那般狭小的居住空间,也会堆着好些天落盖、桶鼓盖、天津盆。
夜里一阵凉凉秋风起,我们上海的混克拉斯在屋里向吃完丰美蟹膏,咪掉小半瓶绍兴老酒。此时此刻,弄堂模子在门口叫嚣,“赤佬模子,夜饭切好了哇(晚饭吃好了吗)?切好了嘛,好斗赚积了!勿要缩(不要退缩)!”原先沉醉于珍馐美酒的混克拉斯们一听后,斗赚积的瘾头就上来了,两个眼睛瞪得滚圆发亮,全身血液沸腾,激动得浑身发颤。混克拉斯们立马捧着蟋蟀罐,跟随弄堂模子,火急火燎跑到他屋里。
近年我们上海旧区改造、棚户拆迁,上海的混克拉斯们大多搬至远郊了。如今住在妖尼角落(边边角角)的上海蟋友还是会于每年八月末、九月初相逢于市区屈指可数的一两个花鸟市场,聊聊嘎嘎,再跟在市场里的河南、山东虫贩子交流沟通几句,打听一下近期赚积的行情。

叁 蹦嚓嚓(跳舞)
前些年,西部舞厅,或许是上海混克拉斯们最后几个能蹦嚓嚓出带有上海风情的舞姿的地方之一。
我们上海素来是惯会调情、长于风情的。曾为上海大亨的许文强,就算是死,也要死在百乐门舞厅前,死得浪漫。上海人骨子里就是欢喜声色人生的。生活中,只有黑白,却无七彩斑斓,上海人要闷瑟特啊(憋坏的)!没有丝竹之声,少了天籁之音,见不着绝色舞娘,上海人的精神世界就会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上海人欢喜在五光十色的舞池中翩翩起舞,舞出人生最后的华章。
几年之前,志丹路上的西部舞厅是上海市区仅存不多的几家开门营业的老舞厅之一。铁马舞厅关门之后,白相心仍重的上海老一辈混克拉斯们常聚集于西部舞厅,在旋律不一的拉丁舞曲中挥摆老胳膊老腿,扭动肥臀细腰,在弹簧地板上宣泄着情感,表达着自我。这帮上海男女混克拉斯在坚持着自己的爱好,也在努力维持着上海的一张名片。试想一下,上海混克拉斯的市井生活中若是没有“蹦嚓嚓”,上海滩还能算是上海滩吗?!
耳中回荡着探戈经典舞曲《一步之遥》那充满男女调情意味的勾人旋律,仍然潇洒迷人的上海混克拉斯左手紧握女伴的右手,右手放在女伴的背部,脚步动起来,灵魂飞起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帮上海滩最后的喜欢在舞池中逍遥潇洒的混克拉斯们仍会坚持。

肆 打街机
那些年,上海滩上年纪较轻的混克拉斯们是蛮喜欢到街机房里潇洒人生的。
杨浦东宫街机房里的街机都是些老爷车货色,那里的高手很少,在里面为非作歹、作奸犯科的却不少。当年常看到一头黄毛、红毛的杨浦职校、平凉中学的学生在里面打群架,拗分低年级学生或是对女生口吐轻薄之言。那里当时是比较乱的,可我当年每次去杨浦与红颜小聚之后,就会去那里看一下街机房里的热闹景象,顺便看看杨浦小辈们的江湖纷争。
我曾经苦口婆心地劝说那些不安分守己的杨浦学生,街机房是神圣的地方,不是打架斗殴、拗分偷窃之地。可换回的却是这些无知少年的一句“老棺材(老家伙),嘴巴呗吾关脱(给我闭嘴)!”
如今东宫机房早已不在,而那些曾在此处叱咤风云的杨浦学生们也不知在上海哪处地面上辛苦营生过活!

伍 录像厅
那个时候啊,上海混克拉斯们已对到国泰、沪西、沪北、东宫、大光、胜利、国际等几家老牌影院看电影,兴趣不大了,他们喜欢去录像厅去看。记得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上海市区每个区的文化馆啊,工人俱乐部啊,都有录像厅的。
录像厅的环境嘛,差是差了点,和影院不好比的,但票价便宜啊,放的片子嘛,也比影院的要新、尺度也稍大一些。听闻,那时候上海南市区、虹口区、闸北区几家录像厅还放过那种思想很不健康、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影片,当然,我肯定是不看的。
但上海录像厅的黄金期也不算长。一方面上海混克拉斯们的个人经济情况随着上海经济大腾飞而大幅改善,有钞票自己买录像机甚至是影碟机了;另一方面嘛,上海的那些影院也在那段时间进行了升级换代,观影环境真正上档次了,将注重腔调的上海混克拉斯们又请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