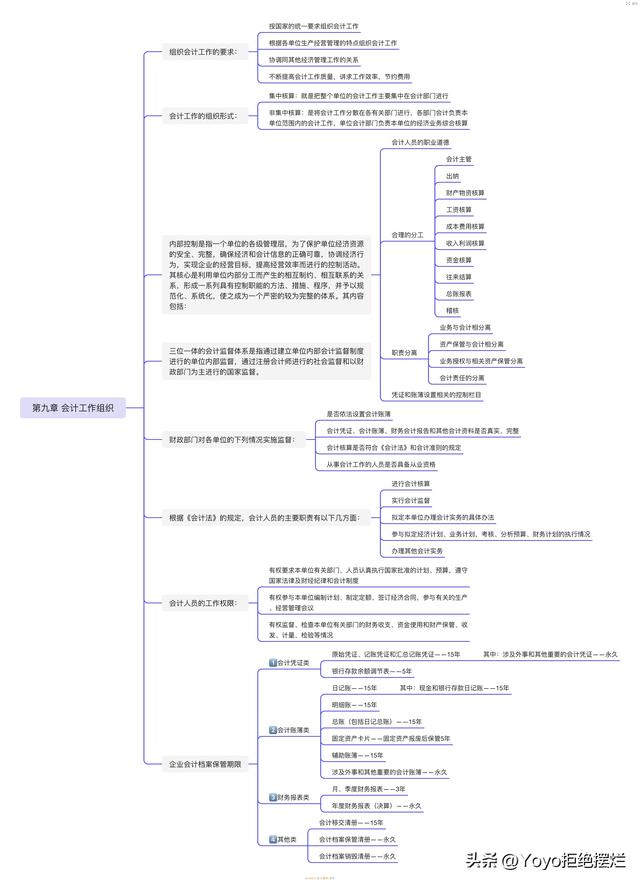作者:范小天
最近,我们福纳影业的策划们推荐了一批毕飞宇的小说给我,我的目光落在了《雨天的棉花糖》上,它是那么熟悉,所有的往事就像在我眼前。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这部我喜欢的却又放手的作品回到了我面前。我突发奇想:能不能由我来把《雨天的棉花糖》拍成电影呢?

毕飞宇 邢虹/摄
一
《雨天的棉花糖》如果就这么在《钟山》上发表出来,会引起评论,却不一定能让当时的同龄作家震撼。
前一阵著名女作家林白发了一张1988年第一期的《钟山》封面,有她的早期小说《去年冬季在街上》,还有史铁生的《原罪· 宿命》,余华的《河边的错误》,高晓声的《老清阿叔》,王干的《父亲》,莫言的《玫瑰玫瑰香气扑鼻》,陈思和的评论《历史与现实的二元对话》,陈白尘的《漂泊年年》……林白不禁感慨:“给范小天看看这个,当年的《钟山》太厉害了!”
20世纪80年代,全国几百家文学刊物,两年评一次小说奖,中篇获奖篇目20部。我当时所在的《钟山》频频获奖。走向1990年代,《钟山》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顶级作家,都把自己最好的小说给《钟山》。仅长篇小说就有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苏童的《米》、朱苏进的《醉太平》、刘恒的《逍遥颂》等。每一期《钟山》只能发表20多万文字,这么多好小说,都舍不得放掉,我们动脑筋,开了一个栏目“三连星”,连载3部长篇小说。同时开辟了一些别的栏目,比如朱伟主持的,陈晓明、戴锦华、张颐武专门谈电影的“十批判书”。再比如,“钟山看好”,专门推出新人。
有一天,王干带了一个翩翩少年到我办公室,说:“他叫毕飞宇。”少年很有力量的样子,目光里让人感觉到他是一定能够成功的人,我的心里咯噔一震,当然,表面上还是我一辈子改不了的既热心热情,又漫不经心的自由任性的样子。毕飞宇给了我一部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小说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当时很多名家的作品,甚至超过了一些名家的代表作。我在这里必须引用一下余华当年给程永新的信:“我一直希望有这样一本小说集,一本极端主义的小说集。中国现在所有高质量的小说集似乎都照顾到各个方面,连题材也照顾。我觉得你编的这部将会不一样,你这部不会去考虑所谓客观全面地展示当代小说的创作,而应该是显示出一种力量,异端的力量。”《雨天的棉花糖》如果就这么在《钟山》上发表出来,会引起评论,却不一定能让当时的同龄作家震撼。
《雨天的棉花糖》在北京一个刊物上发了头条,毕飞宇拿来给我看,我替他高兴,同时还是希望他能“显示出一种力量,异端的力量”。
二
在我眼里,飞宇也是“一根筋”的,他对创作的热爱、执着让我感动。
毕飞宇曾给我的作品写过一篇序,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小天的性格差不多集中体现在他的雄辩上。小天的脑子特别灵光,再加上自负,张口闭口的时候自然就多了一份剑气……”飞宇说我的小说不像我的辩论,说我的小说反而是“一根筋”的,“热烈,忧伤,愤懑,偏执,认死理……但是他“喜欢这根筋,这根筋逼着我反躬自问:你怎么会过得这么心平气和、心安理得?你难道从来没有发现你周围的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在我眼里,飞宇也是“一根筋”的,他对创作的热爱、执着让我感动。带着这跟筋,他创作了很多作品,他的《祖宗》让我眼睛一亮。“太祖母超越了生命意义静立在时间的远方。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落差流荡在她生命的正面和背面。” 冷峻而神秘。近百岁的太祖母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家族对权利的争夺和可悲,让我们看到了民族河流几千年的悲怆和无奈。
很多很多年以后,毕飞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兄弟我最爽的一次写作是写《祖宗》,晚上上手,天亮竣工。”我感受到他那种铆足了劲写作的姿态和对文字的热爱,这是“有力量的一根筋”。我对毕飞宇说:“你能写出来”。很多年以后,毕飞宇表示他听到这句话“顿时就觉得曙光在前头,后背上竖起了鸡皮疙瘩,对于一个除了激情就一无所有的文学青年来说,还有哪句话比‘你能写出来’更令人振奋、更令人欢欣鼓舞的呢?”他从这句话中“得到了力量,从而坚定了自己的方向。”
三
毕飞宇骨子里是现实主义作家。
我决定给毕飞宇上“钟山看好”,同时发4个短篇。我带着“少年”毕飞宇到我们共同的好朋友费振钟家里,我请费振钟给毕飞宇的小说写评论。费振钟说:“我和飞宇是老乡,太熟了,我就不写了。”费振钟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和评论家,我和费振钟是非常好的朋友,没想到我竟然碰了钉子。那些年,我很少碰这样的钉子。在我的记忆里,我是很尊重费振钟的,我们都称30多岁的费振钟为“费老”。十多年以后,毕飞宇告诉我,我当时说了一句话:“你不写,以后会后悔的。”现在想来,我这句话蛮无趣的。一个好的评论家,并不一定要写每一个朋友或者每一个优秀作家的评论,更不需要通过写新人的评论来证明自己是伯乐,眼光怎么怎么好。从另一角度说,我当时自信明显不够,想通过“发现青年才俊”来证明自己。我今天能这么想,看来我在岁月流逝中慢慢成长了。
我认为,毕飞宇骨子里是现实主义作家,在尝试其他手法之后,再回去写现实主义作品,也许会表达得更好,也许会更深刻。比如写过《河边的错误》的余华,后来写的《兄弟》,我就非常喜欢。我始终认为,一个杰出作家要诞生,作品里一定要有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东西。先锋小说也好,现实主义也罢,你总是要创造,总是要直击读者心脏。
过了不久,张艺谋的策划、编剧王斌给我打电话,希望我给张艺谋推荐年轻的编剧。我推荐了毕飞宇,告诉他“钟山看好”上有毕飞宇的4个短篇,建议他和张艺谋都看看。他们很快就看中了毕飞宇,于是有了他们合作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四
我对他的小说有一种执念,希望能由我拍成电视剧或者电影
我对飞宇的小说有一种执念,希望能由我拍成电视剧或者电影。为了这事,我两次和飞宇喝醉,我可不是酒鬼,五年八年也不会喝醉一次。可是,我的梦想至今没有实现。
1990年代初,杨亚洲到南京来找我,想拍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我找到飞宇谈版权,飞宇说由你来定。我记得当时提出了一个很低的价格,还让飞宇写两稿剧本,飞宇爽快答应了。我能感受到他那种可以和朋友跨刀上战场的情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能够和飞宇、杨导演合作成功,还是挺遗憾的。
根据毕飞宇的小说《青衣》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是康红雷和陈枰执导、徐帆主演的,拿到了“飞天奖”最佳女主角奖。我一直想把毕飞宇的《青衣》拍成电影,这部作品也是姜文和顾长卫都想拍的。我曾经和徐静蕾、梅婷都谈过,希望她们能够出演。她们俩都很喜欢飞宇这部小说。我和飞宇联系《青衣》版权的时候,得知梅婷已经签走了,我只好又和梅婷联系,我们愿意作为合作者参与投资电影《青衣》。2017年,法国文化部授予《青衣》的作者毕飞宇“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这不仅是对飞宇文学成就的认可,也是对他在中法文化交流上作出贡献的表彰。
最近,我们福纳影业的策划们推荐了一批毕飞宇的小说给我,我的目光落在了《雨天的棉花糖》上,它是那么熟悉,所有的往事就像在我眼前。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这部我喜欢的却又放手的作品回到了我面前。我这个天生的捣乱分子突发奇想:能不能由我来把《雨天的棉花糖》拍成电影呢?
(作者为导演、编剧、作家,曾任《钟山》杂志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