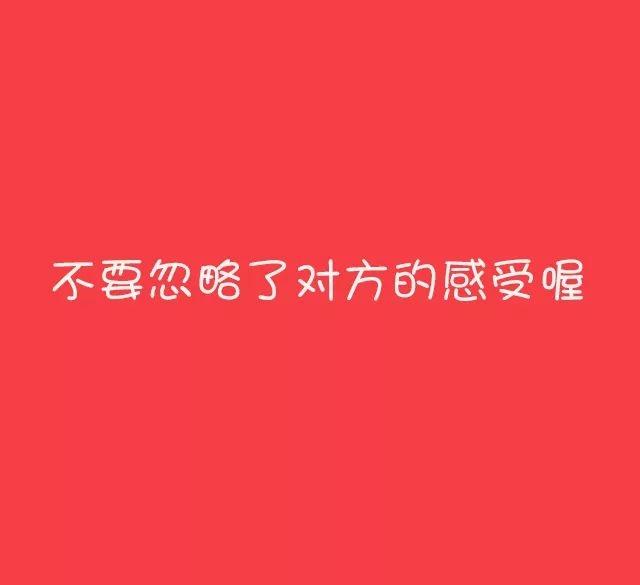演员张国强心里有块禁地,他很避讳触碰,它的名字叫做腾冲,他曾在这里待了180天,完成了《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拍摄,但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地方却总让他魂牵梦萦。
今年5月初的一天,张国强决定再次踏入腾冲,他订了很早的一班飞机,一路上都在往窗外看,下了飞机之后,心就开始颤抖。到了腾冲,他买了四箱白酒去国殇墓园和革命烈士陵园拜祭。
张国强在《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饰演迷龙,一个不想打仗,一心想回老家的东北兵。作为一个演员,他没有想过一部戏,在戏外能对他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他说,直至今天,他也一直在维护《我的团长我的团》《士兵突击》给他带来的荣誉。

以下为他的自述:

到腾冲的那天早上,天空一直细雨濛濛的,我买了四箱白酒,一箱12瓶,共48瓶,都是当地的老酒,我觉得这样更能代表(我的心意),一直往国殇墓园和革命烈士陵园走。当地的一些影迷朋友听说了之后,还特意跑过来在后面搭手帮我抬着。一路上,我就一边洒一边喝,这是兰晓龙(《我的团长我的团》编剧)告诉我的一个方法,喝一小口,洒一些,那真是遍山遍野的酒香啊。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十几分钟吧,蓝天就出来了,阳光透过国殇墓林山上的树木射进来。
你就很难形容当时的心情,就感觉眼前的一切和当年拍戏的那些记忆瞬间都混杂在了一起。一方面,很沉重,你就看国殇墓园那几千块墓碑上面的名字,写着二等兵、下等兵、上等兵、19岁、哪哪的人,你就完全不行了,这段历史太让人难过了。另一方面,还是怀念,想起之前和兄弟们一起在这里拍戏的日子,你就觉得当年的大家怎么都这么好。
《我的团长我的团》是《士兵突击》之后,原班人马拍的一部戏,记得我刚进剧组的时候,就被惊到了。下了车,一进宾馆,走廊里贴的满满的都是抗战时期的照片,因为导演要让演员沉浸到那个情境中,那时候的创作氛围很浓,大家伙一门心思全在这个戏里面。
当时我们拍戏的日常大概是,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坐大巴车出发,因为我们住的宾馆到外景地,要接近两个小时车程,我们所有演员早上起来昏昏沉沉地到现场,换好衣服、造型结束,就开始往身上撒土。我们当时,做到哪种程度呢,就是你脖子上的纹路里面都是油泥,即便打仗的间隙,到村里了,脸白了,但是脖子上依然是黑的。因为那个年代,战士们怎么可能老是洗澡呢?而且我们这是一个在假团长龙文章的带领下,临时凑起来的炮灰团,它的状态就应该这样。

演这部戏,我们大部分演员都只有一套戏服,也尽量保持不洗,后来大家伙都特别习惯了,就觉得那个衣服也是有灵魂的,就像街上的乞丐一样,他可能就是那套衣服,生满了虱子,然后臭不可闻,但穿上,我们就变成戏中人了,就那么服帖。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是,怕不接戏,因为它已经在这了,你一沾水的话就又完了,把这个地方洗掉了,下一场,观众会觉得,唉,它这有个血点怎么没有了。
我始终觉得当时剧组的创作氛围,演员的创作态度,是现在很多戏不可比的,不只是我,你找任何演员,问这样的话,他可能都会这么说,那真是深入角色骨髓里的创作。当时,我就记得大家伙儿的剧本,台词上都标上发音,什么上扬、下滑什么的,因为我们这个剧的角色都是用方言。
你看(王)大治要倒川口、李晨要倒川口、张译是北京话,还要学英语,范雷是广东话,我是东北话,段奕宏在里面什么方言都会说一点,因为语言一丰富,地域性的特点一下子都出来了,就会让人们印象特别深刻。有的时候方言是给演员加分的,但你真是要下工夫去练,要私下做足了功课。现在哪有几个人那么做功课啊?我不是吐槽年轻演员,会有人那么去做功课吗?太不可能了,不敢想象了,现在就赶紧拍完这个戏,中间接好多活动,然后揣着钱就走了,赶下一个戏了,哪会这样创作啊?

这次到腾冲,我谁也没告诉,是偷偷过去的,我订了一家酒店,是当年我们拍戏,经常去健身的一家酒店。他们派了一辆别克车来接我们这些住客,一位女士在下面装行李的时候,就问我“你是不是那个演员张国强”,我说“我是”,她说“哎呀,我的天呢,我太喜欢《我的团长我的团》了”。我们一路上就在聊,她说:“你知道吗?我就是因为‘团长’这部戏,决定一定要来腾冲看看”。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的团长我的团》给很多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到现在还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真实”。
首先是角色真实,“团长”里面的角色都太丰满了。就比如我饰演的这个角色迷龙,他是一个军人,但他就不想打仗,整天就想着回家,东北人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但他也特别能孤注一掷,把所有东西故意输给别人,就跟着去了缅甸,因为你不打不行啊,哪个是你家啊?你家可能都没了,你回什么家啊。这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不是所谓的神一样的人物。

我们拍“团长”的时候,永远都是龟缩在里面,端起枪,打完之后就换弹夹,因为没有打不完子弹的枪。你看现在很多战争戏,角色端个机枪,露出三分之二的身体在那儿扫射,开玩笑吗?那不是傻子吗?那不让人当活靶子?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演员自己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导演的问题。你在干吗?你看监视器时在干吗?
编剧兰晓龙也是有情怀的人,兰晓龙写本子,一年一个完整的大剧本都不一定能完成,他是真的全身心地在创作。现在哪有几个编剧那么创作了,某些大编剧们找很多学生当枪手,你写这块,他写这块,然后署名是我们的大编剧。关在房间里面,一两天就能写出一集剧本,东搬一块,西拿过来一块,堆砌成了一个作品。在一个作品里面,能看到无数个作品的影子,那是创作吗?那不就是抄袭吗?
角色不分地域、不分种群,都说着同样的语言,某一个人物的对话,你在另外一个戏中也能看到,那种陈旧的语言,老套路的对白,简直太恶心了。一次拍戏,我就拎出一段词说,这段戏,咱们写的是当代社会,但我要把它放到民国时候也能用,把它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能用,但是它不可以这样通用。
很多人在创作上就是这样,他不愿意动脑筋,就是东抄西抄,他写不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就是为了骗俩钱,就为了养家糊口。正因为我们这些兄弟们是真的有情怀的人,所以才造就了这样一个经典的作品,这些年,我碰到无数的影迷,老中青都有,都说“我很喜欢这个戏”,你能让他们有这样的印象,我真的太幸福了。

我现在看到一些老兵的视频还是会很难受,你就想当时的年轻人,十八、十九岁,有的是学生,就放下书本,放下笔,拿起枪,这是什么样的家国情怀?你想想就会很感动。站在烈士陵园,我一度觉得我们是魂魄相连的,因为大家伙都有着一颗激情澎湃、沸腾的心,即便我们是创作者,不是军人,但是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真的会穿上军装,拿起枪来去战斗。
演员是不是把角色塑造得深入骨髓,真的能看出来,包括现在一些军旅题材塑造的军人,离那种真正军人的状态还是差得挺远的,扮演一个军人它不是穿上军装,戴上墨镜,配上枪支这么简单,那只是帅。像不像,你得看他的精神面貌,得看他的眼睛,他整个轮廓的状态,他的精气神。
我们这个行业这几年有不少滑稽事,比如拍一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戏,突然出现一个矿泉水瓶子,娃哈哈;演一个古装戏,一条牛仔裤出来了,或者格格跳舞,远处宫廷门外面停着一辆面包车,导演也不看,现场道具也不盯着,都稀里糊涂的,所有人都在边上玩手机,你说你看见这样的情况,你不说吗?你得对得起你的创作良心,不能眼看着他穿帮。
当然,很多事情是咱们无力改变的,但我们可以说出来,然后发出来,去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它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不能这样创作下去了。
当然一个特定的时期,投资方也许认为只要搞定一个“流量”,就行了,其他的不重要,但粉丝可以是假的。谁也别吹牛说自己是“流量之王”,一个网剧你说你有几百亿的点击量,中国才有多少人啊?有没有流量,你上电影院试试就知道了,全折,全傻,你的几千万粉丝呢?
不过,从去年开始,圈子里也经历了一些变化,一直到今天,这个圈子里似乎也在进行一种洗牌,现在戏越来越少,很多演员都是,包括我也是。以前很多人投几个亿拍个电视剧的,现在也没有了,大家伙也都消停了,老实了。我们还是回归到创作上面来吧,不要拿着很高的钱,贡献出很低级的表演。
今年是“团长”播出十周年,这些年,也一直有人讨论,要不要把“团长”的下半部分拍出来,我觉得这个成行很困难,你要不是原班人马,它就不成立,而且我们这群演员也都四、五十岁了。到今天来说,它已经是经典了,哪怕它有一些小的瑕疵,就放在那儿吧,别去破坏它了。
对于迷龙,我这些年也是一直心心念念,电视剧里没拍到 “迷龙之死”,所以,那天在一个朗诵活动上,我就特意挑选了这一段(朗诵),算是给迷龙一个结局了吧。最后,还是向对咱们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士们,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我爱《我的团长我的团》,这是我最想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