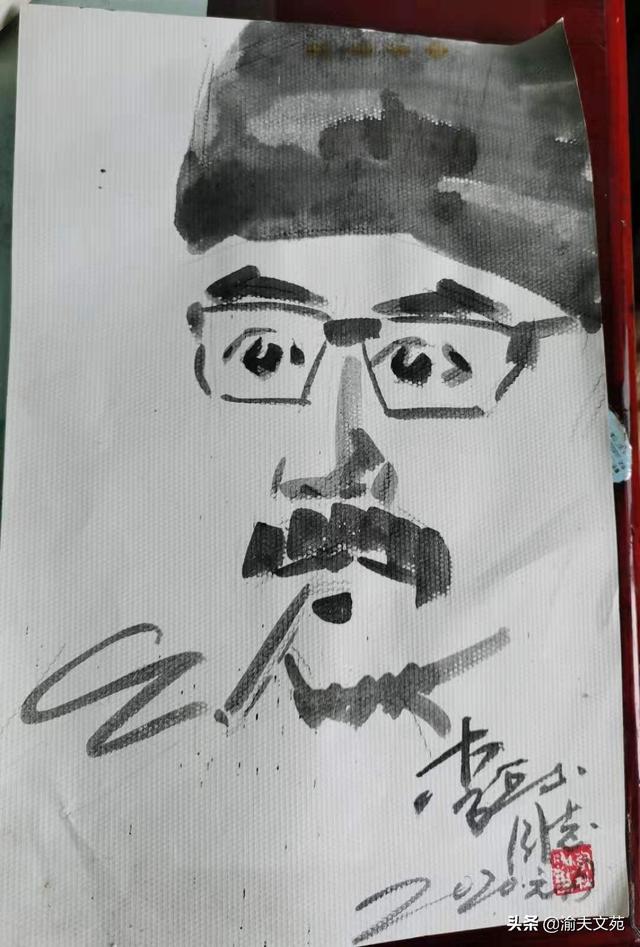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农历癸丑年),太平军北伐部队于10月26日抵达距沧州七十华里的泊头镇,在这里收集到大量船只,水陆大军沿大运河一路浩荡向北,直指离北京仅仅240华里的沧州城。
时任沧州知州沈如潮,字月海,浙江桐乡县人,嘉庆年庚午举人,道光二十九年任治。当太平军横扫江南打下南京的消息传到几千里外的沧州,沈如潮凭直觉唀出危险的气息,开始囤积火药加固城防招募乡勇,日夜加紧训练城防部队。沧州自古民风剽悍,有尚武传统,在乡绅捐资帮助下沈如潮共招募到回汉各族乡勇3000余人。

清朝沧州州县官员

沧州府衙旧址

入秋,太平军北伐部队由山西进入河北,经献县、泊头、南皮,意图沧州。城防守尉德成派出探马侦查,几次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太平军只有三四千人(估计只看见先头部队,实际太平军北伐部队由山西进入河北时总数已达30000人左右)。错误情报促使沈如潮最后决定带领驻沧满营500披甲兵,及3000多水陆乡勇在城南五里大运河一处叫“红孩口”的地方迎敌决战。
大运河就像一条巨龙蜿蜒北上,流传着很多故事,“红孩口”就是之一。
距南城门五华里,现在大运河湾公园的运河大弯东北角有一段几十米长的石砌堤坝,这里就是沧州人所称的红孩口。为什么会有如此奇特的名称呢?原来,早些年在沧州流传着一个传奇般的传说。
有一年汛期,大运河在这里决口。正值午夜时分,情况万分危急,众人不知所措。夜色中突现一位银发道士,站在决口旁对众人说,此处决口人力难以抗拒,诸位不必着急,待五更时分会有一身穿红衣骑着毛驴的孩童来到这里,他会降服水妖。说罢,银发道士消失在夜幕中。
人们焦急地等待着。到了五更时分,人们听见由远而近的铜铃声。顺着铃声望去,晨曦中果见一骑驴的红衣孩童沿河岸奔来。到了决口处,骑驴孩童从驴背上跃入水中,顿时河水不再涌流。接着,决口处的堤坝向上隆起,很快堵住了决口,这才使全城百姓免遭水灾之苦。自此,这决口处便被称为红孩口。


沧州大运河湾公园附近“红孩口”
知州沈如潮与沧城守尉德成之所以决定选择这里迎敌,从地形看,运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大的急弯,战船走到这里必定减缓速度,当船队转过弯道,前队暴露在清军火力下时,后队还在弯道外面,船上火器是支援不到前面部队的。另外,沿着运河东岸道路这里有一个较大的坡路,防守方正好居高临下对陆路敌人进行攻击。此地距南城门5华里,如果不敌战败,还有一缓冲空间撤回城内。
史载,沧州城当夜出现异兆,丙寅时(凌晨3-5点),空中有不明白色环状毒雾压城。毒雾时隐时现,缓缓移动。少顷,林鸟多坠地而亡。
丁卯(日出时分)运河两岸大雾弥漫,太平军于浓雾中沿运河水陆并进,剑指沧州。清军于城南五里之红孩口列阵待敌。城北驻防北堡干总刘世录亦来助战。探马疾驰来报,敌军已至五里外捷地镇!顷刻间,浓雾中运河上已隐约望见太平军密密麻麻的旗帜,待战船徐徐转过河湾,一声号令,清军火枪大炮首先开火,枪炮环施震耳欲聋。一时间,河道内外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群鸟惊飞。深秋大运河早晨的宁静瞬间被枪炮声打得稀碎……
太平军一路走来势如破竹,万万没想到在此遭遇如此猛烈抵抗,猝不及防间,在强大的火力面前,前队伤亡无算,阵脚大乱,很多人中弹坠落到运河里。在东岸与迎面战船的火力夹击下太平军战船纷纷靠到西岸。兵士纷纷跳船逃到岸上。清军和乡勇趁此时机,水陆并进一拥而上,大刀剁,长矛刺,瞬间给太平军造成很大伤亡。

其实,史料记载,太平军的装备非常精良,除了大量装备火枪火炮,手中兵器都是一丈多长的长矛,腰间再配挎短刀,交战时远刺近砍,战斗力很强。只因沧州明清以来遍布拳社武馆,沧州不仅是清代河北武状元最多的地区,也是全国武状元最多的地级市。除了清军这500披甲满族兵勇,这三千多人的汉回乡勇大多是自小习武的练家子,别的不说就是这力量及机敏矫捷就比一般人强的太多。沧州武者好使长柄大刀(亦称双手带)和长达三米的大枪,这两种武器非常适合实战。想必此战中肯定发挥不小作用。加上沧州知州沈如潮重视火器的使用,弹药准备充足。一时间,太平军前队阵脚大乱,招架不住渐渐不支……

危急时刻,北伐军总制肖再人自告奋勇带领少数士卒冲到清军火药车旁,手起刀落砍翻数十人,将火药车点燃。几声巨响中,火药车与车上的弹药一起化为灰烬。太平军士气大振。没了火器的支持,清军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渐渐不支,几个回合来往混战中,清军这边,北堡千总刘世录及练长宋广泰等皆阵亡,驾驶战船在河里率水军乡勇交战的从九品团练长张蔚亭、监生尹化行先后中炮落水而亡。这时,太平军后面大队人马陆续赶来投入战斗。传说,红孩口之战中,太平军北伐部队前锋指挥“开山王”,身先士卒亲自上阵,左手握黄旗,右手执刀,如猿猴般矫健异常,一路纵腾跳跃,奋勇向前把清军杀得大败,面对源源不断涌来,人数远远超出预期的太平军,乡勇首先不支先自退败,旗兵死伤殆尽几乎全军阵亡。

红孩口还在激战时,太平军分兵去攻沧州城西北二门,并用火攻小南门。沈如潮、德成急归守城时,太平军已焚毁小南门破城而入…….
有一首五言律诗,描绘了太平军进军沧州的壮烈景观:“几番如脱兔,一霎聚飞蝗,草木瀛州乱,烟麝渤海荒,戊车奔郡邑,战舰蜀沧浪,白刃连营密,红巾罩首狂。
攻进城以后,太平军遇到城里的清军乡勇百姓乡绅的激烈抵抗,巷战中损失惨重。经过激烈战斗最后终于占领沧州全城。知州沈如潮回衙护印被抓获后杀死、城防守尉德成在州衙前街巷战中受伤坠马掉入荷花池战死。

据史料栽,太平军初入城不甚杀戮,后检查人数发现其精锐在红孩口及城内被杀伤四干人,始痛恨,下令屠城,一时间沧州城血流成河,尸横遍地,火光冲天。据事后统计,屠杀及交战中致官兵满汉回百姓共死万余人,其中大多数是死于城内外屠杀的普通百姓和官员眷属。特别是满族人,只要被发现,不管老幼不留活口。因为汉族妇女大多缠足满族妇女不缠足,民间传说,很多大脚满族妇女因此遇害。“多幸世事多出城避去者,不然几乎无遗矣。”
同治元年编撰的《沧城殉难录》及沧州地方志对太平军攻陷沧州城均有详细记载:“德成巷战死,如潮骂贼死。余文武官及绅民巷战杀贼死甚众,贼叹日使郡县皆如沧州官民拼死相御我等焉能至此。”
《沧城殉难录》记录还原了当时部分惨烈场景:“马宽成率家人巷战,凡杀十二贼,贼火其室,焚死全家殉难,子登云手刃五贼死尤烈。”“潘立忠殊死战,被贼砍为两段。”“杨炳南贼索草料不与大骂,被焚死。”“阎大利立水中骂贼,中铳死。“刘凤巢,字在梧,候选州同,慷慨好义,闻贼警日近,捐资练勇,贼至督众力战,复登屋以旗磨众使前及败,反舍方收合余烬,思再战,贼突入其室,搜得练勇册,贼怒缚于庭柱,先刺目断臂,复碎磔之,至死骂不绝口。又杀其侄锡荣及其妻侄女并仆温等十一人,惟其子锡恩为女仆张氏易敝衣给为已子获免。”
文中所提刘凤巢,就是当时著名沧州回族富绅刘凤舞的兄弟。
关于沧州癸丑之难,到底有多少人死于太平天国北伐军的交战与屠城,有文献详细记载,太平军走后,官府善后时,将男女无名尸体2864具运往北门外(老市一中一带),男女各埋一坟,男名“忠义"墓,女名“节烈”墓。俗称两个“肉丘坟”。新任知州奏报朝廷为清阵亡将领和士绅2900余人新修祠堂。事件第二年,咸丰四年三月谕:“桂良奏查明驻防官兵妇女殉难请恤一折。上年贼陷沧州城,守尉德成力战阵亡,业已降旨优恤。其防御四员、骁骑校四员,副骁骑校八员,均同德成力战阵亡,德成之妻同时殉节。又披甲兵四百十名、养育兵十名、闲散兵三百九十名、殉难妇女一干八百三十七口、幼丁四百八十名,或临阵捐躯,或杀身全节,义烈之气,可泣鬼神。妇孺何辜,罹兹凶惨,满州旗仆,深明大义,临难孝忠,毅然不夺。嘉叹之余,尤深怜悯,均著加恩,交部从优议恤,以奖忠烈。其现存兵丁,仍著照支给钱粮,妥为安置。”这是城防部队官兵与眷属随仆等的死亡人数共计4000余人。加上前面2864具无名尸体,就有八千余人。张蔚亭等落水阵亡清军乡勇的尸体第二年春天才在运河湾红孩口原地打捞上来。另外,还有亡者亲属自行收殓的亲属尸体,死难者达一万余人还是比较可信的。如果不是很多人提前出城逃避战火,相信还会有更多人遇难。
据沧州老人们说,新华路西北角沧州迎宾馆这个地方,解放前有座香火大庙,庙内供着一排排写有职位姓名的木质牌位,就是祭祀当年死于战火的官吏乡绅的“癸丑之难”祠堂。在七十年代大化建成以前,沧州北门外几无住家,碱地茫茫荒草萋萋间遍地可见累累白骨。
沧州之战后,北伐军挥师北上准备攻打天津,受到沧州屠城影响,沿途官民惊恐万状,静海知县江安澜竟然吓得自尽身亡。天津保卫战中,官、兵、民为了活命殊死抵抗。据说最后连监狱的犯人都投入守城御敌的战斗,因此在天津独流镇大战中北伐军遭遇重创。严冬来临太平军后援不至,加上沧州屠城后百姓忌惮远之,后勤补给严重短缺。不得不步步向南败退,一直到沧州东光县连镇,被清军围困,最后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