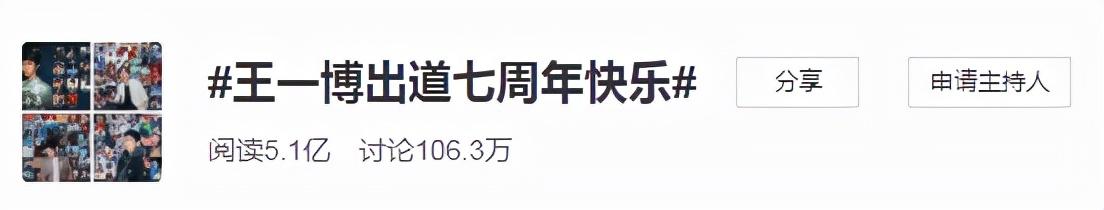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孙雯

王朔出新书了——过去一周,这是文学界最热门的消息。蛰伏15年,王朔以一部《起初·纪年》宣告复出。
8月12日上午10点,《起初·纪年》开启网上预售。仅过了两个多小时,出版方新经典库房里未被分发的书已经被分销商全部抢光。与此同时,关于这本书的讨论在网上开启——书评人、大V、网友……无论已读还是未读的读者,都在讨论这部书,以及这一次出场的王朔。
翻书偶得
《起初》为四卷本系列小说,分为《鱼甜》《竹书》《绝地天通》《纪年》。作为最后一卷的《纪年》,最先出现在读者面前,王朔在序言中说——“最后完成这卷即本书,文字最顺,阅读体验最好,而前数卷趣味、用典、用辞则多有可商榷。同意编辑意见,应该把最好、无歧义部分优先提供给读者。”
《纪年》的故事,用王朔自己的话来说,是“取材于《资治通鉴》《汉书》《史记》所载汉武旧事”。
书中第一段,王朔这样写——
起初,我六年,匈奴左骨都侯呼衍朵尼驮着紫貂皮、精炼羊奶酥酪和河磨玉来访,自上谷入境,王恢在红山口岸接他,护送他到长安,安排他在国宾馆住下,来找我,跟我说:姐夫问你好。我说什么姐夫?
“我”是汉武帝,也是书中的主人公。
“国宾馆”这样富有穿越感的字句,在之后的叙述中频频出现,比如:“成活率”、“公主班”、“香型”、“人体工程学”、“我署对匈工作可分中行老师入匈前和中行老师入匈后”……读起来,非常王朔。

《起初·纪年》
作者: 王朔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品方: 新经典文化
虽说以历史为骨架,但《纪年》不是一部历史小说。本书的编辑在一则长文中给出自己的观点:王朔也以历史为参考、吃透了不少古书,书中枝蔓庞杂,天文、地理、气象、医学、物理学、数学,包罗万象。从中国传统小说演变来看,它所接续的是《三国》《西游》一路,取一点历史的因由,讲的则是全新的故事,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这脉络中的一环。书中的汉武帝,从北征匈奴时的踌躇满志,到独居甘泉宫的垂垂老矣;从试图混一四海的万丈豪情,到酿成巫蛊之祸后的满怀悔恨。凡有所得,皆如流沙逝于掌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起初》也是王朔对自己数十年创作历程和人生的总结和交待,是一部关于人自身的史诗。
这一点,王朔的序言也有解释:“前人文学作品已提供足够故事性,除了致敬还是致敬,再生人家文本也无非于骨架间贴一些皮肉,所谓借一步说话,说的什么呢?人情世故,叫读书笔记、乱翻书偶得也成。”
最长脱口秀
细读《纪年》的自序,可以发现王朔交待了这部小说的诸多秘密,形如“聊天体”、新北京话口语、外地方语、从音从俗不从字、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同时,这则序言,也是潜藏着诸多网上面对这部新作诸多评议的答案。
王朔为什么会选择汉武帝的故事,他说“无他”,“只是碰巧对他这一朝几个人知道得更早”。
其实,与很多人的成长经历无二,王朔在很小的时候,自然也是不知道汉武帝是谁之前,就对“灌夫骂座”、“金屋藏娇”这样的故事有印象,“大概小时候家里有本前后汉故事集,至今书中灌夫揪人耳朵灌酒黑白插图尤在眼前,当然那时对这样的故事很不满意,喝醉闹酒炸为什么写在书里?金屋藏娇有什么意义呀?”
除此之外,他还有“另一个不好意思的原因”:“我幼时其实是个军迷或叫武人崇拜者,李广李陵爷儿俩悲剧性命运对我有一点刺激,直到成年无处安放,和我熟知的大英雄套路完全不同,初衷有相当成分意图借汉武朝军事活动把本人军迷时代攒下来的小爱好、小见识发挥一下,过过瘾。”
编剧史航说《纪年》就像王朔说的一场漫长的脱口秀——“从头到尾却没有现场观众;但他又像立起了密密麻麻的无数面哈哈镜,每个人都可以梳头照镜子,找到和自己有关的印证,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种掰手腕的乐趣。”
将小说写成一场以“我”——也就是汉武帝领衔的脱口秀,王朔有自己的打算。
在他看来,如《史记》《通鉴》这样的史家名作一般认为也具有相当文学性,“《通鉴》几乎肯定借取了小说、传奇,反正一展开文学性自动就来了就对了。——故皆有将历史戏剧化倾向。而我就个人偏好而言并不喜欢故事过分戏剧性,这会增加叙事负担。从技术上说,而叙事一向是我弱项,为避叙事常以对话代叙事即所谓‘聊天体’,在本书中亦如是。”
从“我”到他
之所以用“起初,我六年”这样的第一人称,王朔想“规避”一点历史体裁的麻烦:“细节考证能累死谁,全知等于难为自己,故取惯常所用第一人称,所见限于一己之侧,能少交待少交待,是不得已。”
第一批拿到书的读者,也已发现,王朔写着写着,由第一人称转为第三人称,缘由在于——
没想到历史景观自有其深远和无垠,一旦进入有特别大的身不由己,有些视角不容遮蔽,走着走着就在故事之外上千年,不留意间已转入第三人称叙事,几十万字岔出去回不来。有些人物所行骇人,心机莫测,远超常人所想所能驾驭,亦为第一人称天然具有同情之理解所不容,故在很多篇幅陆续出现第一、第三人称混用章节,乃至最后写丢了第一人称,通篇以第三人称尬然终了。
这一次,王朔还是那个“拿口语所谓新北京话写作的作者”——检查文字也须拿口语来回溜,没磕啵儿,才觉得通顺。
当然,“写出二里地发现口语不够使”,所以,熟悉王朔的读者,这次可能会读到很多新词。比如,他将老实巴交、烂七八糟则改为“老实芭蕉”“烂漆疤糟”。
王朔说,变文以使其陌生化。对于读者而言,初读感觉陌生,但读着读着,也可进入他的语境当中。
猫奴陈阿娇
在很多推介《纪年》的网页评论区,会看到类似“王朔还是那个王朔”的评论,但是年轻一代,并不熟悉王朔,他们会是这部作品的读者吗?
《纪年》的编辑是位“不肯自视为中年人”80后,他说,给渠道讲书之初,也是感受到在新世代的年轻人中,王朔因为太久没有出现,似乎已经不为“短直一代”所熟悉;在短平快的文本收获最大传播率的当下,王朔写就这样一部极为罕见的长河式小说,在拒绝了一切的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之外,似乎也在拒绝年轻一代的新读者。
但是,编辑部的90后打消了团队的担忧,不管书里讲了多久的粮草战备,兵戈谋略,90后的妹子中人气最高的是书中的陈阿娇。
陈阿娇作为“金屋藏娇”的女主角,几乎人尽皆知。但在《纪年》中,她不是顽劣的刁蛮公主,不是“千金纵买相如赋”的长门怨妇,也根本不是对刘彻痴心一片的皇后。她养猫、吸猫、爱猫,忠于猫;汉武帝催生,她暴躁地说:“滚”。
《纪年》的编辑说,陈阿娇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猫奴”,一个独立的、走到读者心中来的人物。
而且,陈阿娇不是一个人,在作为第一批读者的编辑团队看来,《纪年》中有家长里短、职场倾轧、困顿迷茫、甲方乙方……只是,“TA们和历史人物有着一样的名字,似乎也分享了类似的经历,但TA们是TA们自己。我们也在里面看到了我们自己。”
《纪年》正在陆续到达阅读者手中,你看到了怎样的王朔,怎样的过往,或者是怎么样的自己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