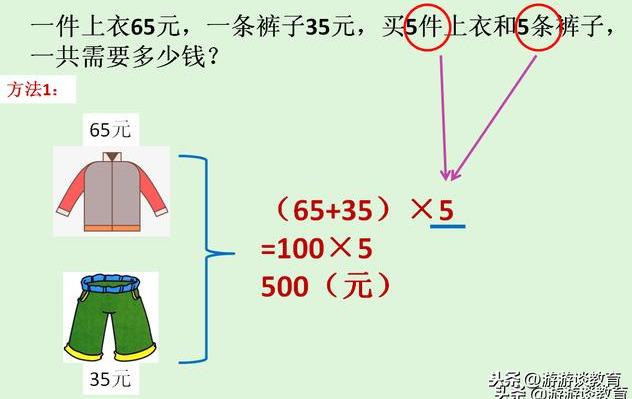骏瑜
近期,一则“高铁上应不应该卖卫生巾”(“卖”而不是“免费提供”,“建议”而不是“规定”)的讨论被推上了热搜,即使不排除话题炒作的可能,这样的内容还能产生争议,也是颇让人感慨“今夕是何年”。

要知道一两年前,我们关注的还是“月经贫困”问题,思考如何避免贫困女性因为这种正常的生理现象造成额外支出,加剧困境。彼时也有各种意见: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当然是应当免费提供,也有人从市场的角度,担心完全免费会破坏市场秩序,打击生产厂家——毕竟手纸也没有完全免费,于是有人综合不同观点,提出是不是可以提供最低保障,满足贫困女性的基本需要,同时允许非贫困女性按自己的意愿在市场中获得质量更高或品牌溢价更多的商品,接下来有人就提出,如何甄别真正有需求的贫困女性可能是一个困难……
所有这一切都是健康的公共讨论。没有非此即彼的立场,所有参与者都在试图以自己的知识基础和视角,听取他人的意见,帮助有需要的人群,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哪怕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完美的答案——而不是像“理中客”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说的,社会服务没有给你提供方便的义务,你必须自己解决你的事情,即使是与生俱来的、和你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的生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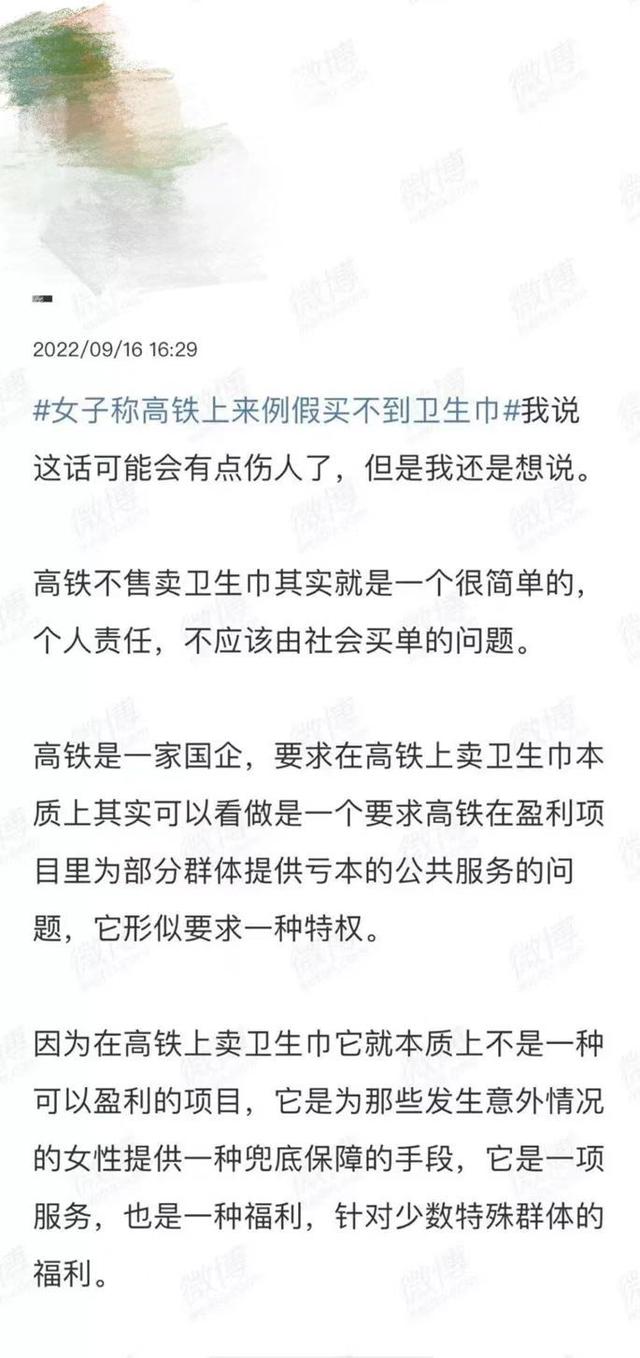
作为有性生殖的代价之一,月经给全人类的一半带来了无数问题,每月一笔额外的开支、出门时额外的行囊,都已经是小事,痛经的苦楚、社交场合的尴尬更让人难受。随着现代化进程,“月经羞耻”开始淡去,一些文化上的耻感在慢慢好转,但月经造成的代价仍然存在,而且主要由女性承担。
9月23日,李清晨医生在他的公号上发布了一篇题为《有性生殖的代价应该由谁来承担?》的文章,说得非常到位:“月经这种生理现象造成的麻烦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为人类生殖功能付出的代价,理应由两性共同承担。演化的结果让这一麻烦单独落在一个性别身上了,但文明的使命就是要矫正自然的不公”。既然每个人,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是由于人类的生殖功能才得以存在,那么与生殖功能相伴的月经,就没有理由让一部分人单独承担代价。
不仅是月经,由于生理原因,女性在人类的生殖过程中担负起了大部分工作,怀孕、分娩、哺乳、养育,所有这一切,不应该轻飘飘地用一句“这是你们出生时生理因素带来的光荣使命”就可以卸责。
更进一步,同样是李清晨的观点,很多遗传性疾病,也是个体的人类在为进化承担代价,这种情况下,全社会都应该提供支持。

中学的生物学知识告诉我们,在采取有性生殖的生命体内,携带遗传信息的基因总是成对出现,很多“缺陷”基因在与另一个“健康”基因配对时,不会致病,只有两个隐性“缺陷”基因一齐出现,个体才会得病,这种机率是非常低的,犹如魔鬼抽签。
而上文的“缺陷”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很多基因不能绝对说“好”或“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它们会以不同方式帮助人类的进化和生存。如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基因影响到患者血红蛋白的合成,携带两个这种基因的人会得病,血红蛋白不能正常供氧,影响正常生理功能。但如果只携带一个基因,携带者可以正常生活,同时由于血红蛋白的异常,能够抵御疟原虫的入侵,增加人类在热带这种疟疾流行地区的生存概率。从这个意义上,不幸的患者是在为热带地区生活着的千千万万人类付出代价。
这也是公益组织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不论是大病救助,还是贫困扶持,都是在为我们中“不那么幸运”的群体支付代价。出生抽签时运气不好的他们,可能会患上遗传病(或者更容易患上某些疾病),可能会陷于贫困,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挣脱,这时就需要公益组织来帮助他们,资助、赋能、创造条件,并通过社会募款的方式,将代价成本分散到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
代价需要共同承担,风险也一样。
现代商业社会得以兴盛的基础之一,正是由海上运输发展而来的风险共担的保险。海难是一个不可测的随机风险,而且对遭遇者是灭顶之灾,但海运和随之而来的商业交易,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繁荣和福利,这些繁荣的缔造者,不应该由于随机的、不可抵御的灾难而落入悲惨的境地。于是发源于北意大利,成熟于英国的海运保险逐渐成形,继而延伸出火灾、疾病等种种保险。
诺斯(Douglass C.North)也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中提到过,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到现代,有三个因素:非个人化(个体得以摆脱封建依附,脱离具体的个人身份,以技能在社会中生存);熊彼特所谓的破坏式创新(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以谋求高额利润);创新失败后为不幸个体兜底的福利保险。没有摆脱人身依附,个人就不可能凭技能创新,没有破坏式创新,社会就无法发展,没有兜底,个人就无法承担失败的代价。
让每个个体仅凭天生的资源条件生存和竞争,而不考虑合作和风险代价共享,那是霍布斯的丛林,不是文明社会。我们需要再一次重复这句话:“文明的使命就是要矫正自然的不公”。
当然,在代价和风险需要共担的情况下,谁应该分担,如何分担,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大部分的公共决策讨论,其实本质也正是关于此,谁应该为公共利益付出,谁会从中受益,这样分配是否公平?例如传染病流行时,为保护一些高危人群,全社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是理所应当的。不过,这个代价应该以多少为限?是否可以不经讨论,将风险从高危感染的人群转移到失业人群,且不成比例地放大?所有这一切,都有待正常、充分的公共讨论。

,